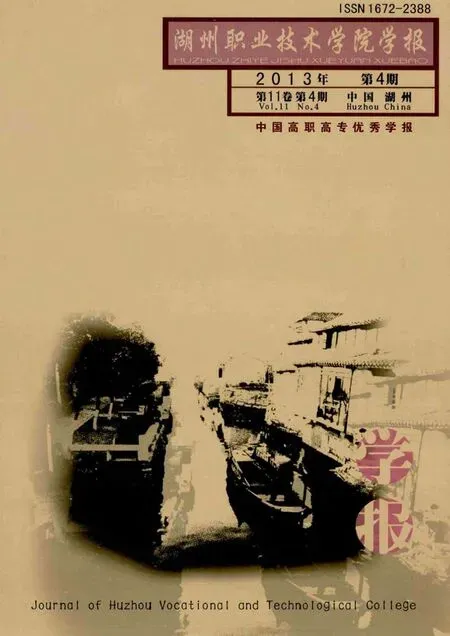中国音乐起源新论*
2013-04-12黄昌海
黄 昌 海
(衢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音乐起源于大自然的恩泽。《礼记·乐记》这样写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1](P160)
这里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就是指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产生雷霆、风雨、四时、日月等各种谐调的自然现象。音乐就是天地之间这种和谐景象的摹写。 “圣人作乐,所以象天地之和”这种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最高境界,体现了中国古代“乐与天通”的音乐起源论。与此相仿,《吕氏春秋》中也有“音乐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的描述。但这种抽象的结论并没有道明音乐起源的线索。
对于历史的考证,原本属于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职责范围,现在摆在了音乐学家的面前。它给我们一个启示:透过考古学家高度倍数的镜片对各种出土文物的凝神默想,我们可以跨越世纪的阻隔,透过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埃,尝试用一种描述性和经验式的方法去探寻人类初原时期与音乐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履迹。
一、音乐的源流概要
在我国,据考古发现,山顶洞人已经懂得装饰,并开始学会用符号来象征人的观念和情感态度,并能有意识地在死者身旁放置随葬品、装饰物,在尸体身上撒上红色的石粉,而且这种现象不约而同地存在于世界各个地方。许多古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都认为,这种现象已包含着或提供了某种观念含义,它源于人的灵魂意识,而这种灵魂意识则是由“巫”来实现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源头之一。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红”色象征着血液和生命,死者涂上红色的石粉,就意味着赋予死者新的生命。所以,红色就带有了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并伴生了朦胧美的意味。
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仰韶先民的瓮棺底部都有一个孔,意在让死者的灵魂自由出入,这是原始人类灵魂意识的物态化的反映。现在,世界各国仍然保留着的招魂仪式,大概也就是这种灵魂意识的继承。
从我国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和河南舞阳县、贾湖县贾湖史前文明遗址的挖掘中,分别发现了八千多年前用禽类肢骨制成的骨哨,特别是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一百多支品种各异、音色也各有特征的骨哨。在德国南部的布劳保峪勒还发现了一支三万五千年前的骨笛。而在仰韶文化遗址也曾出土多件陶埙。它们形如橄榄,中部圆形,两头椭圆,顶端有一个吹孔,另一吹孔贯穿两端。这些出土的远古乐器经考古学家放射性探测后,被断定为均制作于距今六千至八千年左右。这种分布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远古音乐现象,使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音乐史家无不感到惊讶。我们的先民对于音乐的认识和使用,远在他们创造文字之前。他们所从事的音乐活动比我们今天所能了解的要丰富得多。他们在当时意识水平的基础上,极大地开发和积累了对音乐功利性的认识能力。这些大量出土的远古乐器,以一种物态化存在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远古先民原始文化中音乐意识形成的源流,并对我们研究史前音乐史具有重大意义。
二、音乐起源的劳动说
一种社会文化的出现不是先民梦中想象出来的,它往往与自然现象及人类的劳动生活相关联。远古人类几乎在同一阶段的相当范围的地域空间内对音乐产生了认识。人类产生对音乐的认识不是孤立的人类文化进化现象,而是人类在与大自然的交合中产生的必然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大自然构成的必然关系。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在一种“前艺术”的文化中,必定蕴藏着人类文化心理的许多秘密,有着某种人类共有的规律性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原始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这种人类所独有的音乐形态,一方面丰富了他们所需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听觉感知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人类音乐创造对象化的产物。
同时,大量实证表明,与劳动紧密相关的原始乐舞同原始人类的生活具有直接的关系。
就音乐的构成来看,形成乐音动态形式的基础是节奏。这种原始乐舞中的节奏意识是强化人对节奏感知力的重要来源。
那么,原始人类最早的节奏意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集体性的劳动中,某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动作,使他们感到好奇,如共同把猎物抬回家时,必然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杭育、杭育”声。在两千多年前,古籍《淮南子》对这种劳动号子即有记载:“今夫举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动力之歌也。”[2](P3)这种劳动中产生的协调律动,就演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节奏意识,使原始人从中感到了愉悦。而要把劳动中力量的实际使用所引起的愉悦再度体验的愿望,则促使了再现某些动物动作和劳动动作的舞蹈的出现。仅从云南现存的各种少数民族传统舞蹈中,就可发现这种原始乐舞的胎记。如佤族木鼓舞,便是劳动场景的生动再现:蒙羊皮的大鼓二至三行顺序摆开,每只鼓的鼓尾站一人,鼓前站两人。众多女子成双起舞,应和鼓点,阵容宏大,声势热烈。舞蹈表现的内容是从栽秧到收获的全过程,耕田、撒秧、拔秧、绑秧、送秧、分秧、栽秧、割谷、捆谷、打谷、背谷等――再现于舞中,共计十三套鼓点。每套鼓点各异,其间还有不知名的鼓点,使栽秧鼓谱复杂多变而丰富,跳鼓者潇洒优美。时而敲鼓,时而用鼓槌交叉碰击,发出悦耳的节奏,再加上那种陶醉自若的舞姿,令观众的思绪随着鼓点去追忆那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
节奏意识的起源必与舞相联系,而节奏又是产生音乐的基础,所以,这种与舞相生相伴的音乐舞蹈,被后人称为乐舞。
劳动中的节奏是产生音乐的起源之一。如云南韶通的苗族芦笙舞,在他们举办活动时,少则十来支、多则上百支,大大小小的竹簧笙聚集在一起演奏,它们没有统一的律制,也没有统一的调性,只有相同的节奏,众人聚在一起“齐声高奏”。那恢弘的气势,新奇的音响,充分展现出远古先民特有的表达方式。而云南沧源佤族的传统木鼓乐舞,在木鼓的敲击伴奏和“歌唱”中能使舞者体验到情感的升华,还会使舞者达到迷狂状态,不到精疲力竭不会停下。于是,云南民间有“从早跳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的民谣来比喻这种痴迷。这种乐舞形式就是一种非常久远的文化样态。
三、音乐起源的巫术说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经历过巫术时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无论怎样原始的民族,都有宗教与巫术。”[3](P3)而巫术的主要功能在于“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达到影响自然以及他人的目的便产生了巫。”[4](P226)这说明,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很粗浅,而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相当幼稚时,便会去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以便支配自然。这时,巫术就应运而生,并由此建立起一种确保自我的保护机制。
巫术在原始社会里具有超常的社会功能。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巫,祝也,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在原始人的意识里,巫的一切言行都是受了天地之托,神力无限,能代表鬼神的旨意。因此,巫师集部落宗教、生产以及艺术的知识于一身,他们是“智、圣、明、聪”的化身,而且她(他)们常常就是部落的领袖,被奉为神的使者,能对灵魂、风雨雷电、大漠山川等自然中的神秘现象做出权威性的占卜和解释。
巫术的存在与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极为密切。巫师除了具备上述神通广大的能力外,还是“歌唱家和舞蹈家”。她的所有占卜都与歌唱、舞蹈相联系,于是才有古书中记载的远古传说:“川石拊石,百兽率舞。若国大旱,则帅巫舞?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这些都是巫师在社会生活中远古身影的再现。这种巫术的礼仪活动不单在远古的中华大地存在,在南美、澳洲,人类文化学家也发现了几乎与之一致的活动,如在他们现今的土著文化遗存中,剽牛要先跳舞、唱歌,以示对牛神的安慰。非洲部落的人出猎前都有占卜和歌舞的仪式。歌舞和巫术是合二为一的,它们与其部落、氏族的命运兴衰息息相关。
巫术在文学中的反映是神话传说,在音乐中的反映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原始乐舞的基本形态。在《楚辞·九歌·东君》篇中就有“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和篇”,说的就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紧密相连,三者合为一体的文化形态。
原始人在巫术的幻觉中,常常通过乐舞宣泄达到与外部世界的和解,以求得内心的平衡。
人类许多古老的文明能传到今天,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巫的存在,是巫师们在各种节日、集会、祭礼、婚丧等活动中一代又一代地传唱下来的。所以,何晓兵教授称巫师是“人类第一批传道解惑的知识分子”。
巫师作为介于人与神的中介,他们的言与行都不能同于凡人,语言要用音乐这种“神的语言”,动作要用“神的肢体动态”,才能达到与神沟通的目的。只有音乐中那富于强烈情绪的感染力,才会使原本冗长的讲述变得生动;音乐与人声语调和生活节奏丝丝入扣的配合,才加强了听众的记忆力。所有对洪荒时代的遥远回忆,对空有轮回的追问和应答,都被巫师化为部族都能听懂的故事。最终,部落的精神形态、生产经验的积累,以及相关的行为规范,才得以在星空下的篝火旁、在同天地交感的幻觉中代代流传。
因此说:“后世的一切艺术、科学、哲学都诞生于原始乐舞的摇篮之中。”[5](P89)并且,正是音乐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化形态,陪伴着我们原始先祖从“兽”彻底进化为“人”,从蒙昧走向智慧,从野蛮迈向文明。
李泽厚先生激动地写道:“后世的歌、舞、剧、画、神话、咒语……在远古里是完全揉合在一个未分化的巫术活动的混沌统一体之中的……想当年,它们都是火一般炽热虔信的巫术礼仪的组成部分或符号标记,它们是具有神力魔法的舞蹈、歌唱、咒语的凝化了的代表。”[6](P11-12)
巫师作为人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于音乐的把握、运用,早已在我们不能认知的年代扩大了原始人的听觉感知力,并埋下了审美的种子。自巫术存在的那一刻始,巫师们从事的每一次礼仪活动,就是一次远古音乐形态的活化,都是一次原始人类音乐听觉模式的重建和人类审美意识的催生,更是音乐作为一种载体赖以生存、传播和发展的重要依托。
巫术,它作为远古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观念形态,它的存在本身也只是一种意识物态化的符号,它不是艺术起源的全部动因。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它又是审美文化的母体。
在人类的初原时期,乐舞之于巫术也只是作为巫师手中“宣唱法理”的一件道具而已。在原始宗教礼仪中,乐舞的表演对原始人“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一种力量,一种支配与征服其他物类,控制人类命运的力量。音乐这种功能只存在于巫术仪式中才能得以体现”。[7](P517)
原始时代艺术的“含义”与“代表性”,是指巫术的一种象征性。也正是文化本身的社会意义,直到近代,许多原始民族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技或政治,却无一没有音乐,这其中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四、音乐起源的模仿说
人类社会能摆脱原始社会大踏步地走向现代,靠的是善于思考的大脑和灵活的双手。因此,音乐起源于模仿是音乐起源于劳动与巫术之后的必然命题。模仿与劳动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最直接的两条途径。
生产力的低下,认识的贫乏,使原始人对自然界怀着一种神秘的恐惧和崇拜心理。正是由于无知而引发疑问,疑问而引发想象,而想象则引发出了模仿。
我们可以肯定,史前先民在制作这种模仿鸟兽的哨音时,一方面开发了人类最早的音乐听觉感知力和双手的灵巧性;另一方面又从这种鸣响中获得了听觉的愉悦,并在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中认识到自己主体存在的价值力量,从而使这种模仿行为摆脱了简单的劳动性质,而带有一种内心审美体验的意义。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就对音乐起源于模仿进行过研究,并有许多的论述。他们认为:“艺术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模仿”,“人从模仿中学到知识”,“音乐源于模拟”,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模仿产品的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产物。
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茨指出:“人们在开始能够编出流畅的歌曲而给听众以享受的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用口模拟鸟类嘹亮的鸣声,最早教会居民吹芦笛的,是西风在芦苇空茎中的哨声。”[8](P22)
在众多的原始乐舞中,人类无一不是将劳动中的习惯动作活化于舞蹈之中,或模仿劳动的过程,或模仿自然中各种动物的动作、叫声。人类在这种模仿中获得审美的愉悦,演绎出今天音乐的雏形。
节奏是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在原始乐舞中,节奏性乐器是最早与乐舞相联系的节奏工具。故,作为一种节奏性工具,它的出现虽然并不与舞联在一起,但又与乐舞相关联,它是最早与乐舞融为一体而具备了乐器功能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鼓的产生:雷是一种威力巨大的自然现象,它能带来狂风暴雨、洪水灾害,能引起森林大火,击毙人兽。原始人类对此感到无比惊恐。他们看到其他人群和各种兽类常被雷声吓得四处奔逃,就对雷鸣产生了迷信和崇敬,希望自己也能通过什么办法发出雷鸣,借以吓退其他部落的掠夺,并可在围猎时使用。为了达到模仿的目的,原始人类开始寻找雷兽。在他们“万物有灵”的心理看来,雷鸣一定是某种凶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因此,史籍中有“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如雷”[9](P248)这样根据传说的记载。鼓在非洲是一种非常普及的乐器。布隆迪人的鼓在制作上还模仿母体的形态,同时表现出一种生殖崇拜。在布隆迪人看来,鼓的每个部位都与母体的每个部位相对应:整个鼓面是婴儿安睡的怀抱,固定鼓面的钉帽是母体的乳头,加固鼓面的皮条是母体的冠带,鼓身是母体的腹部。我国云南傣族的象脚鼓,也是典型的带有模仿性质的乐器。我国古籍有“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的记载,表明朋友相聚,在“鼓瑟鼓琴”中获得愉悦。
无论是原始人类模仿雷声制成了鼓,还是模仿鸟鸣制成了鼓哨,模仿黄莺唱出了悦耳的歌,这些历史都为我们揭示了远古初民在审美听觉上已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心理结构,从而才使各类具有拟音特征的乐器从初级的模仿发展到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创造,从单音意识发展到二度音、三度音,直到今天变化无穷的七音十二律的各种组合。人类音乐文化的这种发展进步本身,也反映着原始人类通过劳动发展自己、改造社会所经历的实践过程。这也是音乐文化的发展在特定物质条件下的一个必然过程。纵观人类音乐发展的历史,它们无不带有这种姗姗学步的痕迹。
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提高,为“音乐模仿说”提供了更多可供借鉴的理论依据。
无论是“写实”模仿或“抽象”模仿,它们都在作曲家的琴弦上幻化为动人心弦的乐音。从音乐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它们两者是相互结合、相互参证、相互促进的,共同构成了人类音乐文化壮丽雄奇的音响之流。从古到今,世界各民族的艺术正是在一种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符号意义。正如人类学家吉尔兹说的那样: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符号的和解释的。如此,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各种文化才能在悠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交融,各民族文化多元并有的格局才能逐渐形成。惟其如此,一部人类音乐的发展史才成为一部充满随人性之骚动而起伏,并因之形成了各民族艺术风格独立、流派纷呈、多彩多姿的音乐风格史,也是人类自由理想的追求史。
参考文献:
[1]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2]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
[3] [英]马林若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和神化[M].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6.
[4] 方 坤.民族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 何晓兵.音乐与智力[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6]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7] 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8] 何乾三.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9] 冯国超.山海经·海内东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