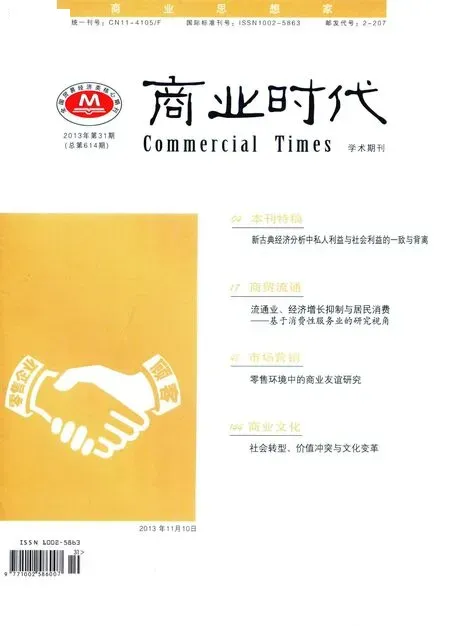社会转型、价值冲突与文化变革
2013-04-11雷信来副教授李大卫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 雷信来 副教授 李大卫(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大理671003)
社会转型与冲突及国学的勃兴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学热就开始在国内兴起,最开始是由于一些学者担心中国传统文化失传而引起,接下来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国学热,是对市场化、城市化冲击下传统熟人社会瓦解、传统社区崩溃、传统道德沦丧的反应。而当前这一波的国学热则以政府为主导,其主要目标是希望通过重建社会道德,加强公民的道德自律,抑制政府腐败,减少社会失范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国内这一轮国学热的兴起有其客观原因。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西方的文化霸权不断受到挑战,文化多元化逐渐成为时代潮流。东亚经济的复兴,东亚模式的早期成功,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逐渐受到国际学者们的关注,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也使东亚各国开始重新审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并重新树立起民族文化自信心,文化复兴成为普遍现象。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传统文化的复兴就成为必然,国学热的兴起是其外在表现。此外,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传统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由于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态、能源危机而饱受诟病,现代化必须转型已经成为精英的普遍共识,但西方文化显然难以解决全球合作、人与自然之间的剧烈冲突问题,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崇尚集体主义、道义至上、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除去这些外部因素,国学热在国内不断升温的更深层次原因应该是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而导致的应激反应,现代化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消解,在传统道德秩序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间,都会出现一段价值的真空期,再加上社会结构的剧变带来的利益、身份的剧变,必然会加剧价值危机、社会冲突,文化保守主义是其反应方式之一。
从当前国学热中政府角色看,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应该是当前这波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急速的社会转型,而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性质更使转型变革时间大为压缩,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继时性矛盾变成共时性矛盾,使各种矛盾交织、重叠、共振,相互制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变革的艰难性。由于现代化源于西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支撑,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更大,与传统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激烈,社会秩序的混乱,传统道德的崩溃程度更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完全可以借鉴西方与日、韩的现代化经验,然而,作为文明古国,悠久的文明传统,长期的文化辉煌形成了路径依赖,使中国的文明转型比日、韩更为艰难。长期片面的现代化,政治改革的滞后,使特殊利益集团滋生,使改革阻力重重。为维护自己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特殊利益集团拒绝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妖魔化民主,鄙弃启蒙思想,采取了保守主义对策,企图通过复兴封建的国学来继续愚弄国民,以达到维护自己特权的目标。
如果说民间国学主要侧重于传统道德与文化,有其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此次政府推动的国学热则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在学者们的心灵鸡汤失灵以后,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企图借助政府的权威来推行封建礼教,平息民众的不满,化解日益激化的社会冲突,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然而在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巨变,全球化影响日益深入的背景下,这种脱离国情的保守主义应对政策显然难以适应社会需要,不能满足民众对公平、机会均等的诉求,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冲突加剧的根源,这也就决定了国学热难以真正地热下去,更难以解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
社会转型冲突的应对模式及其效果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交替期,会出现普遍的社会秩序混乱与价值观崩溃,社会失范行为增多,社会冲突加剧,给人一种礼崩乐坏的感觉。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冲突,主要存在着三种危机解决模式:保守主义、折中主义、激进主义。
保守主义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转型冲突解决模式,几乎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所有重大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中,这种反应模式特别受旧统治阶层的欢迎。因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极力维护过时的社会结构并不断美化之,为自己过时的权力披上合理性与合法性外衣。即使在今天,各种保守主义依然大量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就是其代表。在社会转型的价值真空期,思想与价值观的冲突难以避免,冲突意味着传统上层建筑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对旧的上层建筑进行合理扬弃,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传统的超越。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的过度美化与维护甚至回归,其实是一种反历史行为,必然难以解决转型造成的社会冲突,并有可能使冲突变得更加激烈。
折中主义是在对传统合理扬弃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这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社会转型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像保守主义者那样抱残守缺,对于传统的上层建筑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全盘肯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保留,剔除其中已经过时或者糟粕的部分,弘扬其中的精华。对于国外先进的社会转型经验与国外先进的制度、文化与技术成果,也不像激进主义者那样教条主义地全盘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接受,并能够把传统文明的精华与国外先进的制度文化进行融铸、提粹与重构,创造出适应本国社会需要的新型文化。一般来说,折中主义既不那么保守也不过于激进,因此,以这种模式进行的文化转型一般比较成功。
激进主义者对于国外先进经验、文化与体制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企图实现制度转型的飞跃。这种转型模式由于脱离本国实际,对本土资源的忽视,也没有考虑到国外经验与本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水土不服,反而加剧了转型冲突,后果更为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东亚四小虎对东亚模式的简单模仿,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企图继续依靠威权体制来实现现代化的飞跃,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和金权体制的蔓延,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发展之路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没有对启蒙思想的认同,激进的现代化转型只能是徒具形式,民主体制亦难以巩固。
在三种社会转型冲突解决模式中,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两个极端,前者的抱残守缺会延误社会发展,后者的教条主义会导致转型失败,欲速而不达,只有明智的折中主义才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在对传统合理扬弃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部的文明精华,融合提炼,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新文化,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扬弃
当前国内的国学热比较浮躁。因此,对于当前国内出现的新一轮国学热,有必要进行认真鉴别,合理扬弃。
首先,必须对国学进行比较清晰的界定,区分其性质。一般来说,狭义的国学主要包括儒学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学术著作,广义的国学则包括了几乎中国所有传统文化,它分为几个层次,精华与糟粕互现,需要进行批判地继承。只有狭义国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其中的儒学更长期被作为“国学”,法家、道家、释家也为统治阶级所推崇,成为他们压迫和麻醉老百姓的工具。因此,与“民间”国学不同,对于具有极强意识形态性质的“官方”国学,应对其进行全面扬弃。随着世界启蒙运动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中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于植根于封建土壤的“官方”国学,有必要进行合理扬弃,使其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其次,人的有限理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验论证方法决定了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由于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信息收集能力和成本的制约,个人只能达到有限理性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理性,并且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个人的认识也只能达到相对真理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的高度。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国学”经典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轻实践重先验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中国文化中很多的唯心主义成分经不起实践与科学的检验。
最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要求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重新达致统一。一些人割裂经济与文化、政治的关系,企图在经济基础改变时继续坚持过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这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东亚四小虎后威权体制的衰微就是前车之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精华需要继承,然而不可否认,作为专制社会的产物,必然会存在着很多落后过时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专制思想,虽然孟子也曾提出过民贵君轻思想,但不占主流地位。长期的封建统治也使中国文化充满了官本位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此外,中国差序格局的文化观使启蒙思想难以推行,法治社会难以建立,小集团利益经常超越了社会共同利益,导致整个社会缺乏信用,社会整合程度低,公民社会极度不发达,社会进步缓慢。
因此,对于国学应该弘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并大力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才能有效缓解当前社会的道德危机,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为中国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创造一个和谐的文化软环境。
弘扬传统与文化再启蒙
当前中国面临的文化、道德与社会危机直接受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从各现代化转型成功的国家来看,传统文化资源虽然能够加速或延缓现代化的进程,但要实现成功的现代化转型,一些共同的准则必须遵循,如经济市场化、产权明晰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等,只有遵循这些基本规则,现代化才能取得最后成功。从历史角度看,接受这些基本价值是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传统文化的扬弃虽然重要,但不是根本问题,中国社会道德崩溃、文化衰败的主要根源在于对启蒙思想的抵制,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腐败高发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机会不均等和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中国道德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官德的普遍败坏,文化不振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对思想的过度控制。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紧要的不是保守主义的文化复古,而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启蒙,使上层建筑能够与自由市场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然而,启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集权遗存的东方国家来说,民主的土壤本就非常瘠薄,再加之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历史体制路径依赖的惰性极大,致使民主市场体制的培植、涵溯及完善就更需要时间。但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拥有先发国家所没有的后发优势,能够加速中国社会的启蒙进程和现代化转型;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启蒙运动并非没有任何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继续发展,启蒙倡导的民主、自由、法制思想必然会最终被接受,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只有顺应时代要求,适时地调整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危机,实现和谐发展。
1.[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美]彼德·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奥]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王文龙.比较优势、威权政治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J].二十一世纪,2007(8)
5.王文龙.后新自由主义、后东亚模式与新东亚模式比较[J].国外社会科学,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