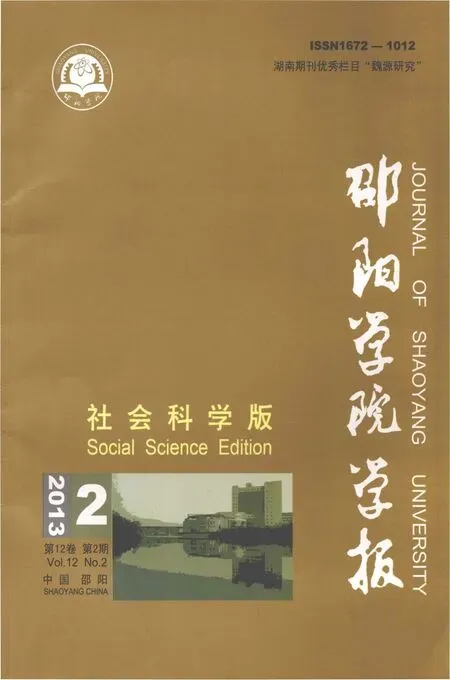《我的名字叫红》的复调性对话
2013-04-11郭建飞
郭建飞
(吉首大学 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于1998 年,之后被翻译成汉语于2003 年传播到中国,但并未引起重视。2006 年,帕慕克凭借《伊斯坦布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此,国内掀起了一场帕慕克研究热。《我的名字叫红》(本文中以下将称其为《红》)也因其独特的叙事技巧而被众多学者反复研究。本文旨在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出发来研究《红》的对话性。巴赫金,作为伟大的诗学理论家之一,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以及狂欢化理论,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凝练及升华,巴赫金又提出了对话理论。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哲学思想前后两个时期的重要主旨,是其文学理论的核心。就巴赫金而言:“对话的本质在于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
一、真正的作者“我”和人物叙述者“我”
《红》中不存在主人公。虽然在小说中,人物黑的叙述有9 个章节,但他只是文中10 多个叙述者的其中之一。在此必须首先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作者,什么是叙述者,什么是“隐者”作者。众所周知,《红》的作者是帕慕克,那么,毫无疑义,帕慕克就是小说真正的作者。关于叙述者,毋庸置疑的是读者印象中的“讲故事的人”。但米克-巴尔认为叙述者除了小说中的“讲故事的人”外,叙述者还作为一种功能在小说中出现。他说“叙述者,或讲述人(narrator)指的是语言的主题,一种功能,而不是构成文本语言中表达其自身的人。几乎毋庸指明,这一叙述者并不是叙述作品的(传记性的)作者”,“我说的也不是隐者作者”,是“所有创造小说的工作的代理人”“没有叙述者的小说是不存在的”。[2]从米克-巴尔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叙述者是作为一种功能存在的,而不是作为身份意义上的人物而存在,他是一种抽象体,他的功能是“讲故事”。而“隐者”作者,是一种身份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人物个体。并且,叙述者有可能存在很多,但“隐者”作者只有一个。
翻开《红》的目录可以发现,每个章节的叙述者都不同于上一个或者下一个,翻开这部长篇巨著如同翻开一本短篇小说集,各个章节间毫无联系,直至读完才发现原来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整个故事就像是各种乐器联合在一起演奏的交响乐,“这种多角度第一人称的叙述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3]
《红》的叙述者有“死人”、“谢库瑞”、“奥尔罕”、“凶手”、“姨夫”、“橄榄”、“鹳鸟”、“蝴蝶”、“奥斯曼大师”等。叙述者不仅是这些有生命的人物,还有一些动物以及无生命的抽象物,如“马”、“红”、“硬币”、“树”,等等。这些有生命的人和物,与无生命的抽象物一起在这个大舞台上可谓是热闹非凡,将戏演的有声有色。有时他们步调一致,有时他们各抒己见,相互碰撞。正是这种独特的讲话方式吸引着读者继续向前继续向下,总想着弄清楚事情的原委,阴谋的真相。但是,情况往往不能如人所愿。《红》的开头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场谋杀案:高雅先生被三位细密画家的其中一位谋杀死于枯井中。作为小说的主要线索,寻找杀人犯成了推动情节发展,引导读者继续下去的一种巨大引力。大家都在分析、猜测、怒骂甚至诅咒这名杀人凶手。处于道德的劣势,杀人凶手本该隐而不语,尽量避免抛头露面,而《红》中的杀人凶手却堂而皇之地作为一名叙述者存在于小说中,述说自己杀人的动机,为自己辩解,甚至总结出是由于高雅先生自己愚蠢害了自己,并列析杀死高雅先生所能带来的种种的好处。
在这场戏中,各个角色都以均等的身份存在着,没有主人公,亦无配角。正是这种真实的存在使得小说成为一支复调小曲,各种音调此涨彼落,此兴彼伏,然却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即使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杀人凶手也有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和空间,试图让受述人相信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让读者无形中受到影响,在该杀与不该杀中徘徊。正是这种复调声音的存在,使得每一个人都以一种独特的声音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姿态与意义。正如巴赫金所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是一种在独特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的与众不同,自我的实现是在世界中与他人通过话语交流的过程中得以实现。[4]
二、非人的叙述者“我”
《红》不仅存在众多的人物叙述者,非人叙述者在小说中也混杂存在。异于传统小说仅将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做法,《红》中非人叙述者的存在是其复调性对话的又一特征。根据人物叙述者的定义:人物叙述者不仅承担着叙述的任务,同时也是所讲述的情境与事件中的一个人物,既以一个人物的身份活动,也与故事中其他人物形成交流。[5]这一对非人物叙述者的定义表明:它虽然是叙述者,但是非人物的,并且不能参与到故事中来。然而,在《红》中,“狗”、“树”虽然是有生命的,但它们是非人物叙述者,“马”(一幅画)、“硬币”是无生命的,它们也是非人物叙述者,但它们却同时又都是故事的直接参与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与其他人物叙述者进行有效的互动。作为旁观者,他们的叙述更加客观,可信度更高。
比如说“马”,作为一幅画,虽然是无生命的,但是作为非人叙述者,它却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杀人凶手留下的一个证据(鼻孔有缺口的画法)。此章节中,通过“马”的叙述,读者了解到了在画哪怕是一种马的不同技巧,笔的起始不同点以及不同的视角。“硬币”,作为一个抽象物,在小说中摇身变作一个叙述者,一个有生命、会言语、可思维的存在体。讲述人们持着为何开始制造假币,不法商人如何用一枚假币欺骗手持真币的农夫,人们为何越来越多的制造假币而不使用真币等等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正是读者对这既被命名又被回避的真相感兴趣,话语狡黠地藉恰似以制造含混,因为含混指明真相,然又平铺直叙地将真相淡化为迹象而已。[6]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在其长期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重要诗学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都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7]《红》甚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对话性更加突出。其叙述规模远远超过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叙事规模,开创了一种更加灵活多变的、思想更加丰富的对话性模式。《红》从头至尾都在讲故事,但故事从未受到任何情节或者人物的影响,作者为了达到更好地叙述的目的,采用不断切换叙事视角的手段,发出众多叙事声音,完全摆脱了直至19 世纪末的那种作者的全能视角模式,剥夺作者的一切支配权和干预权,使得没一个有生命的甚至无生命的抽象物都成为有思想的存在体。所有的叙述者都可以说任何自己想说的话,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享有绝对的自由而不受任何事物的支配或约束。作者也从不评判谁是谁非,各个叙述者也不妄加评价他人,而仅仅是表述自己内心所思所想。
众多叙述者站在同一个舞台,无主角,无配角,每个存在体都是自己的上帝,并同时与其他的叙述者或者是读者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在这个热闹非凡的舞台上,读者从文字中看到的听到的每个叙述者的声音都是真诚的,都是无辜的(包括杀人凶手在内),无法判断究竟哪个叙述者是可信的。
三、两条线索下的另外一种声音
《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一方面由于其丰富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由于其独特的情节结构安排,与此同时,使之如此成功还在于隐藏于两条线索(谋杀与爱情)之下的第三种声音的存在。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最初的期冀是找出杀人凶手,将之绳之以法,但在探寻的过程中,作者并未让读者如愿以偿,而是将这种找到答案的快感加以延伸——爱情故事穿插其中。破解谋杀案、将爱情进行到底成为了引导读者继续阅读下去的动力所在,也是整个故事情节的两条线索。这种阅读过程亦如中国套娃,大娃娃之内还有小娃娃,小娃娃之中还有更小的,更小的内部还有再小的,以此类推,给读者带来无尽的喜悦与惊叹。
作品在向读者展示爱情与谋杀这两个主题的同时,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隐藏在这两条明线之下的文化内涵——第三种声音。《红》并未交待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从各个叙述者的话语中,读者不难发现:就绘画领域而言,文中的土耳其传统绘画正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碰撞。而对于这一冲击与碰撞,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态度:有人固守传统,排斥异己;有人崇尚外来物,全盘接受;有人在新与旧之间摇摆不定,无所适从。第一类固守传统的人物代表是奥斯曼大师和高雅先生。奥斯曼大师对于苏丹王让其用透视法作画是对自己的侮辱,而且,为了避免受到现代作画法的影响,他宁可刺瞎自己的双眼;高雅先生,作为一名镀金大师,服务于姨夫大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有幸看到了姨夫大人让大家所作绘画的全景,也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姨夫大人可以被视作第二类对于新文化态度的代表人。第三类代表人物是黑,可以说他对外来文化的侵入持中立态度,亦可说其在外来文化的冲入之际摇摆不定无所适从。
对于多元文化社会,“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异存,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各自发展与共同发展。”[8]对话本身意味着差异的存在,对话的目的是尽量使不同见解和观点能融洽共在,合法并存,体现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学术思想和态度,是对文化专制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抗争,对理想的文化融合的憧憬。读者也就是这样跟着帕慕克的文字,任由“声音”自己言说,边听边做出自己的判断。
帕慕克通过《红》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交响曲,各种声音均等地参与其中的对话,没有主从之分,亦无优劣之别。帕慕克游荡在新旧文化、古今文化的冲突中,试图在他虚拟的小说世界中,向读者展示落后衰败的传统文化、兴起的现代文明,并向读者展示了在这场变新与革命中不同人的不同声音。在虚构的谋杀故事的背后,作者向读者讲述了一种文明被割裂的真实痛楚,“帕慕克在这部书中,借一个关于细密画的故事,动手解剖这个古老民族的灵魂,并代表土耳其人述说着文明被割裂和架空的痛楚”[9]。
[1]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2]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叙述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41.
[3]陈福兰.〈我的名字叫红〉不可靠叙事者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1.
[4]黄梅. 也说巴赫金. 外国文学评论[J]. 1989,( 1) : 10-14.
[5]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0.
[6]罗兰·巴特,屠友祥译. S/Z[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2-253,253.
[7]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玲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344.
[8]王蒙. 关于文化间的对话[J]. 中外文化交流,2002,(1) :4-5.
[9]Associate Press: Turkey’s Pamuk w ins Nobel literature prize[EB/OL]. Oct.13,2006. Http: //www. msnbc. msn.com /id /15232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