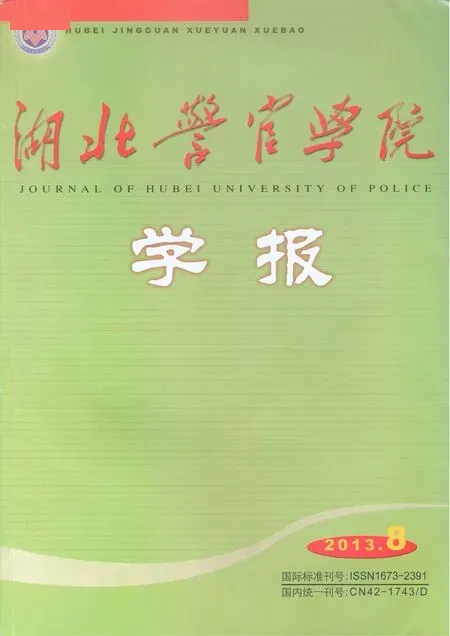试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度
2013-04-11任绪保
任绪保
(中共日照市委党校,山东 日照 276826)
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旨在监督司法机关执法环节中的违法犯罪现象,最终保证法律得到严格贯彻执行。一方面,法律监督权权高任重,是法治国家建设重要的一环,但另一方面,监督的单向思维导致监督权缺乏权力制约机制,因此也增加了其被滥用的可能,法律监督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对监督权本质的正确认知。
法律监督源于对权力扩张性和强制性的警惕。一方面,权力具有扩张性,既得利益者倾向于扩张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表现在权力使用的后果和限制,权力的扩张性和强制性结合起来,就会使权力成为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两受其益,用之不当,则两受其害。因此,只有把法律监督权放在权力制衡机制中才能避免使其成为“脱缰的野马”,也只有成为被监督的对象才能保证对法律监督权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自律和自觉。
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运作的现状
目前,许多学者和检察官在论证我国的法律监督权时,将法律监督的外延无限扩展,涵盖检察机关的一切职权。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检察机关扮演着更为广泛的角色,法律监督不仅是一种有效和可靠的治吏清障手段、法治保障权能、服务社会机制,而且可以借助个案的处理对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我国的检察制度是适应强化国家法治和民主政治的时代要求,用以制约司法权、打击和铲除国家管理权力运行中腐败现象的手段,是一种控权机制。这种对法律监督过分要求的根源在于中国检察权受苏联一般监督权的影响,事实上,它已经超出了法律监督原始的本质和目的。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监督”的字句,但可以通过解释《宪法》第129条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进一步得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实际上承载了有限的一般监督与专门的诉讼监督相互交叉的职权配置——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刑法的,依据有限的一般监督权启动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同时,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依法进行,因此,检察机关对追究刑事责任中诉讼活动合法性予以专门的诉讼监督。
上述看法是一部分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法律监督权本质和目的的误解。事实上,法律监督权并不是检察权的另一种称呼,而是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外延的。法律监督的范围取决于法律监督的本质,法律监督的本质决定其监督的限度。首先,要知道法律监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因此不是为监督而监督,而是通过监督达到法律被严格实施,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其次,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效率也是为了保障公平。事无巨细的监督在实践中无法实现,“无限监督”不符合我国国情,而且也不符合现行宪政结构中的监督法权体系。法律监督与权力制约并不能截然区分,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司法权力的行政化非常严重,检察机关本身就是双重领导体制,可见,法律监督与权力制约二者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我国法律监督权运作的现状。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度
(一)从实体法上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限度
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法律监督应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而不能超出宪法赋予的权力区间。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都要服从于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因此法律监督的“法律”,首要的就是要遵守宪法。法律监督服务于宪法,其目标就是要实现宪政和依法治国,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突破“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监督怪圈,因为法律监督之上有宪法的制约和监督,而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当然不会再有谁来监督宪法的疑问。这就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设计比三权分立制度优越之处。故宪法和法律是检察监督的实体法限度所在。
对于法律监督应树立监督法定原则,坚持罪刑法定,依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仅有好的法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好的法律得到良好的实施。法律监督的目标就是要保证法律得到良好的实施。因此,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核心原则一样,监督法定原则也是法律监督的最核心原则。从实体上看,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坚持的原则是:监督法定、有限监督、重点监督和程序性监督,应当遵循诉讼规律,不擅自行使监督权,做到理性执法和理性监督。从程序上看,法律监督的全过程,从法律监督主体、地位、任务到法律监督的内容、对象和法律监督活动的原则、活动的方式、方法以及程序等,都由法律规定。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检察监督的合法行使和有效行使。
(二)从程序法上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限度
相比于实体法制约,法律监督更重要的是程序法制约。实体上的监督容易导致对司法和执法的过度干预,权力的扩张性使得监督权容易背离法律的初衷。因此,我们认为,法律监督更应该强调程序面。没有程序法上的公正,实体法上即使实现了公正也会受到质疑。因此,法律监督不仅要严格依据实体法,也要遵守程序法的规定;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监督要坚持程序公正优先的原则。事实上,程序法不只是实施实体法的工具,它还具有独立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法律监督权来说,检察院主要的就是从程序上进行监督,被害人和被告人在实体监督权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有切身利益在里面,自然会很关心实体正义的实现。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实现实体正义,避免持续上访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法律的效率。
程序性表明,法律监督只是执法过程中的权能,而不是决定执法结果的权力。法律监督只是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的权力,而不是对另一种权力给予实际处置的权力,其效力主要是启动相应程序和督促有关部门对违法情况进行纠正。但是,必须要注意,由实体监督转向程序监督,会不会引起法律监督权的弱化?我们认为,为了避免法律监督权的弱化,需要赋予检察建议或监督意见合法的效力以及不履行监督建议和检察建议的后果。在价值取向上,回归法律监督权属于程序性权力的基本定位,由强调实体判断的权威性转变为强调程序启动的权威性,即法律监督活动的意义在于法律监督意见或建议能够启动相关的司法救济或矫正程序,能够引起被监督单位或人员的充分重视。另一方面,因为程序面也会涉及到利益的制衡,法律监督不能赋予被监督机关过度的举证责任,否则就会影响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日常工作和职能发挥。
三、结语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非对法律本身的监督,它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必须依法监督。正如我国学者田宏杰所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非一般监督,而是以诉讼活动为时空范围,在诉讼活动中开展监督,行使检察权。故而,法律监督活动的开展亦即检察权的行使,不仅要遵守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而且必须按照三大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定程序进行。由此得出法律监督的限度命题的根本所在,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法律本身。虽然法律监督有时候也会体现执政党倾向,但是有范围和限度,法律监督实施执政党的某些决策和主张是“隐蔽”的,受到具体案件有关客观事实的制约,受到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制约。对法律监督而言,监督是手段,法律的公正实施才是目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监督权只是一种辅助性、保障性的权力,权力依法正确行使既是监督权的目标,也是监督权的限度。
[1]储槐植.刑法契约化[J].中外法学,2009(6).
[2]梁景明.论法律监督的二重性——基于法治和政治二场域的讨论[J].法学杂志,2008(1).
[3]甄贞等.法律监督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