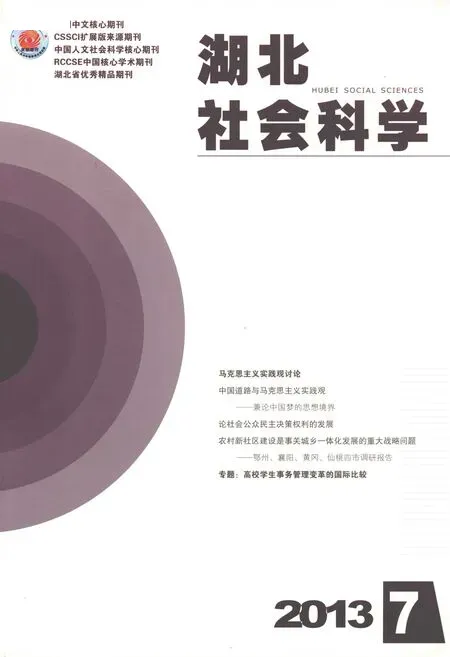南唐“清丽”诗风探析
2013-04-11郭倩
郭倩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南唐“清丽”诗风探析
郭倩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清丽”是南唐诗歌最主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它在诗作中具体表现为细微之美、单纯之美、清净之美和写实之美。这种诗风的形成与南唐诗人们缘情而求实的创作观念密不可分,也和他们清醒而脆弱的心态、雕琢而不失自然的创作习惯有很大关系。
南唐诗;清丽;表现;成因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仍,诗歌创作也相对走进了一个低谷。但正如邱仰文在《五代诗话》序中所言,五代诗歌“盖李唐之殿,赵宋先路,风流依依未泯也。”特别是政局稳定、经济发达的南唐,包括中原在内广大地区的诗人文士纷纷集中于此,与江南本地诗人交往酬唱,其诗作亦因此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审美特质,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清丽”诗风。
“清丽”是传统诗歌审美观的一个重要概念。“清”含有清爽美好、清新脱俗的意思,用以指诗歌审美,则相对于繁饰缛丽、鄙俚浅俗、幽深峭奥而言,一般指诗歌语言清新自然、不落尘俗却又流畅可读。如明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四中指出:“清者,超凡脱俗之谓。”[1](p185)而所谓“丽”,本用以指诗赋的辞采、形式之美,如钟嵘《诗品》卷一称谢灵运诗“丽曲新声,络绎奔发”。[2](p160)而自刘勰《文心雕龙》始,“丽”与“雅”往往互为表里,成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之一:“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3](p136)而“清”、“丽”结合,则有时成为对诗歌艺术的高度赞美,如苏轼《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云:“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4](p2212)
在南唐诗人中,“清词丽句”一直是许多诗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五代诗话》卷三载孟宾于为李中《碧云集》所作之序云:“今官淦阳宰陇西李中,字有中,缘情入妙,丽则可知,出示全编,备多奇句。”[5](p153)而南唐诗坛领导人物之一的徐铉,在《答左偃处士书》一文中也称赞左偃“负磊落之气,畜清丽之才。”[6](p156)而在他们的实际创作中,清丽可人的作品也随处可见。
一、南唐诗清丽之美的具体表现
(一)细微之美。
所谓细微之美,即南唐诗人多关注细微意象、关注细节之美。盛唐以后,山岳、长空、川泽之类的宏大意象逐渐退出诗人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具体而微的意象类型,其中尤以花草意象最为突出。如李建勋,南唐烈祖时即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宗时又拜司空、司徒,赐号中山公,地位尊崇。但检视《全唐诗》所载李建勋诗84首,涉及花草意象的作品即高达52首,占六成有余。其中单写“惜花”、“落花”的诗歌就有9首之多。而南唐存诗最多的诗人之一李中,涉及花草意象的诗歌也多达150余首,占比约五成,其它存诗较多的诗人如王贞白、成彦雄、伍乔、沈彬诸人亦大率类此,真可谓无花不成诗了。
对细微事物的喜爱不仅是南唐诗人个体的审美偏好,还是集体的一种审美追求,特别是在集会分题、应制奉和等情形下创制的诗歌更能体现这一特点。以徐铉为例,徐铉是南唐台阁诗人的核心成员,与地方官员、隐逸士人也多有交往,其存诗中分题、应制类诗歌特多。检索徐铉诗歌,题为“赋得”的诗作有七首,其诗题大多为“彩燕”、“秋江晚照”、“归雁”、“风光草际浮”之类。其中“风光草际浮”出自谢朓《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谢诗正以清词丽句和山水意象的清新秀逸著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作者们的审美情趣。而他的应制奉和诗如《柳枝词十首》、《奉和御制茱萸》、《春雪应制》、《北苑侍宴杂咏》等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组诗《北苑侍宴杂咏》,其《松》诗句如“细韵风中远,寒青雪后浓”、《水》诗句如“碧草垂低岸,东风起细波”、《菊》诗句如“细丽披金彩,氤氲散远馨”等,都体现了诗人对日常景物尤其是自然意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诠释。同时,这些意象的分布密度也相对较小,一个句子中一般只有1-2个中心意象,画面就显得相对疏朗。再加上南唐诗人在描写景物的同时又多杂以平易浅近的叙述,这就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境界不大但却清新自然、刻画入微的画面。
(二)单纯之美。
所谓单纯之美,即意象运用上的单纯化。陈植锷曾将诗歌意象分为描述性、比喻性、象征性三大类,其中比喻性意象指的是“以此一物拟指他一物者”,象征性意象指的是“以某一特定的物象暗示人生之某一事实者”,而描述性意象则“既不是用来比喻什么,也无关习惯型的象征意义的语词,而作为诗歌整体形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出现)”。[7](p140)从这个角度考察南唐诗歌中意象的运用,我们不难发现,南唐诗人运用最多的当属描述性意象,即意象只以其直指的含义呈现审美价值。如此,意象的含义就变得十分单纯而别无所指。我们不妨来看一组酬赠诗:
咫尺东溪路,年来偶访迟。泉声迷夜雨,花片落空枝。石径逢僧出,山床见鹤移。贫斋有琴酒,曾许月圆期。(孟贯《酬东溪史处士》)
致主嘉谋尚未伸,慨然深志与谁论。唤回古意琴开匣,陶出真情酒满樽。明月过溪吟钓艇,落花堆席睡僧轩。九重梦卜时终在,莫向深云独闭门。(李中《赠史虚白》)
这四首诗的赠寄对象史虚白本是江北士人,与韩熙载归江南却无心仕途,后隐居庐山。四首诗都描绘了史虚白的隐居生活,诗中意象绝大多数都属于典型的描述性意象,如东溪、泉声、夜雨、花片、石径、鹤、钓艇等,其用意都只在配合史虚白的隐士身份,描写或想象其隐居生活,几乎不用典故,也并无其它深意。
而即使是在运用其它类型意象时,南唐诗人也往往并不把它的象征意蕴作为重点来展现,意象固有的象征意义被有意淡化。如咏菊诗:
忆共庭兰倚砌栽,柔条轻吹独依隈。自知佳节终堪赏,为惜流光未忍开。采撷也须盈掌握,馨香还解满尊罍。今朝旬假犹无事,更好登临泛一杯。(徐铉《和张少监晚菊》)
簇簇竟相鲜,一枝开几番。味甘资麹糵,香好胜兰荪。古道风摇远,荒篱露压繁。盈筐时采得,服饵近知门。(李建勋《采菊》)
在两位诗人笔下,菊花已经纯粹成为士大夫用以佐酒赏玩、标榜风雅的对象,他们看中的多是菊花之形(色、香),而非菊花的内在精神与风骨。其它如咏竹、咏松等的作品,也大都如此。这些古典诗歌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本有其固有的文化含义,传达着传统士大夫的高洁情操,但在南唐诗歌里,这些意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脱去了崇高沉重的意义,它们大多不再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出现,而弱化为单纯的审美对象,或者仅仅只是一个标签、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阅读这类诗歌,读者往往不需要有太多的思索和知识,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却也能自然领略诗人为我们展现的清丽之美。
(三)清净之美。
所谓清净之美,即色彩运用更加自然和谐,呈现出清净多彩的画面特征。通过对南唐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徐铉、李中、李建勋、王贞白、孟贯、成彦雄等人的写景作品的分析,南唐诗人不仅喜用颜色字,而且所选颜色字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据笔者统计,南唐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颜色字依次是“白”、“青”、“红”、“碧”、“绿”、“翠”、“紫”、“黄”。考虑到“青”、“碧”、“绿”、“翠”色彩相近,事实上“青”、“白”是南唐诗的主色调,间以“红”、“紫”、“黄”,形成了南唐诗景物画面较为独特的色彩格调。
自唐以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诗歌与绘画视为同根同源的两个艺术门类。从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开始,诗歌和绘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提到南唐诗歌的色彩格调,就不能不提到绘画史上以南唐山水画为代表的江南画,其基本色调与风格,正是南唐诗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青白为主、略带清淡颜色的样貌。米芾《画史》载:“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髙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8](p6)董源是南唐画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其画风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平淡天真”。所谓“平淡天真”,指的就是一种简雅自然的风貌,与南唐诗歌中描绘的山水景色的审美特征如出一辙。而关于南唐花鸟画的另一名手徐熙,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里也有这样的记载:“……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9](p139)甚至后主李煜,《画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时纸上横卷花一轴,每时则自写论物更谢之意。文一篇,画一幅,字亦少时作,花清丽可爱。”[8](p16)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窥见,南唐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清丽淡雅的色彩格调,实际上与南唐君臣具有浓郁士大夫情调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诗风、画风的倾向是高度吻合的。
(四)写实之美。
南唐诗人的创作大多局限于自身生活内容,不仅想象之作阙如,连怀古题材也很少。以南唐诗歌留存数量最多的几位诗人为例,徐铉、李中的怀古作品仅各有两首,而李建勋则未曾创作此类作品。南唐定都金陵——山水形胜、六朝故都,本应是怀古题材富集的地方,但南唐诗人却极少发思古之幽情,这不能不说和他们对审美对象的选择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大多数南唐诗人较少将宏大景观写入诗歌,自然对历史、兴亡之类的“沉重”题材也敬而远之,吸引他们的大多是眼前秀美的青山秀水、池沼亭台,江南的秀美风光在南唐诗人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只要忠实描摹眼前之境,以南唐诗人丰富的学养和写作功底,不难传达出江南风景独特的神韵。这在南唐诗人群聚创作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春雪、侍宴、赏花等。据郑文宝《江表志·卷二》载:“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诏太弟以下登楼展燕,咸命赋诗,令中使就私第赐李建勋。建勋方会中书舍人徐铉、勤政殿学士张义方于浮亭,即时和进。元宗乃召建勋、铉、义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图有咏,徐铉为前后序,太弟以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炬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图成,无非绝笔。”[10](p137-138)
其中李璟诗云:
珠帘高卷莫轻遮,往往相逢隔岁华。春气昨朝飘律管,东风今日散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比,落势还同舞势斜。坐有宾朋尊有酒,可怜情味属侬家。
李建勋诗云:
纷纷忽降当元会,着物轻眀似月华。狂洒玉池初放仗,密沾宫树未妨花。迥封双阙千寻峭,冷压南山万仞斜。宁意晩来中使出,御题宣赐老僧家。
徐铉诗云:
一宿东林正气加,便随仙仗放春华。散飘白兽难分影,轻缀青旗始见花。落砌更依宫舞转,入楼偏向御衣斜。严徐幸待金门诏,愿布尧年贺万家。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看到南唐君臣的创作不论是从绘画的题材,还是从诗歌的题材、意象来看,都与眼前之境别无二致,展现出一种“写实”的趣味——善于从眼前的实景展开联想、善于观察和发现细节之美,据实而又不拘泥于实,虽然创造性欠缺,却也颇有一番情味。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创作习惯和审美趣味,生活在江南四季如春的美妙风景中的南唐诗人们,充斥笔下的就大多是“燕飞犹个个,花落已纷纷”(徐铉《春分日》)、“斜日苇汀凝立处,远波微飏翠如苔”(李建勋《离阙下日感恩》)、“鸟啼窗树晓,梦断碧烟残”(李中《春闺辞二首》)之类的清词丽句了。
二、南唐“清丽”诗风的成因
(一)“缘情”而求实的创作观念。
南唐君臣累世好儒,不论是为政之道还是文学观念都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但在诗歌的实际创作中却并非如此。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徐铉,虽然他也曾多次声称“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诗之官、陈诗之职,物情上达,王泽下流”(《成氏诗集序》)、[6](p146)“臣闻尧尚文思,《书》有永言之目,汉崇儒学,史称好道之名,所以泽及四海,化成天下”(《御制春雪诗序》),[6](p140)认为诗歌的功用主要在于察民情、广王泽,但同时徐铉也不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刚刚经历了唐末剧烈社会动荡的诗人,往往会把目光投向更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徐铉在高倡儒家传统诗论的同时,也不断地慨叹这一传统的没落,其《邓生诗序》云“故君子有志于道,无位于时,不得伸于事业,乃发而为诗咏”,[6](p182)其《成氏诗集序》中也曾提到“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性情,黼藻其身,非茍而已矣”。[6](p146)虽然理想中的诗歌的确应该“察民情、广王泽”,但时代既然已经无法让“斯道”推行,诗歌就只剩下吟咏个人情怀的功能了。因此,徐铉诗论虽然多有矛盾之处,但其内核却可以鲜明地体现为一“情”字:“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或情之深、思之远,郁积乎中,不可以言尽者,则发为诗”(《萧庶子诗序》),[6](p145)“成天下之务者,存乎事业;通万物之情者,在乎文辞”(《翰林学士江简公集序》)。[6](p144)诗歌功能论上的理想主义和诗歌创作论中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南唐诗人独特的诗歌风貌。
当然,这里的“现实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南唐诗人们尽管对现实有着深深的关注,也从不缺乏忧患意识,但却极少创作直接反映唐末五代动荡社会的作品,所谓“美刺”、“讽谏”的诗歌功能也基本上没有体现。他们笔下的现实,仅是“钟山楼月,登临牵望阙之怀;北固江春,眺听极朝宗之思。赏物华而颂王泽,览穑事而劝农功,乐清夜而宴嘉宾,感边尘而悯行役”(《文献太子诗集序》),[6](p144)早已萎缩成了打着鲜明个人身份烙印的士大夫生活的写照。因此,南唐诗人相对狭窄的生活实际和生活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太可能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中去,而是对身边的人情冷暖、仕途变迁、酬唱交游、自然物象倍加关注,从而使诗歌内容进一步细微化、单纯化,奠定了清丽诗风的基础。
(二)清醒而脆弱的心态。
虽然南唐地区经济发达、生活优裕,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这毕竟只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尽管其国力也曾一度飞速发展、具备了与中原政权一争高下的实力,但由于君臣盲目自信、妄起战端,南唐在与吴、闽进行了几场大战之后便一蹶不振。与之相反,中原政权在几经变乱之后已逐渐安定,实力不断壮大。虽然这一切尚未直接威胁士大夫的生存,但也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地方。生活的暂时无忧和隐然逼近的战争威胁让身处江南秀美风景中的南唐士大夫深深领悟了生命的脆弱和美丽。正由于这个原因,南唐诗人们毫不吝惜地把目光投注在自然界中一些细小纤柔的事物上,如动物类中的蝉、蜂、蝶、莺,植物类中的柳、桑和桃花、莲等易于凋零的花,使诗歌呈现出前文所述的典型的“清丽”特质:
惜花无计又花残,独绕芳丛不忍看。暖艳动随莺翅落,冷香愁杂燕泥干。绿珠倚槛魂初散,巫峡归云梦又阑。忍把一尊重命乐,送春招客亦何欢。(李建勋《落花》)
所思何在杳难寻,路远山长水复深。衰草满庭空伫立,清风吹袂更长吟。忘情好醉青田酒,寄恨宜调绿绮琴。落日鲜云偏聚散,可能知我独伤心。(徐铉《赋得有所思》)
当然,单从这些诗歌的个体上看,南唐诗歌似乎呈现出一种浓重的悲剧色彩,展现了诗人们面对人生困境时充满无奈的脆弱心态,但毕竟由于士大夫身份和儒家传统诗教的制约,再加上变乱已非一朝一夕,大多数诗人也早已惯看离合,因此就南唐诗歌整体而言,诗人们很少直接发出愁苦的咏叹,而大多是通过对相关意象的展示和描述含蓄地流露自己的情感,在充分抒情的前提下又展现出清醒和节制的一面,从而使诗歌的审美风貌最终走向清丽而不是悲苦寒涩。
(三)雕琢而不失自然的创作习惯。
大多数南唐诗人十分注重诗歌语言的雕琢与构思。他们既然已经无心(或者也无胸怀)去关注深广的社会现实,作为他们诗歌素材主要来源的士大夫生活也无甚新奇可言,那么诗歌创作的着力之处,就从内容的选择转移到了字句的斟酌之上——“唯奋藻而摛华,则缘情而致意”(《文献太子诗集序》),[6](p144)以清词丽句书写着自己对生活的点滴体悟。很多南唐诗人对诗歌语言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执着(苦吟),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李中。
李中长期在地方为官,过着“蓝袍竹简佐琴堂,县僻人稀觉日长”(李中《赠永真杜翱少府》)的生活,但他不以为意,因为有诗作伴:“爱静不嫌官况冷,苦吟从听鬓毛苍”(李中《赠永真杜翱少府》)。日常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觞一咏,都可以引发作者苦吟的兴致:“无奈诗魔旦夕生,更堪芳草满长汀”(李中《暮春吟怀寄姚端先辈》),而同时,有着共同兴致的诗友在诗篇往还、酬往唱答之际,也助长了“苦吟”的习惯,例如李中与同是朝廷诗人的韩熙载、沈彬等有“丹墀朝退后,静院即冥搜”(李中《献中书韩舍人》)、“老去诗魔在,春来酒病深”(李中《赠致仕沈彬郎中》)的诗句,与山野隐士则有“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李中《宿青溪米处士幽居》)的雅兴;与高蹈出尘的僧侣,也有“虎溪久驻灵踪,禅外诗魔尚浓”(李中《赠东林白大师》)的感叹。虽然“苦吟”耗时耗神,过早地让白发爬上了双鬓:“此时吟苦君知否,双鬓从他有二毛”(李中《秋江夜泊寄刘钧正字》),但若偶有所获,便又忻然不已,“吾师惠佳句,胜得楚金归”(李中《依韵酬智谦上人见寄》)。
当然,南唐诗人的“苦吟”为什么不仅没有带来贾岛式的僻涩,反而推动了“清丽”诗风的呈现呢?对此,徐铉的诗论中有很好的例子:“夫机神肇于天性,感发由于自然……若乃简练调畅,则高视千古,神气淳薄,则存乎其人,亦何必于苦调为高奇,以背俗为雅正者也”(《文献太子诗集序》),[6](p143)“精诚中感,靡由于外奖,英华挺发,校自于天成”(《萧庶子诗序》)。[6](p145)在这些论述中,徐铉一再强调诗歌创作须“自于天成”,字斟句酌并不是为了一争奇诡,而是力求以最恰当的遣词用字达到“简练调畅”、自然清丽的效果,出于人工而近于自然,使诗歌创作真正成为诗人的一种享受,这一点与前代以苦吟著称的诗人如李贺、贾岛、孟郊以及同时代的卢延让等是有很大区别的。
综上,南唐的清丽诗风虽然仍以“缘情”为其内核,却大不同于魏晋时代“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观。陆机所谓“缘情”,是为对“言志”、“载道”等诗歌传统功能的反动,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三十一中就曾提出:“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11](p3)在他看来,“缘情”将直接导致诗歌内容局限于“闺房儿女子之思”,审美上趋于浮艳。但南唐诗人在“缘情”而作的同时,却并没有堕入淫词丽藻的“歧途”,而是以其文思之清与文辞之丽,创作出了一首首或许境界不大却独具一格的诗篇,清而不枯、丽而不冶,上承唐之遗韵、下启宋之先声,使南唐诗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散发着自己独有的魅力。
[1][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梁]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梁]刘勰.文心雕龙注(上)[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70[M].孔凡礼,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清]王士禛.五代诗话[M].郑方坤,删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宋]徐铉.骑省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108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陈植锷.诗歌意象论——微观诗史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宋]米芾.画史[A].文渊阁四库全书(81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宋]沈括.梦溪笔谈[M].长沙:岳麓书社,1998.
[10][宋]郑文宝.江表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46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清]朱彝尊.曝书亭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131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邓年
I206.2
:A
:1003-8477(2013)07-0127-03
郭倩(1975—),女,硕士,集美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