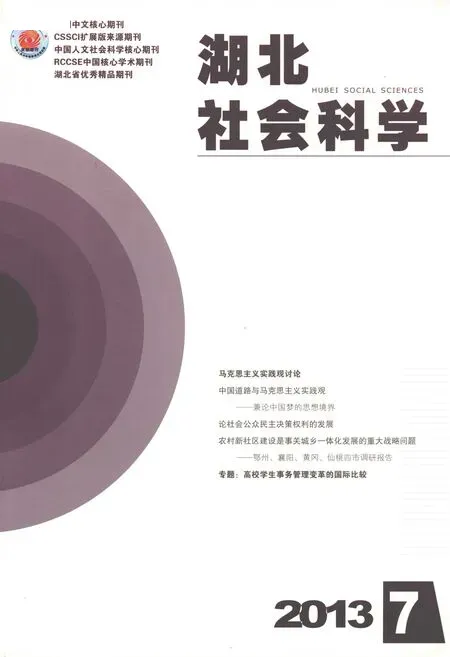从晚清到“五四”:论游记文学中的世界图式变迁
2013-04-11李岚
李岚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人文视野历史·文化
从晚清到“五四”:论游记文学中的世界图式变迁
李岚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从晚清到“五四”前后,大量的域外游记在散文领域中涌现,成为文学领域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时期的游记显影了中国社会观念变革之心路。它是传统中国人从自我封闭状态逐步展开“看世界”旅程的史料,并不断促进着社会观念的觉醒。游记带来了视野的开阔和视角的变更,从观念上进行着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反映和改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一时代文化格局的建构和变迁。通过对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游记文学的历史线索梳理,考察其观念变更的内在逻辑,并评价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晚清到“五四”;游记;“世界景观”;异域想象;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社会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中士人学子远游西方认识世界,或探索新知、求学避祸,或奉命出使、察考政俗;其间所历,以日记或游记的方式记录下来,结集成篇,一时蔚成风气。仅清末王锡祺辑录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便收录清代地理著作1420种,其中游记有六百多篇;而到了“五四”前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散文领域内“打头的是海内外的旅行记和游记”。[1](p10)据贾鸿雁的《中国游记文献研究》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游记集共608种,其中民国时期创作游记集和编选游记集570种,包括国内游记和游记集333种,域外226种,余者兼收中外。这还不包括发表在报刊上的游记和未入专集出版的大量游记。
这一时期的游记关注社会生活,长以景观写心,眼中笔下,情景互见。从晚清到“五四”的游记文学画廊,一路看来如移步换景,其情其状,显影了中国社会观念变革之心路。它是传统中国人从自我封闭状态逐步展开“看世界”旅程的史料,并不断促进着社会观念的觉醒。游记带来了视野的开阔和视角的变更,从观念上进行着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反映和改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一时代文化格局的建构和变迁。本文拟通过对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游记文学的历史线索梳理,考察其观念变更的内在逻辑,并评价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晚清游记的文化视野扩张——从“天下景观”到“世界景观”
晚清域外游记之初,多记载“猎奇”,以描述“异域”风光和西方近代科技为主。斌椿在1866年的《乘槎笔记》中多次提到现代化交通工具,称自行车为“木牛流马”,火车如“奔马”,电梯“各法奇巧,匪夷所思”;曾与他同行的张德彝出国多次,从1866年至1878年的游记皆名《述奇》。对先进“器物”的惊奇是晚期每个出国的中国人都会有的反应,即便是有远见卓识的王韬也未能免,“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车,虽都中往来,无不赖轮车之迅便。”[2](p112-113)只是,王韬、郭嵩焘等开明派人士的游记不仅关注这些“器物”,他们还开始观察外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在王韬1867年所作《漫游随录》、郭嵩焘1876年所作《使西纪程》均有记载,欧洲诸国繁华昌盛,“天朝上国”在洋人眼中不过是“半开化”国家,他们感到了中华文化的危机。关注焦点从“器物”到“体制”的转移,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现代性意识萌芽的表现。
最先出现在晚清游记中的西方世界,是一个“理想世界”:繁华、新鲜、先进、富有;这不能不使“外来注视者”反思的文化身份和国家前途问题;他们对此通常有种微妙的心态,即极力强调中国悠久的文化,不论怎样钦佩西方的科技、艺术和体制,但都认为“文章礼乐”远不如中华。面对现实的触动,对自身文化反思的程度可以见出胸襟的深浅、见识的高下:王韬欣赏西方的科技,同样出国游历的保守派刘锡鸿,则没有王韬的眼光,他认为火车不能利国利民,而且铁轨会损坏他人田地坟茔,必将为民众反抗,属于“奇技淫巧”。他在游记中说,工匠的事情,文人不必劳心,关心技巧不是正途,“非谓用功于身心,反先推求夫一器一技之巧也。一技一器,于正心修身奚与?”。[3](p28)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国家政策长期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蔑称为“奇技淫巧”,“奇技淫巧”是中国人在西方最先被震撼的见闻,却被依然轻视,刘锡鸿的观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其认知视野正是长期农业社会和专制制度中形成的“天下景观”。
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一种“天朝型世界观”,中国以外,莫过夷狄戎蛮,“异域”一词本身就意味着边缘、差异和特殊。我目即中心,目极即天下,天下即世界,是一种“我族中心”的思维模式。晚清国人在“睁眼看世界”之后对天朝型世界观的依然坚持,既是一种对既有文化优势心态的延迟,又是传统社会秩序对西方意识入侵作出的应急反应。同一时期的郭嵩焘由于其公使身份,当他的游记《使西纪程》直言英国“政教修明、乃文明古国”时,换来朝野上下骂声一片,称其“事鬼”,因为他的观点是对人们心中的天朝世界观的极大冒犯。
但是,总有变化在行旅间、游记中出现,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早年王韬是坚持科技是“奇技淫巧”的,出国游历后,他在《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中分别改称“奇迹瑰巧”和“奇技异巧”了,一个词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王韬个人对科技看法的转变,更反映了社会观念中价值系统的逐渐转变;我国第一个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并获博士学位的薛福成在1890年的一篇日记里写道,他本不相信郭嵩焘对西洋政教民风的赞美,询问陈兰彬、黎庶昌等人,都说郭嵩焘之言不假,他亲自赴欧洲后,“始信侍郎之说”。到了20世纪初,在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两部游记中,当繁华已熟视无睹,西方“理想世界”消失了,真实的世界呈现出来,欧美也有贫病污秽,绝不是“豪富逸乐若神仙”,梁启超更反思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足,照搬到中国必然无益。
从斌椿的《乘槎笔记》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相隔近半个世纪的游记的变化所展示是华夏民族心理在新的时代状况下所呈现出的变化,是反映社会观念变迁的一系列文字景观。晚清域外游记通过集体行为初步构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和对中国社会的重塑。
二、“五四”前后游记的视角增殖——“世界景观”的多维度
1912年以来,中国人前往外国留学的风潮日盛,单纯倾听海客谈瀛洲的时代过去了。在“五四”前后的游记里,人们比较自觉地反思中西方文化差异,动荡的世界局势引发了行旅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思考,思考社会改革之路,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欧洲、1917年的十月革命、新兴国家苏联,一连串的世界的变化让中国人困惑。
经过一战,繁荣的欧洲工业社会满目疮痍,从晚清中国行旅者开始建立起来的欧洲集体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不再异化,一些驻外记者和行旅者都写了不少关于战时欧洲的游记在国内发表,例如徐钟佩的《伦敦和我》、《英伦归来》,王云五的《战时英国》等,在游记中不乏对战后欧洲“山穷水尽”的描写。
对于日本,态度比较复杂,主要是亚洲相近文化态度使然。有的游记态度友善亲和,比如周作人的作品;也有如郁达夫在20年代所写的《归航》中那样激烈,称之为“强暴的小国”、“世界一等强国”、“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并透露出《沉沦》中那种颓废、愤懑、感伤的个人情绪;还有的游记呈现了贫弱大国对富强小国的鄙夷态度,如郭沫若在1922年所写的《今津纪游》中说道:“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之不好洁净,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就好象是世界第一。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所有的侧街陋巷,其不洁净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4](p308)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异域的地位依然不高,受到歧视的事情在此时乃至以后很多年的域外游记中比比皆是。
总的来说,此时的域外游记反映出三种与以往不同的倾向,这三种倾向虽然是游记中行旅者的个人观点,但是真实地体现了国内思潮的纷纭涌动。
第一种倾向是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申,用西方的思维方法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作品就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世界局势动摇了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体现的对欧美文明的信心,他自筹经费,与几位朋友到欧洲游历。欧洲的现状没有给梁启超太多的政治上的启迪,却给他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机会。“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5](p7),欧洲人中“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5](p15)所以他认为要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地位,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东方文化是精神的,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的中西融合的文化互补观。[5](p35)《欧游心影录》在国内发表后立即推动了当时已进行了约10年的有关东西文化优劣的争论。
第二种倾向是向东方同类文化取经,即学习日本的一些发展方式。周作人在1919年7月访问了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基地新村,非常欣赏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把新村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他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新村的生活方式和运作模式,“深信那新村的精神决无错误”,“对于新村运动,为中国的一部分人类计,更是全心赞成。”[6]周作人的这篇游记详尽写实,坦言日本新村实验的现状和不足,但他声明新村的前景可观,主张用新村这样平和的方法代替暴力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在这次访问之前,周作人已经在国内大力鼓吹新村模式,他的一系列文章引起巨大的反响,使新村主义有了一批追随者。
第三种倾向是人们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趣。苏联的成立无疑给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社会模式,很多人前往苏联旅行和考察,尤其是探索国家民族出路的知识分子,苏联的社会面貌比山水风光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1920年,瞿秋白被《晨报》聘为记者,到苏联访问考察,写下了《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两部游记,在《赤都心史》里,瞿秋白考察了俄国革命后的经济状况,描绘了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全国集权状况,对苏联临时政策的优缺点能够客观的分析。总的来说,瞿秋白在游记中表达的是一种对苏联的向往和礼拜,从某种角度上,这时的苏联代替了19世纪欧洲社会想象,成为一个新的期待点。
但是也有人并不欣赏苏联模式。1925年,徐志摩到苏联游历,写作了游记《欧游漫录》,字里行间多有对苏联的惧怕,“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文明的骸骨间,是人类鲜艳的血肉间”,整个社会没有“新文化”、“旧文化”可言。[7](p258)与徐志摩文化渊源相近的胡适与徐志摩的观点又不同,他在1926年途经莫斯科后感到,“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所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8](p74-75)他们感受的相左主要是因为各自所取的观看立场和角度有所不同。
三、“交互认知”渠道:游记的异域想象与“自我”真相
从晚清到“五四”,使游记这种文体参与到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和认知过程中的渠道,是人们在游记中对异域想象的营造与“自我”真相的揭示。游记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改变的过程和过程中的心态,一方面在景观和主体之间进行间接的沟通和互动。前文已经论述了游记里所呈现的民族和世界观念,这些观念是经过行旅者和游记以及作为对象的现实本身多元共生而形成的结果,三个来源缺一不可,共同产生了中国人的异域想象。对于游记的阅读者而言,事实只是被个人陈述的,是始终缺席的,通过游记的叙述和通过行旅者的凝视一样,都是在塑造他者形象,就是进行自我确认。异域想象与“自我”真相之间有一个镜子式的映照关系,中国人的世界、民族、价值等观念的改变都和这个映照有关,所以,游记里没有直接出现的“自我”真相构成了问题的另一面,它表现着行旅者以及当时中国人的自己的理解和欲求。
在晚清的异域行旅之初,以“蛮夷”为主的西方想象尚是社会群体意识的一部分;到20世纪初,行旅者则抱有“西方科技文化先进”之期待视野。当身处其境时,期待视野会有所动摇,但是对西方的美化仍是“五四”前后游记的主流态度。游记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集体想象物对作者的影响,但同时它又是新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缔造者。
让·马克·莫哈认为,异国形象有意识形态式的和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的异国形象是按照自己的社会模式、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把形塑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投射到作为他者的对象上,通过消解、同化他者让其适应本社会的价值观;乌托邦式的异国形象偏于相异性和离心性,是用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的看法塑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否定形塑者社会的价值观。[9]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心态是把西方作为他者的,用中华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对西方文化进行消解,所以被称为是意识形态式的。“世界观”就是一种综合表现,这种意识形态式的西方形象在闭塞的中国社会中成为自在的和独立的,泛化为群像,代替了现实的西方,成为闭塞环境里的人们的唯一经验,据此,对于“天朝型世界观”在晚清的顽固和“红毛鬼”一类的套话的长盛不衰,就很容易理解了。
西方的“奇技瑰巧”让行旅者对西方的印象有了乌托邦式的倾向。王韬在《漫游随录》里记录他看到西方戏剧,“视之甚审,目眩神移,叹未曾有”,评西方绘画“技也而进乎神矣。”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中称“意人之尊艺术至矣,宜其画学之冠大地也”,“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王韬和经世致用的洋务派诸君在接触到国外政体、军事、经济建设、礼仪之后都颇为称赞,他们大多希望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改革。这些由衷的称赞和中国社会的群体价值观是相反的,否定了对西方的传统想象,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对中国的“天下”、“中心”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呈现出莫哈认为的乌托邦的形象倾向。这些对外国的描绘构成一个共同的印象:奇异、发达、文明、开化,这个印象在众多的游记中或深或浅、异曲同工,它是晚清中国人对外国文明的统一认识,构成了一系列“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中国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同一性或相异性的解释。
从19世纪开始,人们通过近现代交通工具成规模地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时,异域的异质性成分大量凸现出来,排拒性的分化体验成为现代行旅体验的主要内容,我族与异族、我国与异国,成为行旅观看的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两端,“天下”景观被“世界”景观所代替,两者间差异的突出使得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分界更加清晰,从而有利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实际上,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在域外思潮直接涌入中国并发生影响之前,域外游记扮演了传递外界信息和引发积极思考的最有效的媒介角色,当这些游记在中国传播之后,其中对外域的描写就成为晚清最初的现代国家观念,他们对东西方异域世界的描述在国内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作为信息媒介传递了一系列现代国家形象。而在认识“夷狄”的同时,中国也有了初步对自己的反观。这种反观是完全不同于清末“天朝上国”的观念的,它具备了一定的反思价值,不但意味着崭新的晚清世界观念,更直接促进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现代想象和向往。
1912年以后的中国不仅接受了西方文明,更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时期,国内对异域的态度是比较一致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共同完成了这个发达、文明、开化的集体想象物的塑造,并且不再感到奇异,文化心态平和了很多。人们大量翻译外国作品,在文学、哲学、政治等各个方面被西方渗透,每当有人主张复兴传统文化时,都会引起一定规模的论战,异域的社会模式和政治理念,总会有人热衷地试验和宣传。可见从社会范围而言,乌托邦式的西方形象占了主流地位,文明、开化、发达是现代工业西方的形象特征,落后、闭塞、愚昧是农业中国的形象特征,西学直接性地压倒中学。当然,有一些游记所直接反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乌托邦式的西方形象,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它的文化、体制成为另一个代表先进的想象物,和原有的西方形象并不冲突,因为,同样是中国人在向异域寻求一种新文明的源泉,用异域的话语方式去侧重表现异域的特征,以便颠覆自身文化中假定有害的方面。
相对于异域想象的变化,游记里中国的“自我真相”比较稳定。从晚清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但是还要竭力维护,在多元跨国的文化语境中发生了最直接的现代经验,如何用这种经验去进行对近代中国的回顾和文化想象呢?文学和艺术就成为其中赖以支撑的信念之一。然而域外游记对西洋图景的新鲜描述已经让他们成为异端。其实作为行旅者,文化身份始终与异域文化是相对的,他们在异域场景的凝视下,更容易被证实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中华身份被确认的同时,进一步被确认的是落后于世界步伐的共同体文化,域外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典范和契机,而他们本人就成为最初的先锋者,例如刘锡鸿见识短浅,但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政俗、海防、议院的种种好处。此时他们自我意识里的矛盾与国内态度的矛盾相交织,呈现的是文化转型期的必然态度。
结语
概言之,晚清到“五四”的游记文学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显示着近现代中国社会观念和文化精神的演进轨迹。游记中的情与景、对象与视角、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种种嬗变,成为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投影,呈现出这个转型时期的人们认知图式的转换、情感方式的更迭和文化思考的深化;同时,现代行旅体验也推动着传统文学观念和技法上的更新,从内容和形式上带来了全新的期待视野。晚清以来的游记文学作为伽达默尔意义上的“历史流传物”,在中国和异域之间相互传播,接受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的注视、阐释和“改写”,作为“视界交融”的媒介发挥着文化参照物的作用,对自我认知和了解他者具有直接的意义;它在记录社会观念变化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观念变化,并为文学史和思想观念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研究维度。
[1]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
[2][清]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清]刘锡鸿.英轺日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C].上海:中华书局,1936.
[6]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J].新潮.1919,2,(1).
[7]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3卷[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
[8]胡适.胡适文存:卷一[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9][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周刚
K252
:A
:1003-8477(2013)07-0096-04
李岚(1979—),女,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0q1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