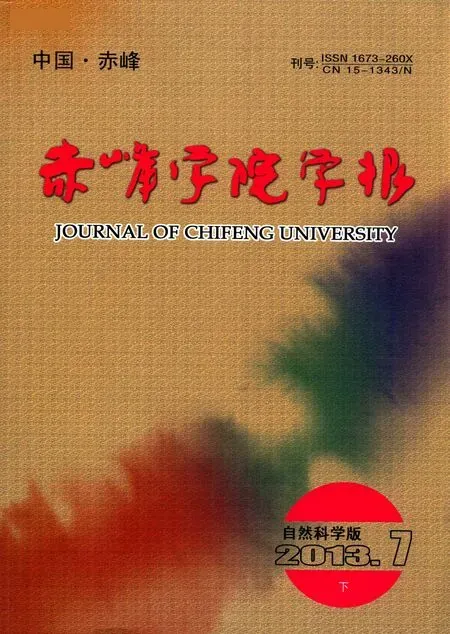文化变迁与蒙古族游牧体育社会性格的生成
2013-04-02高美琼
高美琼,李 洋
(1.内蒙古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2.赤峰学院 体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品过浩繁的中华历史,人们常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江南出才子”,文化生态学给予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全新解读,在交通工具与信息相对闭塞的时期,生态环境决定力对民族成长来说,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南方与北方差异较大,无论是疆域版图的勾勒,还是文化版图的描绘,都足以产生鲜明各异的区域性特点.北方游牧民族则是文化版图中风格迥异的一块,也是极具北方文化特征的一景,尤其蒙古族体育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重要“活态”文化的一支,更加体现出马背上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理念,生存方式.
毋庸质疑,民间是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最大空间,同时,也是传承蒙古族体育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也充分反映了蒙古族人的一种北方的生活态度.从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的趋势来看,生态环境、地缘特征、民族特质等方面与民族对项目的选择上有着较大的关系.蒙古族地区的人们共同的民族心理特质使得其在运动项目选择上更倾向于体现草原主人“阳刚”“激烈”“血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尤其是对区域性本土传统体育项目青睐.然而,面对现代信息化、全球化的冲击,随着各民族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休闲体育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空间,草原牧民——蒙古族已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定位的先民形象,而是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而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发明着一系列的传统.如何看待文化变迁下的游牧体育给予蒙古人带来的影响,则成为本研究的一个主题.通过对蒙古族群对游牧体育习得、认同,外化向内化的转向,纳入自己的行为体系,同时,也刻画在民族气质的诠释,来解读蒙古族游牧体育社会性格的形成.
1 解读蒙古汉子“搏克”的参与
蒙古族搏克是改革后的“蒙古式摔跤”,是一种更加贴近于生活的体育项目.激烈的身体对抗性是搏克项目的鲜明特点,吸引各族蒙古汉子积极的尝试和参与.极大的满足了参与者的潜在竞争欲望.不仅仅是体力、技术、战术的角逐,更重要的是精神意志、心理状态的碰撞.在身体接触的过程中,斗智斗勇,身体优势不是比赛致胜的决定性因素.对手不分等级,不管是体重,还是体轻,同场较量,一跤定胜负.在比赛过程中,级别低的选手顽强拼搏战胜高级别选手的比赛结果也有时发生,给比赛增添很多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各种级别的人都乐于参与.尤其是对失败者,也不会使其受到冷落,而是首先给予奖品,勉励其继续努力.
“民族性”[1]也是搏克这种项目被广大蒙古汉子喜爱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生活在农牧区的蒙古汉子,有着深厚的民族情节.少年或者成年后习得蒙古族摔跤,渐已成为蒙古族孩子成长必须经历的过程.搏克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成为蒙古族标志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悠扬的“乌日雅”(摔跤入场音乐),狮子舞步,布满铜钉的服饰,这些蒙古族的韵味都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印象.
搏克是一种非周期性复杂对抗性的体育健身项目.两人组合即可进行,对场地没有太多的限制.搏克技术性动作繁多,通过绊腿、抱腰、弓身等动作,引进落空,使对方身体失去平衡,从而获胜.能够提高各项身体素质,包括力量、灵敏、速度、耐力,特别对灵敏素质有很大提高.除此以外,对蒙古族勇敢个性的培养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2 蒙古汉子喜爱赛马的原因透析
赛马这项蒙古族传统体育运动与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族人民有着特殊的渊源.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生活中当然少不了马.世界许多名马系的祖先,无不追溯到亚洲的两大名马系,即蒙古马和阿拉伯马.蒙古马就是蒙古族数千年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曾驰骋欧亚两大洲,举世闻名.蒙古马是蒙古人最忠诚的朋友,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要求也是最低的.
蒙古族擅长育马,也精于骑术,早以被世人所熟知.解放后,速度赛马独立成项.同时,蒙古族更注重马的培育,即驯马.1996年,在中国马王杯争霸赛中,草原的蒙古族骑士们以优异的成绩夺得第一、第二、第三名,继续保持“中国马王”的称号——原哲里木盟骑手扎那获得首届“中国马王”称号以来,又一骑手那达木德再获“中国马王”称号.蒙古族传统赛马有速度赛马、走马、马术表演.速度赛马一直被人们所热衷.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速度赛马已逐渐成为草原蒙古族人民所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赛马是蒙古人与马的合并,是蒙古人“崇拜自然”的一个描写,是对大自然的对抗,也是个人“野蛮”精神的一种释放.马代表的不是马自身,而是兴趣、快乐、激情与雄性.
3 蒙古汉子对射艺的痴迷
射箭在草原地区有着久远的历史.射箭习俗在鲜卑、鸟桓、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各个时代一直沿袭.萧大亨关于古时期弓箭的描述时写到:“弓以桑榆为干,角取诸野牛黄羊,胶以鹿皮为之,体制长而弱,非若六钧三石之强也.矢以柳木为之,粗而大.镞以铁为之,有阔二寸或三四寸者,有似钉者,有似凿者,然阵中人不数矢,矢不虚发也.弦以皮条为之,粗而耐久也其弓弱,其矢强,彀元极满,至三二十步发之,辄洞甲贯胸,百步一失.[2]”蒙古人室内大多有弓箭挂在墙上,蒙古族从小就能接触到弓箭.至今在一些部落中,让少年引弓射箭仍是一种传统.大多数少年平时玩习时,也以引弓射箭为乐,比试远度、准确性甚至力量.
射箭项目不同于其他体育项目,诸如:网球、乒乓球、足球等.它不需要一个好的陪练或者队友的协同配合,一个人便可以完成.不需要有良好的技术功底,也能玩的淋漓尽致.自制一套射箭设备,对于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因为有大量的皮革可以利用.射箭是一种避免与对手近身接触,可以实现远程打击目标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胆怯型运动者的一种运动渴望.比赛过程中,上一环为下一环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每一环对于比赛成绩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使得比赛更加具有挑战性.
4 安代舞——蒙古族群体向往美好生活的表现
安代舞在我国少数民族舞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是一种豪放、粗犷,而且充满无限草原柔情的蒙古舞,也是科尔沁地区非常典型本土蒙古族体育项目的代表之一.安代舞源于科尔沁地区通辽市库伦旗,安代是蒙古语“抬头”、“站起”之意[3],据有关资料记载安代舞有30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安代舞是用来驱除灵魂附体,使病人苏醒,也就是用舞蹈来治病的一种表现手法.“通古期”原始部落多崇拜“萨满教”.由于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所在地域,长期受亚洲东邻和东北部宗教所影响,古代蒙古族同北方民族一样,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骏马、沙驼、雄鹰、鹿群、狐狸……被尊为神灵.萨满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蒙古族心理准则和行为规范.蒙古族的萨满教宣传“长生天”,称天为“腾格里”[4].宣扬:众生平等、无主仆、无高下,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在膜拜和祭祀祖先和大自然万物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舞蹈——这就是安代舞最初的雏形.安代舞的起源给这种项目本身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使得有着极强好奇心的青少年中蒙古汉子想要了解它,探究它.
事实上,舞蹈与体育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二者相互兼容.现在的安代舞已脱离了原始宗教的色彩,成为蒙古族以及其他民族日常生活的健身活动.2004年8月18日在库伦旗举行的“中国安代艺术之乡民族文化周”,组织参与安代舞健身操表演的有2000人之多,对安代舞的普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富于现代气息的安代舞,既有大幅度的跳跃、摆动,也有小幅度的滑步.“踏地为节”,口词为拍,配合甩巾.在灵敏、柔韧性、身体协调方面有着极大的锻炼,符合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蒙古人的身心需求.安代舞的运动过程中,蒙古群体以集体的方式表达着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健康、平安的祈祷.
5 布鲁、贵由赤项目对蒙古族个体品质的锤炼
布鲁是一种类似于田径类投掷的项目.通俗的讲,布鲁是一个弯木短棍,常用于放牧时来震慑狼、狐狸等动物对羊、牛群的威胁.布鲁,为蒙古语音译,即投掷的意思.布鲁是一种前段弯曲的短棍,投掷出去后棍体旋转飞行,可以远距离飞行,而且可以击打狼、獐狗、野兔等猎物.布鲁别名面其格、掏来棒子(“掏来”为蒙古语音译“兔子”).打布鲁也作为一种体育运动而出现在竞技场上,而布鲁也由过去放牧打猎的工具变成民间体育竞技投掷器材.但是,投布鲁的技术很难掌握.投掷布鲁的技术,对器械本身的研究和认识,只局限在个别家族或者个人的手中,限制了该项运动的向外发展.但是,大多数蒙古汉子在草间放牧时,仍不断练习,随身携带.在现代的牧区里,我们仍然能见到布鲁的使用.如“贵由赤”项目一样,对个体的意志品质的锻炼起着关键的功用.
“贵由赤”译成汉语就是“快行者”、“速跑者”之意.这项运动,既是活动量较大的体能锻炼,又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辍耕录·贵由赤》中提到:“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在大都,则自河西务起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一饼(锭),馀者赐缎匹有差.”也就是说,这项比赛有两条线路,一条是“东线”,由河西务(位于今天津市武清区)起跑,到皇城大内结束,全程约125里.另一条是“北线”,在元大都与元上都两个点同时进行,全长约180里,这两条比赛线路均比现代马拉松的42.195公里长出许多.从以上资料分析,超强的耐力,超长的距离,是这项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这项目运动的开展,来培养蒙古族群体坚忍不拔的社会个性,来适应社会文化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6 蒙古族游牧体育文化与个体性格的互应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提出“冲击——反应”理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说方式.蒙古族传统体育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全息缩影,不但是一种身体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身体的文化,对大自然生态热爱的一种理性诠释.西方体育引入,对蒙古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的排挤,使得大多数学者研究其传统体育的现代生存竞争下的发展方式.从深层次的分析,很大程度上蒙古族文化底蕴下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个体,有着强化力的文化聚合能力,对外来文化吸收的同时,也对自身文化有着完整的保护能力.但是,对蒙古族个体的传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很关键,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体育文化的传递.
“蒙古男儿三项”即搏克、射箭、赛马,是蒙古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视域下,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体育项目.无论是搏克、射箭,还是赛马都渗透着初民的那种原始的情感.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得以延续.纵然,经历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仍然保持着草原体育特有的风格,而存在于今天人们活动的视野.虽然部分蒙古族体育项目已逐渐淡出或消失,但草原游牧体育给蒙古族群所培养的性格是随处可见的.对于生长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先民来说,蒙古族传统体育与地域性的相关性是无可争辩的.草原的伦理观念、宗教信仰、仪式风格无不贯穿于蒙古族行为之中,对蒙古族传统体育有着诸多的影响.然而,从更深层的文化来讲,人们是悬挂在意义网上的个体.蒙古族游牧体育编织着一系列特殊的符事情体系,来表达个体对自然的崇拜、对外界的对抗、对自我的宣泄.
〔1〕国家民委,国家体育局.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Z].[2006]16 号.
〔2〕栾桂芝.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再认识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71.
〔3〕张连凯,高大光.整合地域特色资源 宏扬民族体育文化[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4(6):712.
〔4〕郭浩,等.走进科尔沁草原[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3.
〔5〕钟志勇.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07(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