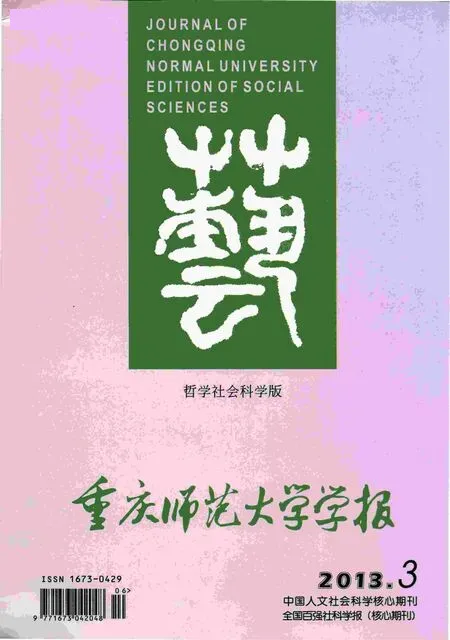试探“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价值
2013-04-02谭真谛
谭真谛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一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西方早有争论。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第一个明确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其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演讲,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逐步消解着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区隔,我们在将“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进行着“艺术转换成生活”。随后,在《消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的三个层次:“第一,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期间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以及其活生生的事件中,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是将生活转化成为艺术作品的谋划。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1](95-97)迈克·费瑟斯通的观点其实包含了对于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各种基本描述,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是对这一系列描述的概括。
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与探讨引发了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兴趣和讨论。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有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它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物质生活质量飞速提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人们日益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过渡的前提下而出现的一种理论对现实的回应。这样的回应,是客观现实对理论的要求,也是哲学、美学以及文学艺术理论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张慧瑜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指出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再也不是‘蛋糕上的酥皮’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非是颠倒美学传统,或者美学与经济基础的支配关系,而是文化、经济的传统划分在消费社会中被打破了,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很难找出一个纯净的经济领域或文化领域,这种越界的看法又借重于布迪厄的场域概念。”[2]
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指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准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消费文化”的蓬勃兴起。“日常生活审美化”无疑消解了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消解了审美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有学者将争论者分为“泛化”和“异化”两派,对两派的区分是建立在学者们关于审美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消解的不同看法之上的。
“泛化”派以陶东风、王德胜、金元浦、周宪等为代表,认为在当今社会中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逐渐被消解,而这种消解实为审美的泛化。如张进所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趋向于美化,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3]大众的日常生活日趋美化,更多地融入了美的成分。“泛化”派将这种现象看作是新时代下审美的泛化。
“异化”派主要以鲁枢元、童庆炳、赵勇、毛崇杰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有着西方的文化背景,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这是审美的异化,与传统审美相背离。如鲁枢元所说:“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是审美活动的实用化、市场化。”[4]“异化”派指出这种现象的本质是非审美和反审美的,是工具理性控制加剧的表现,是片面地从消费自由的角度否认真正的审美,否认审美的人文理性。[5]
二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实际上是关于“审美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对于两组类似却不同的概念进行区分,可以使“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更加明晰。
“异化”派代表鲁枢元在《拒绝妥协——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一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美学、文艺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一个群体,顺应当今社会生活发展的滚滚洪流,隆重推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理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倡导者们尽量谨慎地回避直接谈论其学说的价值取向,但又明白无误地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看作一种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认定它“将把我们推向一个全新的社会”,那将是在技术与市场基础上的美学重建,乃至人类社会秩序的重建。
其实,“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两组概念,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在审美指向、价值取向上则迥然不同。正如鲁枢元所言:就像“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一样,几乎是南辕北辙的。庄子寓言故事中“庖丁解牛”,庖丁“解牛”这一生活化行为由于主人翁纯熟的技法和全神贯注的态度,以致自己都被这一行为过程所感动,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愉悦,平凡的劳作也就变得美好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自我陶醉的“化境”。“解牛”这种劳动生活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入了“审美”殿堂,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反之,若是运用艺术手段进行精心包装,如:包上精致的纸盒,选用美丽的年轻女性贩卖等等。照此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视听,立马畅销起来。这就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鲁枢元指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度,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二者的不同在于,一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一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这样说,并不否定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但其价值的指向毕竟还是不同的。[4]
上述观点对我们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区分“审美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根据艺术规律和生活体验,窃以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强调以美点缀生活,其根本是“生活”,追求的是“美化的生活”。而“审美日常生活化”则是把“美”变得通俗化、生活化,追求完全消解艺术和生活的界限。不过,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可以淡化,却并不能简单地、完全地消解,更不能将二者合并。“艺术”点缀“生活”,而非“艺术生活化”(这里并不是指艺术的普及或题材的生活化而是指把“艺术”与“生活”完全等同)。因此,“审美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联系紧密,容易让人产生混淆,但二者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我赞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而否定“审美日常生活化”。试想,当“艺术”变得和日常生活的吃饭睡觉一样普通时,还可以唤起我们的“审美期待”吗?那将会是无趣的、普通的,最多只剩审美疲劳而已。审美的“泛化”、“艺术”与“生活”的合作,这才是合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区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前提下,“日常生活审美化”追求以美点缀生活,主要表现为三个“泛化”——审美主体泛化、审美媒介泛化(包括场所)、审美对象泛化。具体来说: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审美”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属于贵族、精英圈子的专利和特权,“审美”同样进入每个社会阶层。五彩的霓虹灯、美丽的街心花园、富有设计创意和美感的产品,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美充斥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有能力去创造更多美的事物,而审美意识的提高则让我们能更好更自觉地去发现美。其次,审美媒介泛化(包括场所),传播媒介不再局限于纸墨或传统的乐器,场所也不再是皇帝的后花园、堂皇的歌剧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创造力的提高,网络等一系列新兴媒体逐步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我们传播和获得美的主要阵地,审美途径丰富,使我们获得审美享受更为简单便捷。最后,便是审美对象的泛化。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在人类审美意识强化,以及今天崇尚个性化、自由化、多样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问候信、文化现象、琳琅满目的物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审美的对象不断地适应着我们个性化的需求,仅音乐就有交响乐、爵士乐、布鲁斯、摇滚、流行音乐、乡村音乐、电子音乐等等。不难看出,审美主体泛化、审美媒介泛化(包括场所)、审美对象泛化现象已然存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脚步还在持续加快,已经切切实实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是每一个美学者都不能忽视的现象。
三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具有批判性,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对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批判,对于等级、阶级的批判,是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其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启发性,我们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肯定。当然,就这一理论而言,作为审美的对象并非一定得具有批判性,我们也无意于将“具有批判性”作为审美的唯一特性,否则将是给审美打上“功利性”的标签。以文艺学具有批判性的特点去局限美学是不科学的,将美学硬性地打上“道德主义”的标签,也与时代绝对不合拍。当今世界更加追求和谐发展,人类的进步,需要有对现实的批判,也要有对现实的肯定,更会包容和满足人们个性化的审美需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批判性。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是与“精英主义”相对而言的,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内涵,正不断淡化大众与精英的界限。“日常生活审美化”暗示了大众文化系统对精英主义立场的批判,对等级及某些观念的批判。比如英国伯明翰学派就是对利维斯主义的清算,这在客观上冲击了文化的一元主义局面,也颠覆了“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张慧瑜曾说,“日常生活”的话语在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时期并不存在,所以到80年代中后期,诗歌写作开始对“日常生活”大加青睐。以池莉、刘震云为代表,其早期所写的市民小说对于日常生活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一体化”文学模式的抵制和消解。从这个意义说,“日常生活”是起源于8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的概念,也可以说“日常生活”是一个新的发现。而“审美”则是80年代建构完成的意识形态。贺照田在《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一文中对“文学即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80年代美学的核心命题进行了反思,将审美与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结合在一起,并把审美自身的意识形态性隐藏起来了。从“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历史化角度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似乎可以提供给我们重新反思文艺学以及已经被学科合法化的文学观念及意识形态性。[6]或许今天,有人认为随着主流文化的不断调整,消费文化的政治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其批判性正在淡化乃至丧失。但应当看到,当社会日趋稳定、和谐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眼光局限在对政治的批判上,更多的是以对现实持肯定积极态度去进行创造“美”的活动,这也必然产生与过去不同的审美情趣以及与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多元化审美态度。
综上所述,面对这场“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引发的美学观念的碰撞,我们已经体会到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来临。“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需要结合多个学科知识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不能固执于己方观点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简单的情绪化的否定,或者只将其局限于美学领域进行研究,冷静与客观、超越与务实才有助于美学发展。面对不断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代,我们应当多发现新问题,多提出新观点,多寻找新方法,从而让“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名至实归”。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
[2]张慧瑜.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中国学术论坛,2006,(3).
[3]张进.人论与文论的深度自觉和交互建构[J].社会科学,2002,(2).
[4]鲁枢元.拒绝妥协——“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J].文艺争鸣,2004,(3).
[5]陆扬.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J].理论与现代化,2004,(3).
[6]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J].文艺争鸣,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