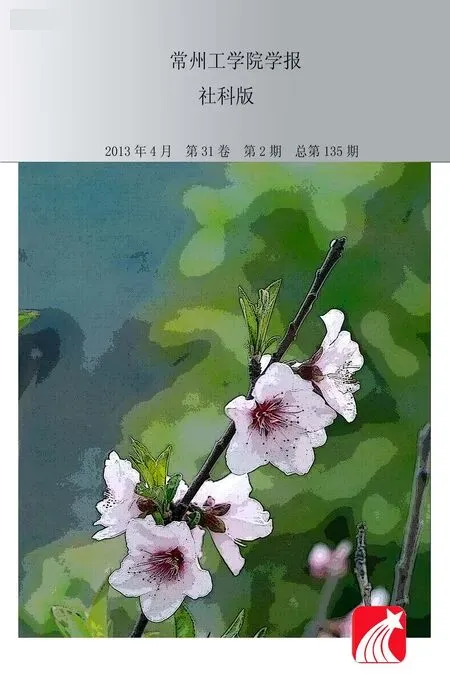小说“偷情”叙事与女性个性意识
2013-04-01王悦华
王悦华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在人类个体意识的发展进程中,女性个体意识的发展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从较早期的对女性个体意识的束缚,逐渐演变为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关注,直至后来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完善和尊重。
一、《金瓶梅》:对女性个体意识的束缚
《金瓶梅》中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的故事家喻户晓。他们违背儒家纲常伦理,追求情欲,暗地苟合,被武松斩首祭兄。他们的偷情行为最终受到了严惩,受到大众的谴责、上天的惩罚。
兰陵笑笑生将三个从偷情走向灭亡的女子名字“金”“瓶”“梅”作为小说的题名,无非也是想借其中人物演绎的因欲灭亡的悲惨故事表达自己正统的道德观念,以达到警世劝世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注重伦理纲常的国家,儒家更是恪守礼治,在对待男女关系上尤其严苛,古来就有“男女大防”的传统,甚至在家庭亲属之间也有严格的男女礼仪制度,《礼记·曲礼第一》记载:“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而在婚姻关系中,夫妻之间的忠诚,尤其是女性对妇道的恪守十分重要,几乎受到了大众的严格监督。《礼记·婚义》记载:“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作为一种维护封建等级伦理制度的有效工具,在古代具有强有力的伦理约束力。所以,偷情作为对婚姻规则的违背,不仅挑战了婚姻的伦理约束力,而且挑战了大众的伦理价值观,受到强烈的批判和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是无可厚非的。《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对于书中“偷情”行为的批判态度,基本代表了千百年来最为主流的恪守儒家纲常伦理的大众的价值观念。
可是当我们审视后世对潘金莲和西门庆这两位偷情主人公的评价时,不难发现,潘金莲已然成为“荡妇”“淫妇”的代名词,而与此同时,西门庆被批判的焦点却只是“风流成性,纵欲过度”,并没有像潘金莲一样被指责为不自重不自爱,以及对婚姻不忠,背叛伴侣。这不难反映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对待两性关系上的男女不平等,女性显然背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在中国历史上,对女性贞洁的重视作为一种性规范,最初是私有制度的衍生品,是财产关系在个体所属关系上的体现。它是父系时代到来的标志,重视女性贞洁即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后来它逐渐成为压迫女性的专制制度[1]。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婚姻这种双方建立的形式上相对平等的对立关系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只是众多男尊女卑价值观念的体现之一。它无疑是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忽视,在人们的价值观被传统道德束缚的时代,女性的个体意识同样被紧紧地束缚着,即使受到不公平的道德要求,女性也并不自知。个体意识的长期束缚使她们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她们甘愿忍受,更不会反抗。
我们不能否认,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事实上,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因为男女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角色和分工的不同,男女在社会生存上享有绝对的公平难以真正实现。虽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这样的不对等关系已然改善很多,但是不公平现象是不可否认的,并且将在较长的时间里存在。其实,不论是婚姻还是其他的对立关系,又或者是权力以及义务的分配,男性女性的绝对公平化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秋海棠》: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关注
《秋海棠》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秦瘦鸥的代表作品,其主人公曲折多舛的人生悲剧就是从吴玉琴和罗湘琦的偷情开始的。罗湘琦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和婚姻,爱上了戏子吴玉琴,不仅共育了一个女儿,而且在不能和情人厮守的情况下,牵挂其一生。不同于潘金莲和西门庆丑陋、罪恶的偷情,他们的偷情行为是源于在苦难生活中对爱情的追求,吴玉琴和罗湘琦对爱情的不懈追求是美丽的、圣洁的。
小说中罗湘琦将背叛婚姻作为对自己悲剧命运的反抗,这也是《秋海棠》这部“五四”后的作品对当时时代的控诉,控诉社会的黑暗面,控诉在金钱和强权统治一切的时代老百姓命如草芥。不难看出,在《秋海棠》中,婚姻关系里的自我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关注,自我意识,尤其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受到长时间的压迫和抑制之后,对封建束缚终于产生了爆发式的本能的抗拒[2]。郁达夫曾这样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①五四运动让人们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意识,在婚恋关系中“人的意识”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尊重。其中,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②为大家所关注和思考。
在传统的婚姻关系里,婚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存在,婚姻关系中个体的情感和需求很少被关注。而在千百年的沉睡后,自我意识的苏醒,让人们将矛头对准了所有的封建伦理束缚,正如周作人所讲:“人们的道德观念中丝毫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这些道德观念是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③人们在思想开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传统的封建婚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家庭幸福的保证,个体的幸福才是婚姻关系中最需要关注的部分,婚姻在个体自由的追求中可以成为守护幸福的堡垒,而在对忽视人性的封建道德一味恪守中,很可能沦为追求个体幸福的障碍。民众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判断都开始产生变化,对于“偷情”的态度不再是严厉批评,似乎也开始采用辩证的态度审视偷情行为。
所以,在小说《秋海棠》中,不同于之前文学作品中对“偷情”的一味批判,作者秦瘦鸥显然对“偷情”这一背叛婚姻的行为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作为一种肯定爱情的形式存在,而在这种关系里,婚姻作为一种形式是不可能喧宾夺主的,爱情比形式更为重要,追求爱情即是追求自由。作者开始打破对婚姻形式的恪守,关注个人情感,关注婚姻关系里的个人意识。作者通过“偷情”这一离经叛道的行为试图打破社会对封建道德的愚昧盲从,试图引起人们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倡导人们勇敢追求自我幸福。现实生活中有太多无奈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其中不少掺杂着时代的因素,引发了作者一系列关于时代的思考。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虽然深爱对方,却无力推翻现实,只能通过偷情结合的情节,控诉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通过对权势和金钱,婚姻和责任的思考,引导读者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定位。
三、《红玫瑰与白玫瑰》: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完善
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和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到她成长经历的影响,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晚清朝臣中的清流,娶了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小女儿,到了她父亲这一辈,实际上已家道中落,但也依然有机会见识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这种遗少式的童年生活以及后来父母的离异给张爱玲的心灵投下了巨大的阴影④。这些经历使张爱玲对世事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洞察力,好像阅尽沧桑的老妇人,能够轻易地转换或柔软或犀利的笔调勾画她眼里的人生。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一部典型的张爱玲式的作品,讲述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男主人公佟振保与朋友之妻王娇蕊偷情,而当娇蕊为了他与自己的丈夫决裂时,佟振保却在犹豫和无奈中抛弃了她,娶了另一个娴静的女人孟烟鹂。小说中王娇蕊以其娇媚的体态、炙热的情感而被看做佟振保生命里一朵怒放的红玫瑰,而孟烟鹂以其娴静典雅的气质成为了与红玫瑰相对绽放的一朵白玫瑰。
小说开篇的这句话让人印象很是深刻,“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⑤这暗示着在佟振保作为男性社会的代表对女性的看法,他将女性分化为对立的两类:妓女和贞女,情妇和妻子。将女人视为不完整的人。不同于佟振保立体的复杂的人物性格,这里的女性形象被单一化、平面化,似乎女性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成熟的意识。“由于女性处于等级社会的最底层,一切社会性活动都与女人无关,女人被禁锁家中,女人在家庭、性爱等封闭性圈子内。”⑥社会活动作为完善人类个体意识的重要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女性生活中是缺失的,就算女性的个体意识开始被发现和认识,女性的形象仍然是不完整的,人性具有复杂性,并不是靠“红”或者“白”就可以简单区分。
在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偷情情节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红玫瑰王娇蕊,她以背叛自己婚姻为代价,情难自禁地爱上了佟振保,而后是白玫瑰孟烟鹂,当她面对已然失控的婚姻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的时候,她也选择了背叛婚姻和家庭来安慰自己。张爱玲利用偷情这一被大众普遍否定的行为进行了人物形象的颠覆。作者通过掺杂着爱恋和欲望的佟振保和王娇蕊挑战伦理的疯狂的偷情,将王娇蕊成功塑造成热烈而美艳的女子形象。而孟烟鹂是素净的,淡雅如同白玫瑰,“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医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⑦她远离了污秽,也远离了美好,她素净到乏味的程度。而就是这样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通过两段偷情的经历,各自悄然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原来的红玫瑰数年之后再嫁,成为了美丽娴静的妻子和母亲,而原本素净如白衣的白玫瑰却变成了背叛婚姻和丈夫与裁缝偷情的情妇。王娇蕊曾经娇美,任性而没有大脑,但危急时刻她行动果断,在佟振保为了母亲和前途要离开的时候,她决绝地“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⑧,她虽吃了苦,但学会了认真地爱,精神逐渐成熟。后来经年相遇,回忆这些年时她说:“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⑨似乎已经在思考女性的价值、地位问题了。而烟鹂也在家庭和经济双重危机中,“突然长大了起来,话也说得流利动听了”,“变为勇敢的小妇人”⑩。
在这里,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故有的偏见彻底坍塌,张爱玲成功地颠覆了男性看女性的观念,女性意识并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她们的意识、情感和思维同男性一样丰富,成熟而立体,可以这样说,女性精神在包容性和可塑性方面甚至优于男性,女性以其特有的优雅而好奇的心态来到了封闭她们的圈子之外,等待她们学习和开创的东西还有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是立体的可爱的,而在恋爱和婚姻关系里男性对女性造成的打击和伤害在某种意义下可以转化为帮助女性成长的重要资源。
四、结语
其实,“偷情”的字面意思是很俏皮的。“偷”的意思易懂,而“情”为何物,却自古无人能够具象清楚地将它描绘出来。“情”的意思虚得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情”不是能包裹好藏起来就守得住的东西,世上的情总是在你我之间来而又往,就算偷来盗去,也没什么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它既然被用来描述人们的情感行为,其中的道德意味就该被遵守和尊重。
人们对偷情行为的道德批判倾向从来没有错,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逐渐丰富,于是在道德审判的过程中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片面、独断的批判或者赞扬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在一次次的道德衡量中,长期受到忽视甚至压迫的女性个体意识被发现和重视,并且得到较为全面和健康的发展。
注释:
①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②鲁迅:《伤逝》,见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③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④潘柳黛:《记张爱玲》,见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昨夜月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36-39页。
⑤⑦⑧⑨⑩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作品集》,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页,第42页,第42页,第44页,第48页。
⑥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56页。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朱贺福.民国言情小说的现代性——以《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为例[J].温州大学学报,2010(3):8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