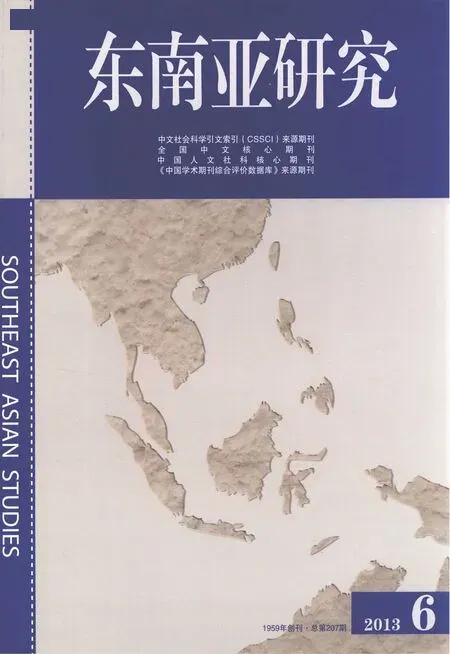忆先生二三事
2013-03-27袁丁
袁 丁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510275)
今年是导师朱杰勤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作为先生的不成器学生,不知该如何下笔,只能回忆二三事作为纪念。
一 初次见面与报考暨南大学
其实,我当年决定报考朱杰勤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纯属偶然。
1984年底,香港大学举办一个华侨华人历史研讨会,我作为在读的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随中山大学老师们一起参加了研讨会。去到香港,当时会议主办方港大历史系的赵令扬教授单独拉我到一边,交代我说:会议已经安排我和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住在一起,让我照顾朱先生的起居。于是会议期间,我一直陪着朱先生。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朱先生。坦率地说,开始时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在中山大学读东南亚历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各位老师们都把朱先生的著述作为必读参考书,无论是朱先生早期的东南亚古史和华侨史的考证,还是华侨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著述,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心里对朱先生钦佩万分。一旦与久仰的大师面对面,确实不知道该如何交往。尤其是作为会议参加者,我提交的那篇小文章,不知道会不会被先生批得体无完肤?
出乎意料的是朱先生竟然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刚一见面,先生就笑容满面询问着我个人学习的经历,然后说要仔细看看我准备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很快,晚餐后一个小时,先生就在房间里与我谈起了论文,而且居然一开口就是表扬,让我顿感意外。于是我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写作缘起、史料搜集过程和写作思路。作为知名的历史学家,朱先生不仅不嫌我浅陋,反而非常认真听我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然后教我分析那些史料,指出进一步深入的途径,让我茅塞顿开。
那天与先生从晚餐后一直谈到半夜。临睡前,先生突然问我:“你想不想进一步深造?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怎么样?”说实在的,此前我并未打算报考暨南大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中山大学东南亚所已经决定让我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特别是领导和硕士期间的老师们都希望我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出国留学或去国内其他大学深造。另一方面,我不久前刚刚去过厦门,很是为厦门和厦门大学的海滩美景所吸引,并与几位老友相约将来一道去那里读博士。在那时,中国的研究生制度刚刚恢复,全国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屈指可数,朱杰勤教授是广东全省唯一的历史学专业的博导,中山大学历史系都还没有博士授予权。所以最初我没敢往报考朱先生这方面想,于是先生这么一问,便成了我最终的选择。
步入师门至今,我一直感慨。倘若没有这次香港的机缘巧合,倘若没有朱先生那番谆谆教诲,后来那三年暨南园的学习生活也许就不会发生。作为前辈长者,作为著名教授,先生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风范,最是值得我辈后人学习的。
二 暨南园中的惊喜
1985年9月,我到暨南大学深造。每周,研究生们都要去朱先生家里上课,因为先生不久前在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时跌伤了腿,行走不便。而且,那时博士研究生没有专门的课室供上课用。
每次去朱先生家上课,师兄弟们都很高兴。先生家中备有一方小黑板,大家围着先生,一边品茶,一边讨论学术,气氛热烈融洽。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对于上课的认真,却是很多年轻教师们所无法相比的。谈到史料,先生总会让我们去书架上翻书,然后爬梳整理;谈到研究,先生又会让我们各抒己见,然后一一点评;最后布置读书计划,让大家回去自己看书。先生还经常要求我们师兄弟之间要多交流,互相切磋,不要关起门来搞学术。
在暨南大学读博期间,平常,大家都各自去图书馆查资料,或者在房间里读书。记得入学后不久,有一天我正在研究生宿舍里读书。同窗的朱凡同学突然带着朱先生敲门而入,让我非常吃惊。一方面,先生不久前在外地摔伤了大腿,走路一直是一拐一拐的,行动不便。另一方面,说实在的,我读书多年,从来就没见过教授到学生宿舍和研究生宿舍探访的,何况是朱杰勤先生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对我来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事先还没有任何通知,完全可以说是突然“袭击”。
朱先生笑眯眯地进来后,先不坐下,而是仔细打量着我房间里面书架上的书,然后翻着我乱糟糟摊在书桌上那堆书——我正在写相关专业的文章。我窘迫地看着房间里横七竖八的杂物和摊得一桌的书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可先生完全不在意,坐下后先是问起我读书情况,给予我很多鼓励,让我心情慢慢放松下来,随后又询问我生活上有何困难和问题,使我倍感温暖。
我忐忑不安问起先生如何来到宿舍,朱凡这时才说:“朱先生要来看看大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所以让我用单车载他来!”要知道先生年事已高且腿脚不便,坐在自行车后座前来,还要爬好几层宿舍楼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
时隔多年,这段往事仍然让我记忆犹新。扪心自问:对于晚辈,对于学生,如今的我,自己能够做到这样么?
三 毕业的相片
我在暨南园读书时,朱杰勤先生是暨南大学仅有的两位博导之一,地位崇高。那时的报章杂志经常有他老人家的消息。有一年回家时,我父母还特意拿出刚出不久的《广东画报》,上面有对先生的专访,有好几幅彩照。
1988年6月我们毕业前夕,几家报社来采访朱先生。其中有位《羊城晚报》记者在朱先生家中,要给先生照几张相片,准备登报。于是我们几位学生也被用各种姿势摆弄在老人家身边。先生高高兴兴地配合照相,完全没有烦言。
毕业那天,我们惊喜地发现,当天的《羊城晚报》居然刊登了我们与朱先生合影的相片,而且居然是在头版!与当下不同,那时的国内媒体对于尊师重教的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更让人意外的是,广州还有一位画家,后来看到报纸和画报上刊登的我们与朱先生合影的相片,居然用油画进行了再创作,还在画展中展出。其画作,又刊登在大报上,被我的师兄弟们看到,并且转告给已经离开了暨南园的我。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那个年代,全民经商的浪潮强烈冲击着校园,国内各地大学教师流失严重。可是在恩师的影响下,我却从未想过要放弃专业离开讲坛。先生那种人格魅力,那种大师风范,一直都是我前行的动力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