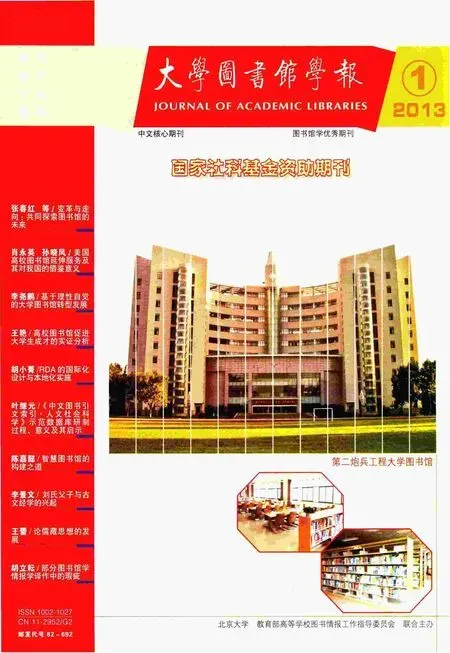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探索
2013-03-27□杨芬
□杨 芬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探索
□杨 芬
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实践,从古籍修复人员配置及其协作管理、古籍修复工作开展规律、古籍修复程序及相关管理、古籍修复技术特点及内涵的文化特质4个方面,总结修复工作的经验与模式,提炼古籍修复工作的核心特征,并延伸对古籍修复发展相关问题的思考。
古籍修复 修复技术 修复文化 北京大学图书馆
前言
北京大学图书馆迄今已有110年的历史,百余年来经多代图书馆员对古籍搜集保护的努力,积累了今日宏富的古籍收藏。目前馆藏古籍总量达150万册,其中善本古籍20余万册,另有金石拓片8万余件。如此庞大的古籍收藏自然决定所需修复古籍的数量之庞大及修复工程之艰巨。然而在图书馆的发展进程中,限于图书馆内部各项业务状况及外部形势,古籍修复一直还很难得到重视而大力发展。我馆修复工作大致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图书馆设有“装订室”,主要负责各类图书的装订、复印等业务,古籍修复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仅一人按自然工作量来修复。80年代,装订室逐步扩大成“文献服务部”,人员相对增加,其古籍修复人员曾多至4人左右,但当时仍主要开展一些较基础的古籍装帧修补工作,如对普通线装书缝线等。80年代后,因各方原因我馆修复人员又逐渐流失缩减。直至90年代,图书馆正式成立了“古籍部”,古籍修复才第一次归并到古籍部,作为古籍部业务中一项专门工作,修复岗位人员基本保持在两人。综而言之,从60年代至90年代是我馆修复工作发展的前期阶段,其修复人员大都是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培训出身的专业人士,奠定了较好的修复技术传统。只是由于各方面的有限条件,修复工作的开展相对处于缓慢、自然、随意的状态。从90年代后至今,严格而言,我馆各方面的修复条件仍未得到明显提高,但在克服资金短缺、人员缺少、条件简陋等情况下,努力调动发挥积极因素,探索古籍修复工作开展的方法,经多年实践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本文试以总结我馆近年来古籍修复工作的经验,提炼古籍修复工作的核心特征,并延伸对古籍修复发展的相关思考。
1 古籍修复人员配置及其协作管理
中国古籍修复专业人员普遍缺乏是历来古籍修复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我们同样面临这方面的问题。此外作为隶属于大学的图书馆,在人事制度上受到学校各方面人事管理与岗位设置的制约,在人员聘用及使用上很难充分完善化。目前我馆古籍部岗位设置中仅有一个名额的修复人员正式编制,如此有限的人数与实际所需的修复工作量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为了解决人员匮乏问题,我们经多方努力探索出“馆内正式人员”与“外聘临时人员”双重合作的模式。前者即学校人事在编的正式人员,后者目前主要包含两个来源:一种为馆聘合同工——即在协调学校人事制度的基础上,为补充行政技术等人员而增设的合同制岗位;一种为外包公司调拨人员——即图书馆与社会有资质的修复公司合作,经馆方与公司方谈判并签订协议后,公司派遣员工到馆工作。其人员在人事制度上仍隶属于公司,在实际工作中遵循馆内各项业务安排与规章制度管理,我馆根据修复总量与修复质量等级计费,将报酬付给公司,公司再为其员工分发工资及奖金。目前,中国社会市场上存在一些中小型的修复企业,其员工往往要经过一定的资质考核,相对积聚了一部分修复职业人员。图书馆与之合作可弥补内部修复人员的不足,并可根据不同阶段的修复量来缩减或扩增人员,相对灵活,保障修复工作的进行。但另一方面,修复企业因私人营利等因素也存在不稳定性,不能作为可靠的依赖对象。由此设想,倘若各个图书馆及相关机构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支持社会修复队伍的建设,便能够在社会中形成较规范的修复职业团体及修复公司的稳定结构。这样的修复队伍可成为各馆共同享用的资源,根据各馆修复工作需要来调配,是各馆修复工作开展的后备军。
在上述双重合作模式下,我馆目前的修复人员结构为:正式编制1人,馆聘合同工1人,外包公司调拨人员2至4人。以正式编制的专业高级技术人员为修复组组长,带领组员展开工作。组长的职责主要包括:与典藏组合作,负责古籍的出入库交接工作;古籍修复等级的划分、分派工作;制定古籍修复方案;发现在修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检查修复质量;组内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工作等。组员主要负责经手修复古籍的安全,保证古籍在修复过程中不受损等。
此外,图书馆身处校园人才培养基地,我们也积极利用学校的资源,来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如与我校考古文博学院合作,该院的专业研究教师往往成为我们的咨询顾问,考古专业学生则常到我古籍部实习与协助工作,还利用考古系的一些检测仪器对古籍书进行相关的考察与研究。总之,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尽力争取多方协作,来有效调动可利用资源。
2 古籍修复工作开展规律
目前面对我馆庞大的古籍收藏,我们还难以完全摸清家底来整体规划古籍的保护与修复工程。故严格意义上说,我馆的古籍修复未能以明确的目标性、清晰的阶段性、严密的计划性来实施。相对而言,在现有条件下,有效地调动人力、物力,协调古籍部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来保障古籍修复工作的平稳进行。多年来修复工作形成了一种在非精细计划安排下而自然稳步的开展规律:
其一,配合古籍阅览服务及时进行修复。在日常古籍阅览服务中,阅览组人员与典藏组人员在读者调阅的书籍中,如发现各种破损书籍,及时归入“修书”书柜。目前,日常处理的大量修复书籍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而成的。因我馆藏书量大,各种书籍的破损情况相对严重,因此,仅就日常发现所需修复的书籍,日久以来已累积了一定的数量,修复工作的开展大部分都在这些书的范围内,且又不断有新发现的书要修,基本无有止尽。书籍修复时间的先后顺序,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状况就以修复人员来选择安排;若遇情况严重者会提到加急修书行列中;或因读者急需调阅,修复人员也会尽力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加快完成修复。
其二,配合古籍部项目开展来推动修复工作。如近些年我馆主持编纂的《清人诗文集汇编》、《明人别集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在研究整理过程中,需要核对版本,查看书品,对书品不良者及时进行修缮,以利扫描出版工作的开展。另有专项修复项目而得到专项资金的资助,从而妥善处理一批书整体的修复方案。如2005年11月,北京大学以较大投入购买了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家藏千余册“禦霜簃”戏曲抄本。程氏书破损程度相当严重,为能尽快开发这批书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图书馆报请学校特批专项资金用以修复。此项资金含两笔费用,即修复材料费和外聘人员劳务费。我们采取与有古籍修复资质的墨林公司合作,由公司派古籍修复人员来馆对程氏藏书进行具体修复工作,古籍部则负责制定修复计划、工作流程、修复技术和方法的指导以及修复质量的审核。修复工作从2006年11月1日开始,至2008年5月完成对有目录记载的程氏藏书的修复与装订工作[1]。至今已全部完成所有修复工作,并特制一批楠木匣子作为此批书的精美装帧。又如从2001年起我馆持续购买家谱,至今已达2200余种,属国内收藏大馆。2012年度,图书馆计划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文物保护研究室共同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北大馆藏善本家谱修复”项目,一方面利用图书馆古籍修复技术,一方面发挥文博院研究所长,共同促进业务工作,并有效借助外来资金解决本馆的实际业务需求。
其三,除了以上两大方面为日常修复的主要任务外,我们也适当接受学校及社会多方面的修复需求来提供服务。如2001年我馆帮助清华大学图书馆修复了大型古籍丛书《古今图书集成》。2011年修复组人员协助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修复大批名人藏书与手稿约一万多页。2011年10月民间胡氏家族之人寻访到我馆,我们以专业的修复技术,将其遭火焚毁、损坏严重、不堪翻阅的家族宗谱,还原到了品相相对完整的书籍状况。
3 古籍修复程序及相关管理
近年来我馆古籍修复工作具体开展的主要模式为“以修复组组长为技术总监,带领修复团队共同协作”。组长掌握较高的古籍修复技术与一定的修复经验,成为修复技术与质量把关的权威;各组员则具备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细心踏实的工作作风,平稳顺利地完成每一部古籍书的修复。在小组协调的合作中,修复工作的开展大体形成以下3个阶段的流程:
3.1 修复前
其一,组长对待修古籍建立修复档案。档案内容主要包括:a.书籍原貌各项信息记录——馆藏索书号、书名、卷册函数,装帧形式、书页规格,以及有关书盒、书套、书函、书匣等情况作为附件记录;b.书籍破损情况记录——书皮或包首、护叶、书叶的破损位置、破损面积及破损比例。除了书面记录外,还可拍照记录存档。
其二,组长研究分析修复古籍,确立修复方案。通常情况下,修复工作所遵循的传统原则是“整旧如旧”,即经过修复,尽量保持书籍原始面貌和装帧特色。因此,修复人员须按书籍的破损程度对书籍全面谨慎地分析,考虑配纸、修补方式、修补顺序、装帧形式等各项修复措施,来妥善地、具有前瞻性地考虑待修古籍的修复方案。
其三,根据修复方案,小组人员共同准备各项材料。如根据原书页的材质准备修复用纸,为了颜色接近,往往要自行配料染纸。另外,还要按需制作浆糊等。
3.2 修复中
准备工作完成后,小组成员分配承担各册古籍具体修补工作。通常修复环节包括:拆书、剔除书叶中的杂质、去污、修补或托裱、捶打、压书,到修补后装帧、配函套等。这些环节主要都由手工操作完成。函套的制作目前为外包业务。因制作函套需要一系列的材料、空间及时间,我馆古籍修复量大,且人力物力有限,所以我们选择与专门的函套制作坊合作。他们可到馆细量书籍规格尺寸,根据每一部书的大小制作合适的函套,待完成后整批送货。由此,及时地满足了古籍装帧配套的需求。
修复中,每一部书的修复情况还可能随时出现各种变化,就需要及时调整修复方案。同时,修复工作的安排往往是交叉进行的,如一部书修补后需要用压力机压放一段时间,期间就及时安排其他书可操作的修复环节。因此,每一个修复人员都应具备全程修复环节的能力,没有明细的分工和专项固定的工作,而是随时根据修复工作需求来统筹安排,大家共同协作,提高修复效率。
3.3 修复后
各组员负责所修书籍的全面管理,在修复档案中详细记录修复内容,包含所修书叶数量、每一项环节具体的修复手段等。待书籍修复完毕,上交组长验收。组长根据书叶、书芯、书籍外观、各式装帧等各项具体的修复质量标准来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查。如查看书籍总体是否平整,补纸的颜色与平整度,书叶拼对是否准确等等。若验收有问题则及时处理,验收合格则归库。
在上述三个流程中,除了以修复组长为核心进行监督外,我们也不断修订《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条例》,将修复工作的各项环节做出明细规定,来规范操作流程,完善修复工作的实施与管理。其中,较为重要的如“修复档案管理”。目前我馆的修复档案管理还停留在较初级的阶段,即仅以纸本文字记录一般信息,部分有图片拍摄存档。实际上一种完善的古籍修复档案应规范地记录修复材料的来源、配方和制作方法;记录破损古籍的修复原则方针、技术手段和修复部位;使用照相技术对修复前后的古籍和修复过程中的独特技术处理进行拍照等[2]。因为作为文物保护的手段,古籍修复既力求每一次修复工作的谨慎恰当,又要保障修复工作的“可逆性”,故保存各个阶段详细的修复档案是非常必要的,以利将来可能有更好的修复技术与修复设备,可对原先不理想的修复状况再次进行修补;而且这样的修复档案对于保存、传播科学的修复原则方法,保存珍贵的修复史料都有着重要意义[2]。近些年,国家图书馆带头开始建设“古籍修复管理系统”,采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对修复工作进行管理,开展修复档案的记录、储存,进行修复档案的馆际交流。建立这个系统的目的在于借助先进科技手段,从管理入手,对修复资源进行整合,对修复工作进行管理,对修复技术进行推广[2]。而且从根本上说,它是科学管理和操作的平台,是促使古籍修复由经验修复向科学修复转化的助推器[2]。可见,古籍修复档案管理应逐步实现从“手工登记”到“计算机管理”的阶段。在计算机管理中,一方面规范文字著录——即细化分列各个著录项及统一著录方式;一方面丰富图片影像资料——即利用照相技术全程跟踪修复流程,一些重要的流程还可通过摄像记录动态过程,以鲜活地保留修复过程中书籍的种种变化。从而所创建的修复档案资料库包含了翔实的文字资料、直观的图片与生动的影像,还可将这些资料系统地组织、规范地排列,以利随时便捷地检索。如果各个图书馆及修复机构能够建立自己完整的修复档案系统,还可相互链接来组建一个更大的档案库与修复资源检索平台,共同分享丰富的古籍修复案例及具体的技术方法等,这将大大促进行业的交流,对于提升整体的修复效率与修复质量必大有裨益。
4 古籍修复技术特点及内涵的文化特质
目前我馆虽未有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各方面的修复条件设施相对简陋,但一直注重和保持着传统修复工艺品质。传统古籍修复技术包含着一系列精微细致的手艺,其中凝炼着古人的智慧及中国的审美观念,甚至是从技术层面上升到艺术层面的精妙追求。以下试从日常古籍修复工作中总结修复技术的核心特征,提炼其内涵的文化特质,并对修复文化及其相关的传承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4.1 注重修复材料的纯粹天然性
传统古籍修复技术注重使用纯天然的材料。以修复所用浆糊为例,它们绝对不能是含化学成分的现代粘合剂,而要用天然的面粉制作而成。通常是靠自己手工制作,方法是将面粉加水和匀,放在水中揉捏漂洗,从而洗出淀粉,滤去面筋。洗出的淀粉置于桶中沉淀,经多次换水淘净、控水、晾干,最后形成高纯度的淀粉。修书时取少许加水稀释后熬制,根据所需浓度调制得当,就做好了修复古书用的浆糊[3]。这种自制的淀粉新鲜、柔嫩而有弹性,是良好的天然原料。浆糊运用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修复的质量。除了浆糊外,修复中还有诸多天然材料,如修复用纸都是植物纤维的传统“手工纸”,订缝材料是蚕丝搓纺而成的“丝线”,修复工具中要用以棕树皮编扎制成的“棕刷”等等。
4.2 注重纯手工操作的精细度
古籍修复作为一种传统手艺,需要诸多精细的手工操作功夫。如“补书叶”时,用笔在破损处或孔洞周围涂上浆糊,补上纸,然后将多余的补纸撕下,而余留的补纸最好控制在孔洞周围2毫米左右。有时因虫蛀,一张书叶上就有几十个破损的小洞,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来修补,以保障每一个孔洞的修补都做得精细。又如,在修补后的复原阶段,需要将多余的补纸依书叶边缘剪齐,不是用机器来裁剪,而是要靠手工“持剪子”的功夫来细致地修剪。剪齐后纸边没有毛茬,光洁整齐,与相邻书叶叠在一起,书叶边缘吻合,误差不超过1毫米。再如,在“齐栏”这一道工序中,完全要靠手工把整本书书口的栏线对齐。这需要眼力的准确度及左右手灵活的配合,在每一个书叶之间作细微的调整。此外,如敦齐书口,误差应小于0.5毫米;扣书皮需大小合适,把书芯四周盖严,不露白边,误差小于1毫米;订书眼的位置、距离需适当,订线后各线段连在一起成为一条直线,误差小于1毫米。诸如此类,这种手下功夫的精细度,诚如明人周嘉胄所谓“良工须具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它一方面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内在心性的修炼。如果心能够安住当下的每一个过程,不急躁,不急于求成,而且怀有对古籍真正的热爱,便可用心呵护至宝,在修复中达到心性的清净明觉,进入艺术创造的体验。
4.3 注重修复实践经验,并随时灵活应对调整
以修复用纸这一道工序为例。因古籍书年代久远,每种书所用的纸张都有其特点,或薄或厚,颜色或白或黄,或深或浅,各自不一,即使在一部书中也会存在书页颜色的多种变化。因此配纸染纸工艺就有各种灵活措施。如我馆修复程砚秋“禦霜簃”戏曲抄本专藏时,其用纸有发白、偏黄、偏红等多种颜色。修复配纸时,我们做了多种实验:纸张上,选用竹纸和毛边纸;染料上,尝试矿物质染料——主要用赭石,加少量藤黄、墨汁、骨胶,和植物性染料——用普洱茶、红茶和橡碗子;染纸工艺上,试验了“排刷法”、“拉染”、“浸染”多种手法。在整个过程中,不断调试染料的用量、水的比例、浸煮的时间等各方面因素。最终,试验出用橡碗和红茶混合使用的效果最佳。橡碗染出的纸较黄,红茶染出的纸较红,实际操作中灵活调配二者的比例,以得到符合要求的红黄色调[4]。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修复技术往往不强调绝对的标准,不严格依据数值规律,而是注重每一次实践的具体情况,在一种看似随意的状态中来达到相对准确的控制。这其中当然包含一定经验积累的稳定性,但确实在每一次中又有相当的灵活度。因此,它一方面来自切切实实的试验,而得到可靠的经验;另一方面,每一次经验的积累又不能作为固定的模式来简单套用,而是化作整体把握事物的智慧,来有效引导每一次精微的控制。这也正是古籍修复作为一门传统手艺,其学习与传承的难度所在。
4.4 注重中国传统思维智慧
古籍修复技术在传承中保留了许多特有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这些处理方式背后蕴含着中国传统思维特征。如果深入体会,会发现中国古人的诸多智慧,它是与西方思维模式及其衍生的方法论完全不同的。以“定书眼”为例。最常用的操作方法是:取一张纸对折(任意方向)一下,再折成一个直角,直角边向右靠齐天头和书背,以天头部位为二,书背部位为三的比例,确定靠近书角部分第一个眼的位置。再用锥子按住中间,把折成直角的纸折向左边,按照已经定好的第一眼的位置扎第二眼的位置;继续把折纸向右对折,依照第一眼的位置扎第三眼;最后把折纸向右展开,原已穿过折纸扎透的书眼就是第四眼的位置[5]。
可见上述方法,从确定第一眼的位置之后,通过折纸方向的变化,就可巧妙得出第二眼、第三眼至第四眼的位置。这种方式重在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以最简洁的方式,以一制胜。而且借助一个具体形象的物来“比量”,不论书之大小如何变化,其间的比例关系是相对不变的。因此其方法就不需要每一次去计量书的全长,再换算各个眼之间的具体分寸。这正是一种中国传统思维的处理方式,它不依赖于精确的计量和细密严格的数学计算,而是重在从宏观把握比例关系,通过契入整体的和谐感来解决问题。诸如此类,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体会传统技术背后的思维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继承保留中国传统智慧,再有效地结合现代手段加以利用。尤其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从表面将一些传统技术视为不科学的,甚至看成落后的而抹杀,一味要用现代科技及机器操作来代替。实际上,传统技艺中还有很多是现代手段不可替代的东西,而且它们往往是更加便捷而又有灵活度的。
综上几点,可见传统古籍修复并不是一门机械操作的技术,而是一门需要灵性的艺术。这些具体细微的修复环节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需要体会传统文化的宝贵性,才不至于在简单的形式中失去对其内在灵魂的理解。因此,古籍修复职业实际上具有广阔的前景,如以这些传统手工操作即可开拓出多种心性的修炼,其内涵丰富的文化特质皆可深入开发。优秀的修复人员并不只是一般的职业技工,而应具备各方面综合素质,甚至是富有古籍研究及艺术创造潜力的高级专业人才。如果我们能从这些方面来建构古籍修复文化,将大大提升修复行业的价值和定位,从而带动更多人才加入到这样的队伍中,逐步解决修复人员缺乏、修复文化之传承等问题。
小结
上文从人员管理、工作计划、工作程序、修复技术4个方面,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实践做了梳理与总结。这其中的一些经验模式不仅仅局限于本馆的古籍修复工作,而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古籍修复工作特征的思考,希望增进对行业的认识及相关问题的理解。基于目前的状况,我们的修复工作本身还有很多不足,随着国家与学校对古籍的日益重视和支持,学校将于2012年启动“古籍新馆”建设,这将为我们全面提升改善古籍保护与修复等各方面工作创造最好的机遇。在物质条件上,新的古籍馆将会实现理想的空间环境与良好的设施条件等。如书库面积、书柜设置、温湿度控制、灭火设备等方方面面,将按照古籍保护标准来全面建设。修复工作将从原先工作间狭小简陋,功能混杂的环境脱离。计划建设新的修复实验室,可含处理间、仪器间、密封间。修复工作室,含操作间和材料库。从而使空间充足,作业明细。各项设施齐全便捷,如消毒系统、上下水设施、动力电系统等皆按照安全标准。在修复技术上,我们以保持和重视传统工艺为基础,可适当发展一些新技术,如纸张去酸技术等,并计划引进一些先进设备,如卧式拉力机、耐折度仪、纤维质量分析仪等检测仪器,以利更严密地展开对修复工作的学术研究。在修复管理上,将进一步增强科学化与规范化管理。如贯彻实施古籍修复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增加修复档案管理的精确性与完整性,创建共享平台,使修复工作不仅停留在低层次技术上的摸索,而是在协作中相互促进提高,拓展修复研究的学术深度等。古籍修复工程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继续努力做好本馆的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并以自身的实践不断拓展对古籍修复技术与文化的探索。
1 吴晓云.程砚秋禦霜簃藏书修复札记.见: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33
2 张志清.浅谈古籍修复的科学化管理.国家图书馆学刊,2004(2):60
3 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112
4 吴晓云.程砚秋禦霜簃藏书修复札记.见: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35
5 杜伟生.古籍修复技术工艺流程.见: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2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520
Exploring the Conservation Treatments of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Yang Fen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treatments of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the paper summarizes some experience from aspects of staff management,work pattern,working procedures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features to be abstracted in the four dimensions,and the author also reflects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conservation technique,conservation management,the heritage of conservation culture and so on.
Conservation Treatments of Pre-modern Chinese Books;Conservation Technique;Conservation Culture;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book=109,ebook=206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2012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