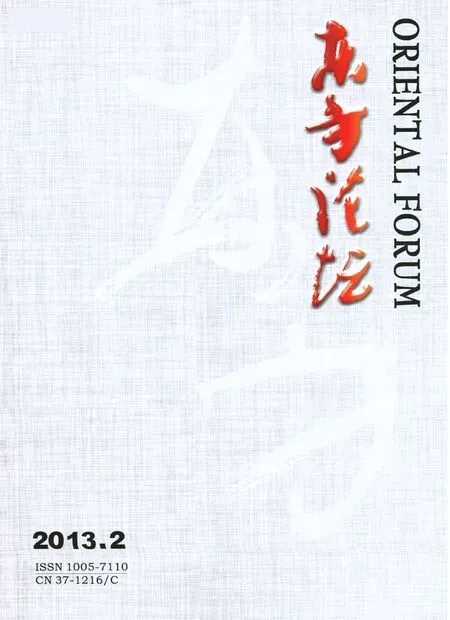关于《走读胡适》及传记的写法
2013-03-27贾振勇
贾振勇
在现代文人中,胡适之可谓提倡传记写作的最知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不但极力鼓吹,而且身体力行。从17 岁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开始,写作传记的癖好,如影随形的几乎伴他一生。
他写传记还有个特点,就是不挑食。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往往被学识渊博的胡博士信手拈来:国外的比如《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康南耳君传》;国内的就更不用讲,从《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朱敦儒小传》、《吴敬梓传》、《菏泽大师神会传》,到《许怡荪传》、《李超传》、《高梦旦先生小传》、《丁文江传》,无论是古之贤者还是今之闻人,凡是能兴会所至者,都可走入他的笔下。这仅仅是标上了“传记”名目的,还不包括他那些以考、述、论、辩、记乃至年谱等形式出现的“变形”传记;他不但写真人,还写虚构的人物传记,比如《差不多先生传》。当然,他老人家更不会忘记给自己写传,比如《四十自述》,再比如虽非亲自捉刀但颇具胡氏风采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译注)。
在胡适写的传记中,字数最多、影响较大的是《丁文江传》。这篇传记以后引来了李敖的挑剔。胡适说李敖“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此话真意何在暂不评论,两个忘年交虽惺惺相惜,但英雄不折腰之才高气傲应该是难免的了。所以,自视“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的李敖如果不挑剔,也就不是李敖了。李敖的确眼尖,在一番热捧之后,笔锋就转向《丁文江传》的缺点,除了点出“引录史料与原文颇有出入”、“偶尔有小错误”、“引语来源不能注出”、“有些地方失之太略”这些貌似轻描淡写的问题外,更是直奔命门:胡适总是离不开他那“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不能“写一部文学味道较浓一点的传记”,他鼓吹一辈子传记文学,然而除了《四十自述》中的《我的母亲的订婚》“算是比较有点文学味道的”,“剩下的恐怕都是些‘历史癖太深’的作品了”。[1](P157)
李敖之所以如此指摘,盖在于他既有为胡适写传的夙愿,更有借胡适一展才华的傲气,于是他写了《胡适评传》。古人说五十步笑百步,李敖确有步胡适后尘之嫌,不但《胡适评传》象胡适的不少大作一样是半拉子工程,就连“历史癖太深”的特色也照单全收。与胡适所写传记不同的,大概是俏皮和文采了。以至于笔者至今还记得他在那半拉子《胡适评传》中的最后笔墨:“上海埋葬了这个不到十九岁少年人的梦,埋葬了他的欢笑与眼泪、上进与堕落,埋葬了他那永不再回的青春,也埋葬了他那‘胡洪骍’的名字。从此以后,人人都不叫他‘胡洪骍’了,人人都叫他‘胡适’。”[1](P338)李敖不愧为才子,这段话笔者印象之深,以至于能在课堂上随口背诵。无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文学作品,一两句神来之笔的点评,往往胜于千言万语的铺陈。
之所以拉拉杂杂写这么多貌似不相干的话,乃是因为最近读姜异新女士《走读胡适》触发的。由于胡适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耀眼光芒,关于他的传记当然要汗牛充栋。那些传记大都是学者写的,自然就有学院派的特点,比如材料充分、考证详实、全面周到,其中的佼佼者也成为研究胡适的权威之作。这样的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容小觑。但问题是“历史癖太深”的传记是否太多?而“文学味道较浓一点”的是否较少呢?我们由此得到了很多关于胡适的知识和材料,可是胡适的神采是否能水涨船高呢?我的感觉是,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或者是具体的事例,能“撄人心”者比较罕见。
可是,当从网上购得姜异新女士的《走读胡适》并饱览一遍后,大有耳目一新之感。要知道,学界对胡适研究的水平,比鲁迅研究的水平差不到哪去,能让人有新鲜感实属不易。不必说这本书的文采,早就听闻姜异新女士是才女,这部书只不过是这个听闻的验证而已;也不必说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能在众多胡适传中让人侧目,非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不能达到也。我感兴趣的是,这部书竟然叫《走读胡适》。沿着传主的人生地理空间的位移,追随传主的足迹,追古思今、指点江山,实现了真人版大穿越,真让人艳羡不已:我当年写《郭沫若的最后29年》,就怎么没有机会沿着传主的足迹走一遍呢?
“走读,不只是走,更要读,读出新意,而不是穷搜未尽的史料”,姜异新如是说。这部别致的胡适传如何有新意,我就不啰嗦了,相信很多的读者会比我更有眼光品评。我要感慨的是,且不说这部传记披露的一些史料填补了某些空白,关键是她对史料的拿捏和运用,有恰到好处之妙。史料不是无情物,如何化作春泥更护花?如何让史料活起来,甚至创造性地运用史料,尽显传主之风采,这是很多传记作者面临的难题。然而,姜异新女士以“走读”的方式,“真诚地邀请胡适住在心中”,轻描淡写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不但走读出了胡适的风采,走读出了历史的深意,而且也具有了“历史的贯通之气”。
姜异新在自序中记载了一个朋友的意见:“你这是在写胡适吗?你这不是在写你自己吗?”质疑者大概还是在尊奉那个所谓“客观性”的述史理念,以至于有此一问。我要是说的是,我们所崇信的那个“客观”的历史及历史人物,早已遥遥而去,我们已经不可能重回历史长河,只能根据历史的遗迹来模拟一个所谓“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形象。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既是无奈也是必然之事。是否能写出传主的神韵,是否是一部“写生传神”的传记,才是问题的关键。
倘若胡适地下有知,他对《走读胡适》会作何感想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早已意识到自己将成为耀眼历史人物的胡适,是期待有人能将他“写生传神”的写出来。他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就为传记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而且倡言:对近代史上的洪秀全、胡林翼、郭嵩焘、李鸿章、俞樾、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骞、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等“关系一国的生命”的人物,“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2](P596)其实,这何尝不是在告诫后人:对他胡适这样一个也是“关系一国的生命”的人物,为他写传亦应如是?
《走读胡适》自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如学术评判那样来写胡适传,但游踪所涉、笔墨所至,却往往在颇富情感的叙事中,尽显一个历史人物的卓越和荣耀。借用苏轼的话来说,《走读胡适》“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其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走读胡适》是否写生传神,还是让时间来鉴定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也是写传记的一条“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的道路。这种写法的价值,在我看来,不亚于学院派的高头讲章。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也。学院派的胡适传,自有学院派的气度,《走读胡适》对胡适的心领神会,对胡适的心有戚戚,使它别具风采。李敖写《胡适评传》,花大力气做了那么多考据,我想他是为了证明他不但是才子,还大有学问。但心高气傲的他不会耐着性子写下去,以至于开篇不久就煞尾。他的那些繁琐的考据我没记住多少,反而不时闪现的神来之笔至今难忘。《走读胡适》恰当地运用史料,加之以文采斐然的笔致,加之以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式关照,无疑尽显了“本色胡适”。所以,这部传记的价值自有公论,不必我来说。我想说的是,《走读胡适》给我的最大印象,恰恰就是它的笔致和个性:边走边想,边想边读,边读边写,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个鲜活而“温热”的胡适,就此从一百多年的尘埃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1] 李敖.胡适研究[M].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2006.
[2]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 第4卷[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