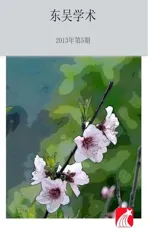论曾朴小说的现代精神
2013-03-26申明秀
申明秀
翻译与创作是晚清小说齐头并进的两大潮流,晚清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在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中,曾朴无疑是最“现代”的作家,因为他不仅精通法文,而且还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曾朴天生浪漫的气质,与法国现代浪漫主义可谓一拍即合,而强化了其思想的现代性色彩,其创作自然也带有鲜明的西方现代小说因子,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最早的开拓者之一,无怪乎郁达夫称其为:“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的这一位最伟大的先驱者”。①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50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五四新文学兴盛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像曾朴那样的更早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正如王德威所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②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五四文学不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迸出来的,没有晚清文学的长期孕育,五四新文学的产生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一、曾朴的浪漫气质与现代思想
大凡文学家皆有浪漫气质,只是浓淡不同而已。浪漫是灵魂的一种向上的冲动,而与庸俗为敌,浪漫者重想象与情感,活在自己圣洁的精神王国里,而与世俗难以融洽甚至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浪漫是一种先天性气质,而不是后天习得的。从古代的屈原、李白、龚自珍到现代的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再到西方的雨果、歌德、普希金,浪漫气质造就了一个个天才般的伟大诗人与作家,照亮了古今中外文学的天空,而成为人类文明的脊梁。《诗法源流》云:“诗者,原于德性,发于才情,心声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学而神意不可学。”③吴乔:《围炉诗话》(1-2册),第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所以前人感叹杜诗可学,而李诗不可学,其关键的一点就是李白难以复制的浪漫气质。同样富有浪漫气质的郁达夫可谓曾朴难得的知音,虽然他们交往不多,但曾朴的浪漫天性却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脸上的线条,当他微笑的时候,表现得十分地温和,十分地柔热,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他的笑里,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像春风似的慰抚。有一次记得是张若谷先生,提起了他的《鲁男子》里的某一节记叙,先生就露现了这一种笑容;当时在他左右的人,大约都不曾注意及此,我从侧面看见了他的这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于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这一种感想,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和我一样。”①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49、72-7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曾朴虽然也是一个传统文士,可他自小就展示出与众不同的浪漫个性与气质,正如他晚年所自我总结的那样:“我的一生完全给感情支配着,给幻想包围着。在幻想包围中,我绝不能满意眼前的环境;在感情支配下,我就充实了冲破篱笼的勇气。”②时 荫:《 曾朴及虞 山作家 群》,第49、72-73页, 上海:上海文化 出版社 ,2001。首先,少时的曾朴就不喜欢读枯燥的四书五经,而嗜好形象化的小说。《曾朴年谱》记云:“十三四岁时,经名儒潘子昭先生的指导,开始课艺的研讨,然先生笃好文艺,每背人窃读名家说部以及笔记杂集,当时目为斫丧性灵的书籍,虽师长叱责不顾焉。实则先生的文学基础,就在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动中打定的,可是师长都不知道。”③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52、152-1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在曾朴的自传体小说《鲁男子》中,作者这样描写自己早年的读书情景:“鲁男子生性十分聪明,只是十分淘气,记性很好,只是有些贫多嚼不烂,悟性也还可以,只是常常见异思迁。开首读《大学》、《中庸》时候,糊糊涂涂不过依着先生教的腔调,并不是读,是唱;读到《论语》、《孟子》,便觉厌烦;后来换上《易经》、《尚书》,越读越不懂,不是厌烦,简直怨恨,心里不自觉地起了反抗,不愿意依头顺脑做鹦哥般学舌了……在那时候的鲁男子,唯一痛苦是读书,然唯一快乐却是听书……鲁男子渐渐地觉得听人讲书不大满足了,要自己看书,不免在他祖母书桌里偷了几种他看得下的,像《来生福》等类的唱本,藏在书桌抽屉里,得空就偷偷看。后来唱本看腻烦了,进一步换看平话;从《封神榜》,《列国志》,《西游记》,《镜花缘》,一直看到半文言半白话的《三国演义》。”④曾朴:《鲁男子》,第13-14、14-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再然后就是偷看他父亲收藏的《红楼梦》与《野叟曝言》而被父亲训斥。爱听书,爱看小说,这一切还只是曾朴浪漫天性的初步体现。
重感情与好想象是浪漫气质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曾朴年谱》有云:“先生诚挚的热情,已找到了一位恋爱的对象——是他一生最倾心爱慕的恋人,是他到六十多岁暮年时还惓惓需于怀的爱宠——不幸宗法的社会,不容许他那种奔放热情的流露,结果,他是被斥为狂妄,为浮薄,而遭受了恋爱上没世难忘的创痛。这个创痛,他永远隐忍着,直到五十多岁创办真善美书店的时候,才借着《鲁男子》第一部《恋》,以小说的形态,尽情宣露了出来。所以这一部小说,可以算他青年时期的自传,也可以算他晚年回忆的忏悔录。”⑤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52、152-1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曾朴自己后来也在日记中回忆道:“我幼年时,感情极丰富,性欲也极强烈,我和T的恋爱,只为尊重她,始终保守着纯洁,没有犯她的童贞,这是真的,但我的受苦是大了……后来我和T婚姻问题,已绝了望,我病了一场,精神颓唐到万分。”⑥曾朴日记.http://eltonzeng.blog.hexun.com/9202954_d.html.而只有读了《鲁男子》之后,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曾朴感情真挚而强烈的程度,跟歌德的自传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曾朴对自己的情感与想象力也深以为然:“鲁男子的同情心是极丰富的,讲到《岳传》,自己便认作岳武穆,讲到《征东传》,自己便算是薛仁贵,唱着《天雨花》,好像就是左维明,唱到《安邦志》,好像就是赵安……鲁男子的想象力本来非常强盛。他把几年来偷看的书得到的印象,从前是想拿动作来表现的,现在却集中起来,搅合在‘自我’的范畴里,只想拿想象来在脑海里逐日一段一段地表现了。”⑦曾朴: 《鲁男子》 ,第13-14、14-16页,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充满真诚与热情乃至激情,重感性而轻理性,可谓浪漫气质的重要标签,曾朴的为人处世无疑是这种浪漫个性的生动注脚,曾虚白这样描写父亲:“这是先生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对事对人总是十万分的专,十万分的诚。凭着他一股热情,凡是他爱好的,他可以舍弃一切,牺牲一切,非得到他自己的满足,不肯罢休。在这一点上,他是勇敢迈进,绝对没有妥洽性的。”①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63、160、179-180、1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比如曾朴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雨果的迷恋,在阅读、翻译雨果等法国作家的作品时,他异常投入,如痴如醉,乃至大病一场:“我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②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15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再比如他当年进总理衙门受挫被侮,而愤然出京,《曾朴年谱》这样写道:“连夜套车襥被出都,悻悻之情,不能自已也。出东便门,行若干里,适值永定河发水,田野漫溢,不辨轨迹,乃弃车乘马,宁颠踬以前,不愿迥辔再入都门矣,当时先生的愤懑如此。一日行程,时云暮矣,行抵杨村附近,先生实已困惫不堪,据鞍朦胧,不觉竟打起盹来,翻下马鞍,跌在一二尺深的水淖里。”③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63、160、179-180、1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像曾朴这样的举动显然就不仅仅是年轻气盛的问题了,而主要是性格使然。
曾朴从仕途卸任后还到上海创办真善美书店与杂志,其目的并非是要赚钱,而是其浪漫的文学天性所致:“开书店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结纳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式沙龙的空气……先生于著述之余总喜欢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朋友,作一种不拘形迹的谈话会。那时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满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岁三十岁的青年,可是先生乐此不疲,自觉只对着青年人谈话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个老少年。”④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63、160、179-180、1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而晚年经常生病的曾朴又以种花怡情。总之,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创作翻译,曾朴身上始终都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质。
浪漫气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世俗的反抗与决裂,表现在曾朴的身上就是其鲜明的现代思想。从屈原“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自放,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傲,再到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的狂狷,无不是其浪漫气质的自然流露,而一致地表现为与世俗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与叛逆人格。诗言志,从曾朴青年时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倾听到他与屈原、李白心声的强烈共鸣。曾朴虽然迫于父命,也曾屡入科场,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却是发自内心的反感与厌恶,而有会试时故意泼墨污卷,写下《试卷被墨污投笔慨然题二律》后昂然离场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举,诗中“功名不合此中求”之句更是明白地宣告了自己跟传统与世俗的彻底决裂。他在《赴试学院放歌》中就表示了对汲汲于功名的士子的鄙视和自己的无奈:“丈夫生不能腰佩六国玺,死当头颅行万里,胡为碌碌记姓名,日夜埋头事文史!文章于道本未尊,况又揣摩取金紫,笑我今亦逐队来,未能免俗聊复尔。”⑤时萌:《曾朴研究》,第1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曾朴对传统的反抗,有着多重的原因,浪漫气质只是内因,晚清腐败的时代大环境和宗法社会对他初恋的扼杀则是两个重要的外因,而西风东渐则让几乎窒息的曾朴找到了新的精神出口。
曾朴特别反对封建迷信,居家守孝期间,曾因办学而与地方守旧势力发生过冲突,据《曾朴年谱》记载:“常熟素称文风最盛的一邑,据父老传说,文化的所以盛自有它风水的关系,因为在城东有一座方塔,这是激发文风绵绵不绝的建筑,这座塔不坏,常熟的文人是不会断的,一旦崩坏,文风歇绝,可以预卜,凡是老辈多确信之,所以修塔就有了指定的专款。曾朴先生当然不信这些迷信的谰言,以为办学校才是真正振兴文风的事业,这一笔无稽的浪费,正可移来补充经济十分拮据的小学经费,于是据理力争而引起了老辈们群起的排击,甚至联名电请省当局,驱逐先生出境,说先生是一个只会做小说的浮薄少年,怎可叫他担当办教育的重任。”⑥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63、160、179-180、1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而《孽海花》开篇就直斥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与野蛮:“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⑦曾朴:《孽海花》,第1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鲁男子》中借云凤之口继续抨击祖宗及因果报应等迷信的荒谬:“祖宗不是已死去的人吗?是失去了意志,消灭了思想,腐烂了血肉,人们永看不见的一具骨架,怎么会来管我们活人的闲账?拆穿西洋镜,不过古来几个聪明人的暗弄玄虚,和如来、天主一样,造成一种无形的偶像,来做驯服子孙的一架永不开栅的鸟笼。”①曾朴:《鲁男子》,第192-193、193-1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不仅如此,还进一步以现代科学精神来重新定义人的姓氏:“我不懂什么叫作姓,一个姓不过人群里一种分别的符号,和一、二、三的数目字一样的用法,没有重大意义。譬如开一爿店,挂一块招牌,便由主顾的辨认,至于店的本身,有招牌也是店,没有招牌,还是店,换一句话说,有姓是这个人,没有姓还是这个人,丝毫没有变动。后来姓的尊重,就像开店一样,有了资本和声名,一有这些,便成了物质的传授,所以姓也有了遗产和族望的遗传。像我呢,根本就不需要遗产和族望,只知道保有我的意志,做强盗也是我,做圣贤也是我,若讲到女性,我要做做娟妓也可以,我要做做修女或童贞也可以,都不干人家一点儿事;人们偏要把竖、画、点、劈,构成没灵魂的姓字,来拘束我的自由,我实在死也不懂。”②曾朴:《鲁男子》,第192-193、193-1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虽然曾朴后来研究佛经后也能从佛教的视角来阐释自己的作品:“我如今且把佛说来作我书的注脚,我说的外现环境,就是五蕴里的色蕴,内在环境,就是五蕴里的受和想二蕴,善恶的行为,就是五蕴里的行蕴,人生的认识,就是识蕴,人生跳不出五蕴,所以也跳不出环境。无论你大英雄,大奸慝,惊天动地地干,费尽气力,只得到苦谛,无论你大哲学家,大破坏家,翻江倒海的说,绞尽脑筋,还是遍计所执。本来整个的人生,全是承苦器,我不过把《鲁男子》来作苦器的总模型,在这苦器里渗漏出来点点滴滴的血泪罢了。”③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4、3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但他反对迷信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面对胡适指责小说林本《孽海花》第八回有关烟台孽报含有迷信意味的批评,曾朴的《孽海花》真善美本不仅删去了相关的迷信描写,将原版的“耳鬓厮磨的端相的不了,正在出神,忽然见彩云粉颈中一线红圈,明若胭脂,细若丝缕,不禁诧异道:‘你颈上红丝一条,是染的么?’彩云笑道:‘这是我胎里带来的,擦也擦不掉,染的哪里有如此鲜明呢?’雯青听了,垂下头去,颜色渐渐惨淡,不知不觉两股热泪,从眼眶中直滚下来”直接删为真善美本的“耳鬓厮磨的端相的不了,不知不觉两股热泪,从眼眶中直滚下来”,④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而且还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的序文中用西方文学的话语专门对此作了回应:“我以为小说中对于这种含有神秘的事是常有的……近代象征主义的作品,迷离神怪的描写,更数见不鲜,似不能概斥它做迷信。只要作品的精神上,并非真有引起此观念的印感就是了。”⑤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4、3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可见,曾朴一直都是站在现代科学与西方文学的立场上反对封建迷信的,而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现代文明姿态。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充满着揭露与批判封建社会的离经叛道的现代精神,曾朴主要就是被这一点所吸引而迷恋法国现代文学的,他选译雨果的戏剧代表作《欧那尼》,正是因为该作对封建统治阶级大胆的批判,而对雨果另一戏剧名著《吕伯兰》的翻译,也是如此:“那时我正服务于南京,我时时感觉着执政的贪黩,军阀的专横,比起西班牙查理第二时代很有几分相像。我被这种思想驱迫,再拿吕伯兰特拉姆反复的诵读,觉得它上头的话句句是我心里要说的。”⑥病夫:《〈吕伯兰〉自叙》,《真美善》1930年第6卷第3号。
对曾朴的浪漫人格与现代思想,他的亲人们其实最有发言权。曾朴去世后,他的儿子曾虚白等一起作了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长篇祭文《哀父》,其中有一段文字可谓曾朴一生的生动写照:“爸爸,人家说您是政治家,是理财家,可是我始终认定您是一个文学家,是现代文坛最纯粹最伟大的浪漫文学的宗匠;您思想的超越现实,您热情的弥纶万象,再加上处事待人的专恳诚挚,对于物质享受的淡漠寡欢,遇到危难时的勇往直前,爸爸,您的一生是浸淫在自己幻想所结构的天地中,您的生活是包裹在自己热情所打起的浪潮里;这一切浪漫文学必具的特殊色彩,您有生时就挟之以俱来,求之世界文坛,只有法国的嚣俄(雨果)可以跟您作并肩的比拟,这就难怪您恋恋于这大文豪的生活和作品,备致您倾倒之忱了。”①②③④⑤ 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74、36、84、80、16-1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曾朴,诚可谓中国的雨果。
二、《孽海花》: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
一九〇五年小说林本《孽海花》问世后,好评如潮,一时轰动,正如曾朴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说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一出版后,意外地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赞扬的赞扬,考证的考证,模仿的、继续的,不知糟了多少笔墨,祸了多少梨枣。”②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74、36、84、80、16-1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而且又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孽海花》,无疑是清末小说大潮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而赢得时人频频叫好:“近人所著小说,以东亚病夫《孽海花》为最著”、③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74、36、84、80、16-1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④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74、36、84、80、16-1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到了五四时期,胡适一反常论,大谈《孽海花》的短处,而后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孽海花》的评判则更为理智与冷静,将它归入谴责小说之流,只是加上了“结构工巧,文采斐然”的赞语。事实上,无论是褒的还是贬的,都没有涉及到要点,而有误读之嫌。原因是,曾朴的现代文学思想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读者的接受水平,而胡适、鲁迅等评论《孽海花》时又不甚清楚曾朴的法国文学背景。除了其法国文学老师陈季同,曾朴可以算是晚清真正了解西方文学的第一人,林纾虽翻译颇早,但因其不懂外文,对西方文学实际上是不甚了了,所以当年以法文研习西方文学的曾朴,自然就经历了长期没有知音的苦恼:“我辛辛苦苦读了许多书,知道了许多向来不知道的事情,却只好学着李太白的赏月喝酒,对影成三,自问自答,竟找不到一个同调的朋友。那时候,大家很兴奋地崇拜西洋人,但只崇拜他们的声光化电,船坚炮利;我有时谈到外国诗,大家无不瞠目结舌,以为诗是中国的专有品,蟹行蚓书,如何能扶轮大雅,认为说神话罢了;有时讲到小说戏剧的地位,大家另有一种见解,以为西洋人的程度低,没有别种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说戏剧;讲到圣西门和孚利爱的社会学,以为扰乱治安;讲到尼采的超人哲理,以为离经叛道。”⑤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74、36、84、80、16-1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所以其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学色彩的《孽海花》虽一时洛阳纸贵,但真正的读者却迟迟没能出现。
金松岑愿意写一本政治小说,经过曾朴之手后,却变为一部历史小说,而且跟吴趼人《痛史》等传统历史演义小说不同的是,《孽海花》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现代历史小说的模式来进行创作的,正如学者杨联芬分析的那样:“《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是一种‘风俗史’的叙述,而且是一段‘无道德’、‘非英雄’的叙述。”⑥杨联芬:《〈孽海花〉与中国历史小说模式的现代转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而这一点恰恰是当时读者一致的盲区。欧洲现代历史小说由英国司各特首开先河,形成了以虚构的故事来再现历史的创作模式,而风行于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继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风靡欧洲之后,雨果的一批具有强烈当代意识与社会关怀的法国现代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等相继问世,创造了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辉煌。与法国文学有着不解之缘的曾朴,自然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特别是雨果作品的影响,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抛开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写法,所以与雨果小说重虚构不同的是,《孽海花》更强调史实的严谨:“这种强调写实的创作理念,使得曾朴的小说能很好地把清末民初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历史叙事同时纳入小说文本中,生动映现了社会的历史政治变迁和文化转移。这是借鉴了西方,尤其是法国十九世纪历史小说的模式。”⑦吴舜华:《曾朴与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萌芽》,《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为了防止人们误读,曾朴不得不撰文说明《孽海花》的创作方式与宗旨:“这书的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地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①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7-38、40、38、36-3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也就是说,《孽海花》不像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那样,通过塑造英雄人物等方式从正面进行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像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那样,通过对普通人物命运的抒写从侧面去展现广阔的历史画面,只不过《孽海花》更注重人物与情节的真实性。《孽海花》大到历史事件,小到人物安排,无不讲究真实,作者在小说第二十一回开头也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艺术追求:“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只能将文机御事实,不能把事实起文情。”②曾朴:《孽海花》,第16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时人爱读《孽海花》,其独特的真实性应该是主要原因,正如蔡元培所分析的那样:“《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合我的胃口了,它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从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大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③时 荫:《曾 朴及虞山 作家群》 ,第37-38、40、38、36-37页,上 海:上海 文化出版 社,2001。一九二八年曾朴之所以要修改小说林本《孽海花》,原因之一就是原本 《孽海花》部分内容不符史实:“雯青中状元,书中说明是同治戊辰年,与乙未相差几至三十年,虽说小说非历史,时期可以作者随意伸缩,然亦不宜违背过甚,所以不得不把它按照事实移到中日战争以后。”④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7-38、40、38、36-37页, 上 海: 上海 文 化出 版 社,2001。曾朴曾想续完《孽海花》,可是一方面原因是年老精力不济,另一方面是他这样真实风格的写作太费事,只坚持续写了几回就不得不放弃了:“病夫的《孽海花》在这一期里出现了。可是抱歉得很,还只有半回。理由很简单,只因这一回太费事。这里所叙的是甲午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人时吾国民族的反抗事实。看看不过几千字,作者却翻遍了十几部书,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做成的。他常说做《鲁男子》乐,做《孽海花》苦,做历史小说不容易,令人不能不佩服大仲马的伟大。”⑤时萌:《曾朴研究》,第1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胡适曾因结构等问题对 《孽海花》颇有微词:“《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文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适以为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⑥胡适:《致钱玄同书》,《新青年》第3卷,第4期。不仅胡适,包括鲁迅都曾指责晚清谴责小说一味模仿《儒林外史》的连环式结构,其实这有点冤枉晚清作家了,因为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小说结构模式,主要是为了适合报刊连载的需要,而不是有意要重复《儒林外史》。事实上,《孽海花》则更为冤枉,因为它的结构显然比《儒林外史》的连环式结构精致、复杂,尽管事隔了十多年,曾朴还是针对胡适的批评作了回应与辩护:“他说我的结构和《儒林外史》一样,这句话,却不敢承认,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线;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浪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他没有复杂的结构。”⑦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7-38、40、38、36-3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与其他谴责小说不同的是,曾朴的《孽海花》不是先连载后出版,而是二十回一气呵成,直接出书的,它不仅与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标准的连环式结构不同,而且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来串联全书的结构也不相同,因为“九死一生”在作品中主要是起着连缀话柄的作用,而《孽海花》中的金雯青与赛金花的命运故事既结构了全篇,同时更是作品的主人公,而有着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常见结构的痕迹。显然胡适与鲁迅对《孽海花》的批评都显得有点草率而欠妥。
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中,曾朴的思想无疑是最激进与现代的。李伯元、吴趼人、刘鹗虽然都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其中刘鹗又特别热衷于西方的科技与经济文明,积极提倡实业救国,可是他们都反对在中国搞西方激进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力主较温和的维新与改良,这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老残游记》、《文明小史》中有关革命者的叙事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而吴趼人则始终强调道德救国,只有曾朴因其浪漫的个性而倾向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在《孽海花》中有所表现,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民主斗士。曾朴曾积极参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的筹划活动,只因回家料理父亲丧葬,才逃过一劫,在常熟居家期间,不仅竭力解救富有革命精神的朋友沈鹏,而且还热情款待日本革命亡命者金井雄,在办教育时又与地方传统势力进行斗争。在上海从事文艺与出版事业的同时,曾朴就积极参加民众运动,颇有建树,据《曾朴年谱》记载:“在江浙一带,以张謇、孟昭常、许鼎霖、雷奋、汤寿潜为中西的预备立宪公会,是全国宪政运动的首创,而先生实在就是这个团体的中坚份子。后来沪杭甬铁路的兴建,政府方面正在进行英国借款,先生等这个团体,通电反对,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于是在味莼园开会,拟招集民股,以拒外资,那时候,先生与马相伯、雷奋等,激昂慷慨的演说,轰动一时,给久伏于专制淫威下的民众一股刺激性异常强烈的兴奋剂。及一九〇六年,安徽巡抚恩铭给革命党人徐锡麟所杀,浙抚张曾敭,得皖电,搜索党人,竟派兵往大通学校,围捕秋瑾,瑾被害,并株连许多人士,于是浙省民众大哗,积极进行驱张运动,政府无奈,下谕把张曾敭调抚江苏。时先生和上海一班同志以为浙省之所拒,宁可以苏省为藏垢纳污的所在,也就联名电请清廷,收回成命。风潮逐渐扩大,清廷为之侧目,曾密电捕先生等三人,先生屹然不为动,到底还是清廷屈服了,把张曾敭调到陕西,风潮才得平静下来。这是清末民众运动第一次战胜清室,先生实是主动的人物。”①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68-1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自民国进入政界后,曾朴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屡屡与军阀黑暗势力交锋,表现了他一贯正直与抗争的本色。
《孽海花》虽写的是陈年旧事,却表达了作者先进的政治思想,对此阿英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即李伯元、吴研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盖李伯元与吴趼人之思想,虽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但始终不能跳出‘老新党’范畴,拥护清廷,反对革命。而《孽海花》则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②阿英:《晚清小说史》,第2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作品一方面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晚清社会的糜烂,一方面为革命大唱赞歌。《孽海花》使得革命党人第一次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晚清小说中,第二十九回勾勒了诸革命党人“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的伟岸风姿,其中对孙中山的描写更是光彩夺目:“一位眉宇轩昂、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面目英秀,辩才无碍”、“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③曾朴:《孽海花》,第254、254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而且还借杨云衢之口赤裸裸地宣扬了民主革命思想:“诸君晓得,现在欧洲各国,是经着革命一次,国权发达一次的了。诸君亦晓得,现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④曾朴: 《孽 海花》 ,第254、254页 ,天 津:天 津古 籍出版社,2005。另外,小说安排了相当的篇幅进行俄国虚无党叙事,看似冗笔,而实际却蕴含着启发中国革命的深意。还有作品中对赛金花和夏雅丽这两位新女性敢作敢为性格的刻画,无疑又为作品增添了几分现代色彩,而与一般晚清小说的传统叙事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孽海花》能自觉地运用现代小说手法,在清末小说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首先,曾朴能娴熟运用倒叙、插叙、补叙等西方小说常用的叙述技巧,而一改中国小说千篇一律的顺叙面目,这样的叙述革新在今天看来是极平常,可在清末还是让读者耳目一新,饶有趣味。其次,《孽海花》虽主要还是传统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但作者也尝试融进了西方小说的限制叙事,而更加贴近真实。如第三回就进行了一段限制叙事:“雯青坐着马车回寓,走进寓门,见无数行李堆着一地。尚有两个好像家丁模样,打着京话,指挥众人。雯青走进账房,取了钥匙,因问这行李的主人。账房启道:‘是京里下来,听得要出洋的,这都是随员呢。’雯青无话,回至房中,一宿无语……雯青听着,暗忖:‘怪道刚才栈房里来许多官员,说是出洋的。’心里暗自羡慕。”①曾朴:《孽海花》,第12-13、29、93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最后,就是描写手法上的现代突破。中国传统的小说描写大多是写意的,注重神似,即如白描也是最经济的写实,而西方小说的描写受科技文明的影响更强调形似,注重细腻逼真的写实,中西小说这一显著的差别引起了不少晚清作家的注意,而开始了中国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现代化进程。谙熟法国文学的曾朴当然会在创作中尝试西式的描写手法,《孽海花》中主要表现在心理描写与景物描写上。比如第十二回傅彩云初见德国军官瓦德西,其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心理描写:“彩云独自在房,心里暗忖那个少年不知是谁,倒想不到外国人有如此美貌的!我们中国的潘安、宋玉,想当时就算有这样的丰神,断没有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见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见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样的了。”②曾朴:《孽海花》,第12-13、29、93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孽海花》中也多次出现了西方现代小说中常见的那种大段写实的环境描写,如第十二回中关于沙老顿布士宫的景物描写:“彩云一到,迎面就见一座六角的文石台,台上立着个骑马英雄的大石像,中央一条很长的甬道,两面石栏,栏外植着整整齐齐高的塔形低的钟形的常绿树。从那甬道一层高似一层,一直到大殿,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中间是凸出的圆形屋。”③曾朴: 《孽海 花》, 第12-13、29、93页, 天津: 天津古籍出 版社,2005。其他如肖像描写等也有明显西方化的痕迹,而这样的写实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总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孽海花》都充溢着强烈的现代性,其雅俗整合的前卫性不仅超越了一般晚清读者的视野,即使放在五四文学的背景上,它也毫不逊色,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真正的伟大开端。
三、结语:“何必住上海?”
曾朴虽然一度从政,可他骨子里还是一介书生,一个浪漫到视文学为生命的赤子:“我不但信任文学的高尚,我看着文字,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宗教,只希望将来文坛上,提得到我的名,就是我最后的荣誉。”④⑤⑥ 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1、10、22-2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他不愿生活在灯红酒绿的上海,可是为了心仪的文学艺术,他只能牺牲自己:“上海是个商场,我在商业上是个惊弓之鸟,不愿再做冯妇的了。何必住上海?上海是政治的策源地,我于对政治,是厌倦的了,决定在五年内没有谈政治的可能,何必住上海?上海是个游乐场,我既不想嫖,又不好赌,京戏令我头痛,大餐也叫我倒胃,跳舞我不会,游戏场我怕闹,何必住上海?我所以舍不得上海的缘故,只为了一件事。上海是我国艺术的中心,人才总萃,交换广博,知觉灵敏,流布捷便,是个艺术的皇都;既想做艺术国里的臣隶,要贡献他的忠诚,厚集他的羽翼,发挥他的功业,光大他的荣誉,怎能离开那妙史的金阙呢?”⑤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1、10、22-2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如果说《孽海花》主要是展现了作者一腔积极入世的报国之心,那么《鲁男子》则袒露了曾朴矢志追求真善美的浪漫情怀,这两本小说虽都是未竟之作,但已足以表现曾朴那非凡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才能。曾朴在论述文学作品的真善美标准时这样讲道:“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改进的,不是保守的;是试验品,不是成绩品;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⑥时荫:《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第31、10、22-2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其实,这也是曾朴其人其文现代精神的具体写照,他的一生就是一曲真善美的华丽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