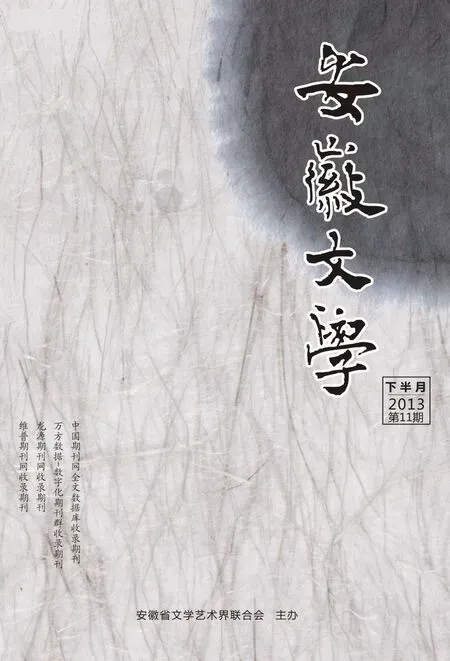论《一个人的圣经》的自审结构
2013-03-22牛婷婷
牛婷婷
论《一个人的圣经》的自审结构
牛婷婷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将同一个人物分裂为“你”和“他”两个叙述人称,二者超越时空沟通对话,形成了自审结构,历史的苦难书写得以升华为对人性的审视。
《一个人的圣经》 叙述主体 叙述声音 自审结构
高行健在《文学的见证》中说,文学必须以一种清醒的旁观者的个人的视角去呈现历史,才能避免流于控诉,而获得一种趣味、一种启发、一种灵悟。《一个人的圣经》审视了一段将亿万中国人卷入大灾大难的历史浩劫,但并不止于谴责,而是由历史书写展开对生命个体的肉身与精神困境的深度挖掘,于灾难和丑陋之中提炼出对生命的诗意之爱。小说抛弃了单一的历时性线性结构,另外建构了一个共时性的延伸,形成一种自审的结构,以此来寻找生命在历史时空中的坐标。在小说中,同一个人物分裂为“你”和“他”,分别承担共时性和历时性叙述视角。十年后的“你”作为一个逃亡者,逼视历史中的“他”,“你”与“他”相通,并与“他”进行对话,此外还有真正的叙述主体带着一双中性的眼睛在旁观“你”与“他”的分离与对话。
一 、“你”与“他”的分离
“你”与“他”是由同一个叙述主体裂变出的两种存在。 “你”与“他”有如下对应关系:

注:第7、17、18、26、33、35、36、48、52、53、56、60章有人称的局部变换,“你”和“他”在这些章节中直接相遇。
通过人称的区别,主体被分解开来,进而,“人与自我”的关系得以鲜明地呈现于文本中,这种“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一种内部主体间性,呈现了“人与自我”的对照结构。下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二、“你”和“他”的中介——日常/性
“你”逃亡后想要彻底将“你”与“他”割断。“你”爱上的是肉身,在肉身的沉陷中,在女人深邃的洞穴中挖掘到存在的质感。但同时玛格丽特丰腴、沉重又被施暴的肉身又能唤起 “你”沉淀在生命底部的痛苦,“你”再次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不能自已。
“你”在回忆中最先想起的是逃亡前夕与一个小护士的性爱。“他”在离开故国的那一刹那割舍不掉的不是乡愁,而是被施暴的情感与欲望的牵挂。“他”只不过是一条虫,是一个跳梁小丑,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掩埋,没有主义,没有理想,唯有肉身的感觉具体而真实。暴力给他带来的最鲜明的痛苦感受,反映在五个女子给“他”带来的肉体的困惑,“他”无法维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与这几个脆弱的、绝望的、分裂的女子短暂邂逅,没有爱情,发泄性欲与惶恐,并带着被摧毁之后的空虚和放纵。“他”在乱世中所追寻的只是欲望的正常满足,和活下去的安全感。然而被暴力所破坏、砸烂的恰恰是人的日常生活和性。
如此,“你”和“他”这两个分裂的主体,终以肉身为中介联系在一起。肉身意味着日常,意味着具体而真实的人性。唯有回到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肉身,“你”与“他”才不再是历史的符号,而是真实的存在,历时性的荒诞书写和共时性的延伸也才能进行充分的有质感的对话。“你”对“他”的追忆,不是一种政治书写,不是历时性的价值评价,而是个体生命感觉的挖掘。
三、“你”与“他”的对话
“你”与“他”通过肉身建立了联系,“你”审视“他”的存在,也被“他”审视,“你”还不断地与”他”进行沟通和对话。
“你”在玛格丽特肉身的诱惑下,不断地陷入对“他”的审视——“他”这个卑微的个体,而不是历史。“档案”、“历史”、“私”、“正义”这些词汇却使你暗自发笑,起鸡皮疙瘩。你从身体上理解“他”。“你”不充当裁判,也不为“他”控诉,“你”审视的只是一个具有肉身的生命个体。
他当时所以发疯,恐怕也是寄托的幻想既已破灭,书本中的那想象的世界都成了禁忌,又还年纪轻轻精力无处发泄,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身心投入的女人,性欲也不得满足!便索性在泥坑里搅水。[1]
因为“你”审视的是与“你”共享一具肉身的“他”,所以,“你”在审视“他”的时候,也是在审视“你”。 “你”是以此时此地的心态去审视彼时彼地的“他”,但“你”并不是隔岸观火,并不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审视者。
你得找寻一种冷静的语调,消除郁积在心底的愤懑,从容进来,好把这些杂乱的印象,纷至沓来的记忆,理不清的思绪,平平静静诉说出来,发现竟如此困难。[1]
“你”和“他”泾渭分明的章节分配总是被打破,难分彼此。例如第52章,当“他”后悔没有理睬孙恵荣时,“你”忍不住跳出来忏悔,“你”久久不能原谅这软弱,不理解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听从陆书记,会不由自主地躲避和伤害那个不幸地陷入泥沼中的女孩子。是的,“你”逃离了“他”所处的荒谬的历史环境,但“你”能逃离“他”脆弱的本性吗?
“你”做不到真正的冷眼旁观,“他”在“你”的审视下也可以与“你”对话。
他说他的问题就在于生得太早了,才给你惹来这许多烦恼。要是晚生一个世纪,比如这行将到来的新世纪,没准就没这些问题了。可下一个世纪的事谁也无法先知,那世纪果然新吗?又何从知道?[1]
“你”之所以与“他”相区别,是因为“他”处在历史中,但是,“他”就一定比“你”卑微吗?“你”和“他”在本性上是不同的吗?“你”在审视“他”如一条蚜虫一样微不足道的“文革”生涯时,“你”也不断地在寻找“你”现实欲望的满足。“你”游荡在女人之间,城市之间,却仍是一无所获,“你”只是在这自由的寻找姿态中感觉到美妙。对你来说,瞬间的美妙就是永恒。
如此,除去“你”和“他”这两双眼睛,还存在着既能审视“他”,又能审视“你”,还能审视“你”和“他”的对话的第三双眼睛,承担了叙述主体的叙述视角,“你”和“他”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状态下的存在,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生命个体的脆弱存在和困境中的挣扎。这部作品的复杂多层的自审结构为叙述主体提供了足够的审美距离,使之做到充分的冷静、客观。灾难与丑陋的历史的书写被艺术化和诗化,成为一曲由一个微弱的个人浅斟低唱的生命之歌。正如高行健在《文学的理由》中曾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关注中。而这关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双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间的垃圾便也禁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情与眷恋之情。 ”[2]
[1]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156,187,441.
[2]高行健.论创作[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7.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