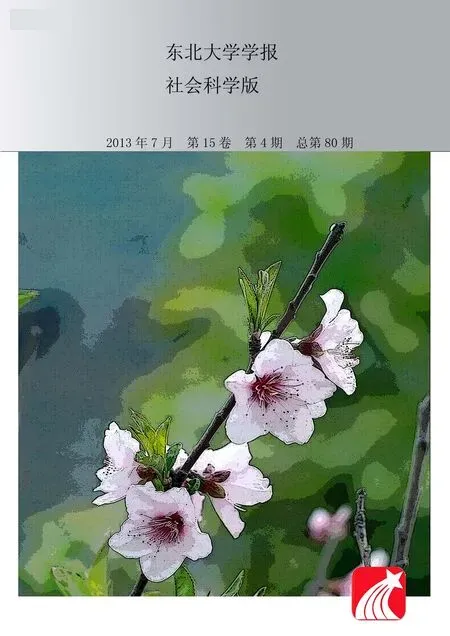抵达之谜的破解与历史性的诠释
——奈保尔的《抵达之谜》中的“空间”内涵研究
2013-03-22周桂君
周 桂 君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康德认为:“空间不是一个从外部经验抽象得来的经验性概念。因为要使某些感觉与我之外的某物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与在空间的不同于我所在的另一地点上的某物发生关系),此外要使我能够把它们表象为彼此外在的和彼此并列、从而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在不同的地点,这就必须有空间的表象作为基础。据此,空间的表象不能通过经验从外部显象的关系借来,相反,这种外部经验自身只有通过上述表象才是可能的。”[1]这就是说,空间不仅存在于外部,空间还存在于外部与我自身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同时,空间也意味着外部与自身的一种融合。奈保尔就是在他的空间转移中体会了焦虑、困惑、痛苦、无根感、漂泊感。这些在日后成了作家创作中的原色。
奈保尔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奈保尔是一位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常将自身的形象转化成艺术形象。《抵达之谜》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写的大约是奈保尔在197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中的经历和思考。这部小说并没有特定的故事情节。《抵达之谜》“针对的是风景、文学和历史以及它们对作家和写作过程的决定作用”[2]。这种独特的形式表明,它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虽然故事的主人公并不与奈保尔完全重合,但却也惊奇地相似。为了叙述方便,有些批评文章已经直接将小说中没有名字的主人公也称为奈保尔了,这也是本文将采取的策略,但应该明确指出,小说的叙述人并不等同于作家。
一、焦虑、困惑及身份的迷失
奈保尔的第一次旅行把他搞得忧心如焚,有整整一年时间,他担心人们可能根本不让他开始这次旅行了。此时,奈保尔获政府奖学金到英国读书,但对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讲,未来既充满诱惑又是一个未知数,他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这是比恐惧更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焦虑。“在恐惧的状态下,我们面前有我们可以‘见到’的对象,我们可以将其移开,或者逃开它。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和对象的存在,我们可以深思熟虑如何面对它。而我们也可以从空间的角度看一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另一方面,可以这么说,焦虑是从背后攻击我们。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从中逃开,却不知道去往何方。因为我们体验到的焦虑不来自任何特别的地方。有时这种逃开是成功的,这仅仅是巧合,而通常这种逃开是失败的,焦虑与我们如影随形。”[3]可见,焦虑远比恐惧更可怕,因为它是无形的、不可预知的。
飞机向高空攀升,这对于奈保尔来说寓义丰富,仿佛随着飞机的升高,他过去的生活被隔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在奈保尔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从天空中俯瞰大海,海是银色的。茫茫的大海在他的面前遮断了一切,遮断了童年的回忆,也遮断了他熟悉的那种生活,这如同一个人被隔在自家的门外,熟悉的那个空间中的故事被关进了一扇门里,那里曾储存过许多记忆,那些对于他人是个谜,而对奈保尔自己,是一个还没有来得及言说和认识的世界。这时,回忆占据了奈保尔的心。早晨的家族告别仪式,已渐行渐远。他感觉自己是在向他的过去告别:殖民地的过去、农民的过去、亚洲人的过去。之后,飞机上升,掠过田野和群山、布满涟漪的大海和天空的云彩。这时,奈保尔感到时间无始无终。这是一种强烈的体验,甚至是一种惊惶,他感到自我意识减弱了。这是一种被抑制的、半真实的感觉。飞机的飞行过程孕育着奈保尔的思想变化。
空间的变化为心理的变化提供了契机,山与云近在眼前,世界仿佛在缩小,而一个人的经历也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被缩小了。那种被抑制的、半真实的感觉源于奈保尔对以往生活的感受。之所以是被抑制的,是因为奈保尔将要前往英国,要在那里成就自己的事业,那意味着故国的一切已经失去了言说的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没有人会与他分享特立尼达的往事,在一个西方文化的氛围中,一个有色人种的青年又怎么能不彷徨。这种抑制意味着痛苦的积累和叠加。所以,他感到,从自己的家乡出来不到二十四小时,屈辱感已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空间的转移也带来了奈保尔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当他身处英国,他抛在后面的是自己的家园,那个家园离他远了;而当他身处伦敦时,这个国家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在特立尼达岛,童年时他曾想象过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很完美,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也许就是在伦敦。现在,当他来到了伦敦,却发现这个完美的世界其实是存在于另一个时段,一个更早的年代。对奈保尔来说,英国和家乡变得一样不真实了。他童年时从文学书中了解的英国与现实中的英国相距是那么遥远,以至于他在这个令其无比向往的国度里再次迷失了自已。后来奈保尔从英国去印度旅行。他感到自己对真正的印度一无所知。这样奈保尔在三种文化中都不能够找到认同。这三种文化就像是三种不同的液体,相互融在了一起。奈保尔是浸在其中的一粒种子,它发芽了,成长了,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棵树吸收了所有的液体,这样我们就无法看出这棵树的根在哪里,而奈保尔自己又何尝知道呢?这就是无根感。奈保尔的心情变得更加酸楚了。作为一个作家,“他自己不断地追寻个人的自由,捕捉自己体会到的脆弱。他毕竟不是按照理论来写作的,他写的是在寻找原创意识时,发自内心深处的挣扎”[4]。奈保尔感到的原创性写作的困境是他身份困惑的结果。由于无根感,他无法选择一个立足点,感到脆弱,不知道如何战胜自己的脆弱,从而陷入了拯救自我的挣扎中。有批评家说奈保尔的“小说、短篇故事、旅游书及论说文都带有这种不可否认的黑暗和损失的重负”[5],正是奈保尔的自我挣扎构成了他小说中的黑暗色调。
奈保尔曾说:“伦敦是我的大都市中心;它是我的商业中心;然而我知道它是地狱的边缘(limbo),而我是其中的难民,因为我一直都是位于边缘的。”[6]这里奈保尔用了“limbo”一词,富有意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limbo指的是在基督降生前死去的未受洗礼的婴儿和善良人的灵魂居所。奈保尔用这个词来形容伦敦,说明对他来说,伦敦一方面为他提供了实现理想的可能;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让他无法满足自己期许的地方,他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
空间的不断改变是流亡的特征,这是一种永恒的旅行。旅行中那些不便携带的东西最终是要舍弃的,而流亡中也一样,也有不需要的东西必须丢掉,只不过这时候扔下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以前的那部分生活,自身国家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旧有的东西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甚至碍手碍脚,于是这部分东西只能被放在一边,放在记忆的仓库里,那是一个落满灰尘的角落,是一个没有人光顾的角落。这个与自己的本土文化隔离的人,实际上等于被放逐,他的身份也由于空间的转换而变得迷离不清。
二、空间转移中的寻根意识
空间转移的经历反过来让奈保尔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审视他所涉足的世界,使他能够重构西方与东方的形象,在这种重构中,两者都转化成了奈保尔反思的对象。在反思中,奈保尔那颗受抑制的心灵得以释放。有批评家说,奈保尔“如同是一个极其敏感和自我意识极强的人,他在混乱、残酷而又难以琢磨的黑暗领域穿行,怀着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战胜它”[5]。
在《抵达之谜》中,奈保尔通过探索生与死的问题,达到对人生的彻悟,此时,他的心结,那种关于自己身份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在《抵达之谜》的结尾处,因为要去参加葬礼而回到家乡的奈保尔,面对死亡,突然醒悟了。他感到生命是神秘的,伴着悲伤与荣耀。这时,他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会选择死亡作为他的《抵达之谜》的主题。奈保尔意识到,童年时代原以为神圣的地方,后来才知道那片土地其实充满了血腥,那里的土著居民惨遭杀戮,神圣世界已不复存在。奈保尔将死亡与神圣联系在一起,这神圣的世界是人创造的,它即使是在原初的意义上也带有幻想的成分,而当奈保尔远离家乡,在遥远的英格兰创作的时候,他将家乡想象成一个更加神圣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奈保尔的内心中,他一直在寻找根和归宿。那归宿总是被他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构建起来,那里渐渐地离现实越来越远,也变得更具有唯美的色彩。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人的新的神奇,也领悟到如果不把历史当做时间叙事,那么历史也是可以重复的,神圣的东西可以找回,作家自己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根也终会得到。这时,奈保尔将草稿扔到一边,抛弃了犹豫,写下了杰克和他的花园的故事。奈保尔已经认识到现实生活与神圣精神之间的关系,承认生命与人的神秘性就是承认神圣蕴涵在人的生命中。人的归宿在何方,这对奈保尔来说不是地理性的概念,而是精神性的概念。当奈保尔参透了生命的真谛,他才真正找到了其苦苦探寻的生命之根。
然而,奈保尔并不是为寻找死亡而寻找死亡,他寻找死亡的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想要参透生命的意义,可以说,奈保尔对死亡的寻求是对生命的寻求,理解死亡,就是理解生命。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奈保尔的笔下,他写杰克的花园,写乌鸦,写废墟,也写那些常春藤之类的欣欣向荣的植物,在这个自然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中,奈保尔思索着生命及其归宿。
《抵达之谜》的题名就富有寓意色彩。《抵达之谜》是意大利画家基里科的一幅画,首先是这幅画的题名引起了奈保尔的兴趣,因为他觉得,这个题目以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方式,让人注意到其内心深处所体验到的某种东西。联系奈保尔在该书结尾处提到的神圣的世界和人的新的神奇,不难看出,奈保尔所体验到的是生命与死亡的神秘,正视死亡就是正视生命,《抵达之谜》这个题名触动的正是奈保尔对人生的思索。《抵达之谜》这幅画则用视觉语言描绘了抵达的神秘。这是一个经典的场面,中世纪的、古罗马的一个码头:在背景里,有几道围墙和门,还有一艘古代海船的桅杆的桅顶;在近处有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行人,裹得紧紧的,一个可能是那个抵达的人,另一个也许是本地的人。这个场面凄凉而又神秘;它也述说着抵达的神秘。这幅画究竟什么地方唤起了奈保尔的感慨呢?在这幅画中,中世纪的场面营造了一种历史感,古代的海船加重了历史的沉重感,同时,也表示有人刚刚抵达,而那两个人裹得很紧,是因为天气寒冷?还是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显然,两者都有。这些景物与人构成了一幅凄凉神秘的画面:凄凉,因为这两个裹得很紧的人都感到寒冷,但是他们又不能向外界索要一点温暖,而是加倍地把自己裹紧;神秘,因为没有人猜想得出这两个人内心的感受,他们的世界是通过一些景物的暗示得以展现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正如要读懂基里科的画,就要读懂画的背景一样,奈保尔将理解历史作为解开抵达之谜的金钥匙。对历史的重视是奈保尔的一贯思想,这源自小说家自身的漂泊经历。在小说第一卷即《杰克的花园》中,奈保尔将自己的处境与杰克的处境进行了对比。一种无所事事的念头,总是萦绕在脑际。作为一个来自另一种背景的人,来到这几乎被遗弃的庄园,这座充满了过去的那个时代的纪念物的庄园,与世隔绝。这个峡谷庄园有点古怪,而作家自己更是个古怪之物,一种漂泊感和陌生感油然而生。杰克在奈保尔的眼里则被看成是景物的一部分。因为他的生活是一种真正的、根基扎实的、完全适应了的生活,杰克是一个完全适应这里景物的男子汉。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如同是华兹华斯田园诗中的一道风景。杰克继承了他祖先的历史,他的根永恒地扎在那里,从来不曾动摇过。奈保尔自己却是与那个环境不和谐的,他是外来者。虽然通过接受西方的教育奈保尔已经熟悉了西方的文化,而且这种熟悉程度已然超过了他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然而,与杰克相比,奈保尔仍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因为不管他的学识有多么渊博,他的根不在英国。所以奈保尔意识到历史对一个人的归属感是重要的。“奈保尔坚持认为历史是重要的。他个人的无根感,来源于其在特立尼达的一个移民群体中长大的经历,而后他成为英国的一个不安的漂泊者,这让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奈保尔的所有作品中,他都直接或间接地述说:个人或整个社会有必要了解历史以便懂得现在。”[7]
在奈保尔的描写中,杰克的花园代表着一种历史,一种过去,一种活在现在的过去。杰克和他的花园、小屋以及他的岳父,似乎都是从文学、景物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杰克的存在,就像一部西方活的历史摆在奈保尔面前,让他感到相形见绌。在寂静的庄园里,似乎一切都停滞了,历史的根会一直深深地扎入地下;但是那种生活是不会停止的,变化是万古常新的。一些人去世了,一些人在变老,一些人搬去别处了。生活的变化也带走了杰克。杰克去世后,小屋和花园渐渐荒芜了。杰克的去世和他的葬礼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杰克的离去对奈保尔来说是一个思想的转折点。奈保尔一直在构思他的这部叫《抵达之谜》的小说,但是直到他接触了现实生活中的死亡之后,才突然明白了死亡的意义,奈保尔说自己书中的人物是多年来一直在他的心中酝酿着的,等待着表现自己,可是,直到有关死亡的新意识出现,他才动笔。死亡是主题,是杰克的故事的主题,也是《抵达之谜》整部小说的主题。杰克的故事是小说的第一卷。杰克死去了,在他的身上,奈保尔曾看到光辉灿烂的历史,而这个人物的消失让奈保尔突然觉得可以动笔写书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死亡让奈保尔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死亡的主题是因杰克而引发,并在小说第四卷《乌鸦》中全面登场。这一卷描写了一连串的死亡,而乌鸦也成了死亡的象征,加深了死亡的沉重感。死亡主题的出现不仅让奈保尔找到了根的感觉,也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根的感觉是相对于整体的西方文化而言,这个根是西方文化之根,而家的感觉,是针对奈保尔个人的人生观而言。在《毕斯瓦斯的房子》一书中,毕斯瓦斯先生一心想要建一所房子。“努力想要建立一所房子是想要有个抓手,好让自己不要滑向深渊,而房子却似乎加速了这一过程,因为理想的房子只能存在于心灵中,而现实中的房子却不然。”[8]在毕斯瓦斯的故事中,奈保尔已经认识到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一种归宿感,这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在《抵达之谜》中,奈保尔的这种思想得以进一步呈现。归宿感只能从精神世界中得来。有批评家说:“奈保尔越来越致力于写旅行,而似是而非的情形是,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便满怀热情地要努力结束他的旅行。”[9]“结束他的旅行”,这意味着奈保尔的寻根之旅已告结束,也意味着奈保尔已经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根,而这个根是精神上的。
三、心灵镜像中的历史诠释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真正的世界历史应当是对关于过去的事件、现象所作的有秩序的表述,是一种内在的陈述,它呈现出具体的形式感受能力。直到今天,我们尚未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形式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生命的镜像。”[10]在斯宾格勒的思想中,历史被当成是“内在的陈述”,而这种“内在的陈述”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在生命”。这样,斯宾格勒就把历史与人的精神,或者说与人的心灵联系了起来。
和斯宾格勒所说一致,奈保尔的历史叙事不再是一个由古至今的序列,而是将历史与人的心灵联系起来。从时间概念上讲,奈保尔的叙述是共时性的讲述。“时间给我的感觉也变了。最初,如童年时代,它被拉长了。第一个春天包含着那么多清晰鲜明的事物——苔藓玫瑰,孤单的蓝鸢尾,我窗下的牡丹。我期盼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后来记忆开始变得混杂起来,时光开始飞逝,岁月开始堆积,我开始很难分清事情的先后顺序。”[11]奈保尔再也无法利用头脑中遗留的印记来对照各种事件。在飞逝的时光中,时间的先后顺序混淆起来。当时间的先后顺序不复存在的时候,那么事件的排列就是一种空间并置。在以时间排列的历史中,奈保尔是无法找到自己的根的。因为那些过去的英国历史和西方文化无论他懂得多少,都不可能变成他自己的。他也不可能成为那大英帝国风景的一部分。然而在空间并置中,奈保尔对历史的认识起了质的变化。岁月不停堆积,那也是春夏秋冬的风景在不断地循环和更替中演变的情形。这样,自然界中和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不再是按时间排列的,而是按事件的相似性排列起来的。关键问题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排列的问题,因为这种不同的排列带来的是我们对历史的新的观照视角。在按时间顺序排列事件时所没有呈现出的本质,现在呈现出来了。
与此同时,当事件离开了限制它、规定它的时间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发生过的事实,而在多数的时候,都成为现在和将来必将发生的事件的镜像。因为,我们很容易找到事件之间的相似性。去年的苔藓、玫瑰和今年的苔藓、玫瑰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按时间顺序思维自然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空洞而没有意义。但是,从空间排列上讲,去年的苔藓、玫瑰和今年的苔藓、玫瑰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从人类心灵的感受去感受历史的存在时,我们发现历史并非只能描述过去,它还可以描述现在和将来。当我们用历史描述现在和将来的时候,我们在语言中当然不能再借用“历史”这个词,政治是现在的历史,预言是可能的未来的历史。历史再也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组合,其实,这种逻辑的组合通常都是后人对历史的诠释。而在这种诠释中,人为建立的体系看上去十分严密,但事实上那不过是在有限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人为的连接与组合,就像把不同色彩的毛线编织成毛衣一样。此外,这样的空间并置也可以延展我们的思路。既然没有时间的限制,所有空间发生的事件都可以统统拿来放到一起。文化的分界线消失了,文化的界碑倒塌了。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奈保尔才将自己的西方文化积淀而化成一种根的感觉。因为既然无法辨明时间,那么,记忆的沉积物就成了时间的见证,这种沉积物是知识,是文化,这形成的沉积岩层再造了历史,而这个历史是属于奈保尔的。正是这种时间的共时性让奈保尔抛弃了无根之感,化解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死亡让奈保尔在对生活的反思中认识了生活的真谛。“从英美人中有点权威性的观点看,奈保尔的作品是一个作家的反思,他的语言有力而清晰,让他理所当然地担当此任。”[12]在这种反思中,最重要的是奈保尔学会了与世界达成妥协。奈保尔在描写庄园的景色时说,尽管从窗外看上去眼前是一片完美的景色,但是,这景色也有瑕疵。人们可能很容易被它的完美吸引而忽视了它的不足之处:比如残留的常春藤和林中的残木、堵塞的河边草地等。面对自然景物的不完美,人由于自身的某些缺陷和遭遇,会使得他在精神上感到畏缩,没有什么事物能激发他去清除美景中的瑕疵。这景色却似乎在告诉人们,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何必要担心,要去干涉呢?这里奈保尔通过写自己对景物的感受,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审视。他已经发现生活是不完美的,正如再美丽的风景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而对此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让它保持原有的样子。接受世界的不足,也就是认可了世界的美丽。因为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人生中不可能将一切都设计得完美无瑕,为了使有限的生命幸福地度过,最明智的作法就是以博大的胸怀容忍世界之不完美。当奈保尔领会了这一道理之后,他多了一份宽容之心。当奈保尔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他所生存的世界时,他意外地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宁静与美丽,在这种发现中,奈保尔也安顿了自己的心灵。“在抛弃了他的第一种生活,即他在殖民地特立尼达的童年生活二十年后,成熟的作家发现了他的第二种生活,一个他平生从未抵达的安全之地。”[13]
奈保尔也在死亡中看到了生活的循环往复。在英国他看到这样的细节:“那就是,它内在的多样性,它的矛盾,它的开放,它那无数的悲剧,它那复杂的希望之网和幻想,它那无数大的和微小的变化,它那不断更新的令人难辨的一次次的衰落,它那不断衰落下去的难以察明的一次次的更新,那无数的不同又总是如此地相似,它那短暂的,不稳定的变化倾向和它无休止的运动。”[14]既然生活是循环往复的,那么,人世的变化也就不能算做一种悲伤。奈保尔此书的第二卷是《常春藤》。那常春藤攀在树上,树死去了。人和树一样。他们存在于你的周围,时间到了他们就离去,然后会有别的人出现。奈保尔此时已经通过理解死亡,理解了生命。他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困惑,因为生命的意义对于来自任何文化的人都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讲,每一个人的根都扎在自己的生命的深处。
奈保尔将死亡与历史意识相联,死亡让奈保尔重新审视并诠释历史。奈保尔打破时间的禁锢,将记忆与知识的沉淀演绎成新的历史叙事,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死亡主题又使奈保尔与世界和生命达成妥协,以宽容、平和的心态继续生活下去。这对于奈保尔来说就是一种“抵达”,对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彻悟。这种思考,建基于多元文化的土壤,又超越各种文化而直达人生的本质。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9.
[2] Naipaul V S.The Writer and The Enigma of Arrival[J].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2000,35(1):72.
[3] Harold K.A Unitary Theory of Anxiety[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57,17(2):129.
[4] Philip C.Naipaul’s World[J].Commentary,1994,98(2):27.
[5] Bibbu P.Naipaul on Naipaul and the Novel[J].Modern Fiction Studies,1984,30(3):454-455.
[6] Baidik B.Naipaul’s New World: Postcolonial Modernity and the Enigma of Belated Space[J].Novel: A Forum on Fiction,2006,39(2):245.
[7] Lynda P.Past and Present Darkness: Sources for V.S.Naipaul’s “A Bend in the River”[J].Modern Fiction Studies,1984,30(3):550.
[8] David O.Theme and Image in V.S.Naipaul’s A House for Mr.Biswas[J].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67,8(4):593.
[9] Rob N,Naipaul V S.Postcolonial Mandarin[J].Transition: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1,52:100.
[10]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韩炯,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11] 奈保尔 V S.抵达之谜[M].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304.
[12] Sara S.Naipaul’s Arrival[J].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1988,2(1):41.
[13] Robert H D.Review: V.S.Naipaul,The Enigma of Arrival[J].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1987,27(2):289.
[14] Ronnie L.Centre-periphery Dynamics,Global Transition and Criminological Transfers[J].Crime,Law & Social Change,2004,41(4):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