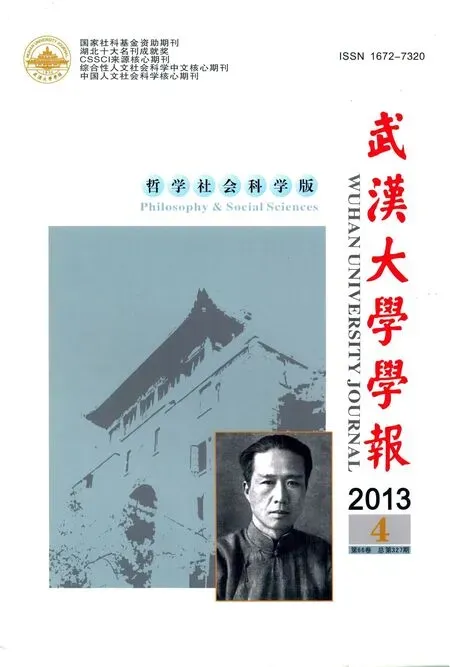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2013-03-18叶麒麟
叶麒麟
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影响冷战后世界秩序走向的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全球化和地区分裂是冷战后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而在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的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自二战伊始就一直是困扰着该地区许多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战后,该地区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而是表现为族群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这种民族主义分离运动和政治民主化运动相互交织,而且持续时间长,对战后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东欧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东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而作为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泰国南部马来族这一特殊族群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即南部动乱,则成为了该地区研究的焦点。因此,如何解析泰国南部动乱问题,不仅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解决泰国民族主义问题,维系泰国政治稳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泰国南部动乱成因:研究现状
泰国南部的北大年、陶公、沙敦、宋卡、也拉等五府为马来族群成员的聚居区。在这一地区,70%以上的居民具有马来血统,信奉伊斯兰教。近年来,泰国南部马来地区不断发生的暴力活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于是,泰国南部动乱问题便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而对于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研究,又集中在动乱成因的探究上。
一般认为,泰国南部动乱问题是指马来族这一特殊族群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形式的政治暴乱,其呈现的是一种“族群政治化”倾向。但是,纵观现有国内外研究,大多数学者主要采用的是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来解析泰国南部马来族的政治化倾向。例如,泰国学者悟泰·杜拉卡森(Uthai Dulyakasem)在《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政治抗争之原因分析》一文中揭示出泰国南部马来族的血缘、文化、语言和宗教与泰族的差异,导致了分离主义运动(Dulyakasem,1984:217-233)。他又在《种族民族主义的强化:暹罗南部马来穆斯林个案研究》一文指出,泰国南部马来族人根深蒂固的族群意识、族群认同感成为分离主义运动的诱因(Dulyakasem,1987:208-249)。又如,国内学者陆继鹏在《试析文化差异与泰南四府民族问题》一文中突出了文化是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重要因素(陆继鹏,2004)。总之,上述学者主要是从马来族与泰族在血缘、语言、文化和宗教等自然因素上的差异来解析马来族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应该说,由于自然界规律的作用,世界上出现了相当多元的族群。若依照上述学者的逻辑,那整个世界就应该一直处于族群厮杀的状态。显然,这不符合客观事实。另外,举一个典型例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族群国家,但其并未像泰国那样出现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此外,更能说明此意的是,泰国北部也存在着山地族群(常被简称为山民),可其并未出现分离主义运动。因此,马来族群的自然因素并非其分离主义运动的直接原因;换言之,族群并不必然主动进行“政治化”。
除了族群内部因素,一些学者还试图从族群外部因素来解析泰国南部马来族的“政治化”倾向。其中,一些学者从社会经济层面进行解析。例如,美国学者谢敏(W.K.Chen Man)在《穆斯林分离主义:菲律宾南部的摩洛人和泰国南部的马来人》一书中特别强调,经济落后和地区差距是培植族群分离主义的沃土(Chen,1990);又如,国内学者孟庆顺在《泰国南部问题的成因探析》一文中强调,现代化进程所引起的经济差距是泰国南部马来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重要原因所在(孟庆顺,2007:19-26)。另外,陈衍德等国内学者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一书中也同样指出,现代化所引起的经济落后,导致了泰国南部马来族的边缘化,从而成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因所在(陈衍德等,2008)。总之,上述学者主要认为泰国南部马来族的政治动乱在于与泰族之间的经济差异。但有意思的是,泰国北部的山地族群经济也同样落后,却未出现类似的政治动乱。就此意义而言,社会经济层面也并不是泰国南部动乱的直接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族群的自然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层面未能很好地解析泰国南部马来族的“政治化”倾向。而在现代国家整合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相对和谐的族群关系往往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泰国南部动乱很大程度上正是政府为了实现国家整合而施行的同化政策和军事打击手段所导致的。换言之,泰国南部马来族的“政治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整合的反效果。因此,国家整合成为了比较可取的解析视角。而从国家整合层面解析泰国南部马来族“政治化”倾向的现有研究,不管是从量还是质,都还不够。即使现有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政府的同化政策直接导致了泰国马来族的反弹,从而出现动乱现象,并且也试着站在现代国家整合的高度来解析其民族分离现象,但其对于现代国家整合的内在机理还未能深入探析。另外,“族群”与“民族”这两个基本概念被混淆使用。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现代民族国家整合视角,基于民族政治和族群政治两个基本维度,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整合的内在机理,对泰国南部动乱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解析。
二、族群政治与民族政治: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
自17世纪伊始,作为现代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逐渐建构起来,并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虽然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国家,但正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边界(borders)”(吉登斯,1998:4)。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主要是由家族、部族、种族等地方性族群共同体组成的,传统国家的权力并未深入底层社会。而在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才能与这种要求所需的领土边界直接对应起来”(吉登斯,1998:20)。就此意义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国内学术界往往对“民族”和“族群”不加区分,并且常用“民族”概念来替代“族群”概念。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原则的区别的。“民族”(nation)是指国族,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人为建构和想象的共同体,是在政治权力推动和保障下建构起来的,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而“族群”(ethnic)是指族裔,它是基于血缘、宗教和文化等自然、社会因素而形成的,如汉族、犹太民族等。
另外,正如吉登斯指出,民族国家是两个不同的共同体的融合:“一个是以行政和领土有序化为表征的‘行政统一体’,即国家(state);另一个则是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表现为民族(nation)。两个共同体之间既彼此依存,又常常抵牾,由此形成了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郭忠华,2006:63)其中,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共同体为认同基础的国家共同体。没有共同民族认同的国家,无法被称之为民族国家。而作为人为建构和想象的共同体,民族需要国家来建构和维系。国家和民族之间除了相互依存外,往往还会相互抵牾。它们之间的抵牾主要是由族群问题引起的。因为国家对民族的建构和维系,必然面临着如何看待和处理原有族群的问题,即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纵观全球,国家处理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二者关系的方式主要有族群政治和民族政治两种方式。族群政治,是指将自然形成的族群进行“政治化”,将其视为政治群体。在族群政治思维的指引下,国家往往首先通过血缘、宗教和文化等自然、社会因素对族群进行识别,然后要么强制将其进行同化,要么通过给予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特殊权利和待遇,使得地方性的族群成员去认同民族(国族)。而民族政治,是指将自然形成的族群“去政治化”,将其“文化化”。在民族政治思维的指引下,国家不会将族群视为政治群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自然、社会群体。对于族群成员,国家则将他们视为公民个体,给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从而使得他们去认同民族(国族)。
在单一族群国家中,原有的族群认同容易转化为民族的认同,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定的认同基础,因而族群政治和民族政治对于民族的建构并无差别。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大多数是多族群国家,单一族群国家的数量并不多。而在多族群国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族群认同。国家若将族群政治化,采取族群政治方式进行民族建构,则很有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因为各个地方性族群由于受到国家的同化或者特殊待遇,很可能会增强自己的族群认同感,增强自己的族群意识,从而呈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反而不利于民族认同,不利于国家整合。
由上可以看出,作为现代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族群政治和民族政治则是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泰国南部动乱,就是由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所引起的。
三、泰国南部动乱:马来族之“政治化”倾向
现代的泰国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全国有30多个族群,主要族群有泰族、老挝族、华族、马来族、高棉族。此外,还有瑶、桂、苗、汶、掸、克伦等山地族群(山民)。其中,泰族是泰国的主体族群,占泰国人口总数的40%,被统称为泰国的民族(国族)。马来族占泰国人口总数的3.5%,属于少数族群,在语言、生活方式以及宗教等方面,与泰国其他地区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泰族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讲马来语,有着深厚的马来文化根基。
泰国南部马来人聚居于靠近马来西亚边境的北大年、陶公、沙敦、宋卡、也拉等南部五府,约200万人。马来人占北大年、陶公、沙墩三府人口的75%以上,在也拉的比例为2/3,在宋卡则占20%(傅增有,2005:18)。1500年建立在这一地区的马来人统治的北大年苏丹国,在泰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多次被暹罗(泰国的旧称)征服,于1902年被划归为暹罗的版图。正是在此过程中,泰国南部开始出现了马来族反抗泰族统治的运动。而1909年的《暹英条约》又正式将这一地区的马来人割裂为分属两国的跨境族群,导致泰国南部马来族的国家认同出现了决裂,更是加剧了泰国南部马来族的分离主义运动倾向,南部政治动乱问题开始凸显。
1909年之后,泰国南部的一部分马来人因不服泰国政府的统治,不断为北大年解脱泰国的统治而斗争。恰逢二战期间,泰国披汶政府当局与日本结盟,沦为日本殖民侵略东南亚国家的工具。英国殖民者为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击日本侵略者,于是游说和协助前北大年王子哈吉·素隆(Haji Sulong)领导当地人民继续与泰国政府对抗,从而使得哈吉·素隆成为了泰国南部马来族反抗运动的一面旗帜。二战结束前披汶政府的倒台,使得泰国南部马来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泰国南部马来人的这一梦想并未实现。因为英国殖民者出于对这一地区局势的考虑,对泰国南部马来人关于准许北大年脱离泰国的要求未予回应。不过,战后初期的泰国政府颁布了《伊斯兰教保护法》,放松了对泰国南部的管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泰国南部的动乱局势。也正是在此情形下,哈吉·素隆在北大年成立了旨在鼓励各穆斯林宗教领导人团结合作以对抗政府同化政策的名为“北大年人民运动”(The Patani People’s Movement)的伊斯兰组织。此举让重新执政的披汶政府感到害怕。于是,1948年,披汶政府以“分裂国家罪”拘捕了向政府请愿要求“宗教信仰自由,马来语也为南部的官方语言”等的哈吉·素隆。此举引发了泰国南部马来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政府叛乱。在一些马来族政客的煽动下,政府军与马来人的暴力冲突迅速升级。在冲突中,数百人丧生,大量马来人移居英属马来西亚。哈吉·素隆于1952年刑满释放,却于1954年神秘失踪。由此,“北大年人民运动”组织也随之解散。虽然哈吉·素隆没有取得成功,但泰国南部马来人的分离主义运动从未停息过。
1957年,马来西亚的独立,更是极大鼓舞了泰国南部马来人为脱离泰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而斗争的士气。1959年,哈吉·素隆的追随者东古·阿卜杜勒·贾拉勒(Tengku Abdul Jalal)成立了为追求北大年独立、名为“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Barisan Nasional Pembeasan Patani)的第一个军事组织。该组织成员不断与政府军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也由此开启了泰国南部对中央政府的军事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泰国南部存在着60多个军事组织。主要的组织代表除了“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外,还包括“民族革命阵线”(Barisan Revolusi Nasional)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The Pa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sation)等。其中,“民族革命战线”是由一些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为了反对泰国政府将穆斯林宗教学校视为滋生分离主义的温床而成立的。其组织成员主要是宗教学校的师生,他们的目标在于建立北大年伊斯兰共和国。而“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通过伏击的方式打击泰国政府军警的组织。正是在这些军事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1975年的暴力抗争事件。该事件的导火索是1975年11月29日泰国的海军士兵在陶公府杀害了4名马来族青年。此案发生后的数月内,政府从未有过调查的意愿,这就导致了1万多名穆斯林在北大年举行抗议集会。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等分离主义组织逐步采取恐怖措施,袭击了汤孟机场,烧毁了泰国南部的铁路,在也拉地区袭击泰国国王。这些活动随后遭到泰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分离主义组织多位领袖相继落网。在此情形下,加上经济状况的好转,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伊始,泰国南部马来族分离主义组织的影响力日渐消退,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趋于沉寂。
进入21世纪,随着泰国政府加强对南部分离主义组织的打击,泰国南部分离主义运动死灰复燃。2001年,泰国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炸弹爆炸事件。4月7日,泰国南部的一个火车站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导致1名儿童丧生,数名乘客受伤。12月,泰国南部发生了袭击警察哨所的系列活动,导致1名军人和5名警察身亡。2004年1月4日,泰国军队的军火库被袭击,20所学校被烧毁,4名泰国士兵身亡。3月19日,北大年、宋卡和也拉三府的36个设施被烧毁。3月27日,陶公府酒吧爆炸案导致30人受伤。尤其是4月28日,泰国南部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112人身亡,数十人受伤,被称为“泰国近年来最血腥的一天”。据观察家估计,自2004年1月至2005年10月,死亡人数已超过1000人(朱振明,2006:128)。自“4·28”事件发生以来,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仍时有发生,南部动乱仍未完全停息。
四、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之因
在泰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前的一段时期内,马来人对马来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马来人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原本是同一的。因为1500年马来族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北大年苏丹国,那时,马来族既是马来人的族群共同体,又被视为马来人的民族共同体,从而实现了马来人对北大年苏丹王国的政治认同。但是,随着泰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北大年苏丹国这一马来族政权被摧毁,该王国也被划归为泰国的版图。在主导泰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精英看来,泰国的民族应是泰族,马来族仅仅是族群而已,不能再像在北大年苏丹王国时代里既是族群,又是民族。马来人对马来族的认同应该仅仅是一种文化认同,仅仅是一种族群认同,而不是一种政治认同,不是一种民族认同。马来人的政治认同应该是对泰国这一现代国家政权的认同,其民族认同应该是对泰族这一国族的认同。总之,认为马来人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应割裂开来。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泰国南部动乱是马来族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形式的政治暴乱,呈现的是马来族的“族群政治化”倾向。具体而言,马来人对马来族这一族群的文化认同变为政治认同,对马来族的族群认同变为民族认同。当然,马来人的这种认同转变,最初的直接原因在于泰国对北大年苏丹国的征服,激起了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分裂抗争运动。马来人的这种遭遇与举动,在许多多族群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都存在。但是,他们大多往往会对所征服的少数族群进行有效的整合,以缓和、平息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分裂抗争运动。显然,自北大年苏丹国被征服至今频频发生的泰国南部动乱,表征了泰国的国家整合出了问题,致使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分裂抗争运动未被缓和、平息。泰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对马来族这一地方性族群的整合主要采取族群政治方式,而正是族群政治的国家整合方式,才导致马来人对马来族的认同时常由文化认同变为政治认同,由族群认同变为民族认同。
不可否认,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泰国南部动乱与马来族的强烈族群意识、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有关。但是,它们并不是泰国南部动乱的主要原因。泰国南部动乱的主要原因在于前文所述的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在于泰国政府的同化政策和军事打击。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泰国南部发生动乱的程度与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和军事打击的力度之间的关联性可以看出。1939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披汶·颂堪一上台执政,就改国名,将“暹罗”改为“泰国”。同时,极力推行对马来族的同化政策,颁布《泰人习俗条例》,禁止马来人讲马来语、穿马来装、采用马来族习俗,强制他们讲泰语、穿泰装、采用泰族习俗。此外,强制马来人信奉佛教。披汶政府带有“泛泰主义”色彩的强制同化政策,使得泰国南部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在披汶下台之后,泰国政府颁布了《伊斯兰教保护法》,放松了对泰国南部的管制,泰国南部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然而,随着1948年披汶再次上台,再次推行严厉的同化政策,泰国南部的局势再次紧张。正是泰国政府的同化思想,使得海军士兵杀死马来族青年的行为得到默许和纵容,也才导致1975年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2000年2月,泰国政府再次加强对南部分离主义组织的军事打击,引起了泰国南部分离主义者的反弹,才发生了后来包括2004年“4·28”事件在内的一系列动乱。因此,纵观历史,泰国南部动乱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为了实现国家整合,而对马来族施行的同化政策和军事打击手段所导致的。
五、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解决之道
正如前文所述,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泰国对地方性族群的整合主要是采取族群政治方式。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政府对马来族这一地方性族群实行同化政策和军事打击手段,激起了泰国南部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分离主义运动,致使泰国南部频频发生动乱。这也就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即为了阻止国家分裂,政府施行国家整合,结果反而助长了国家分裂。正如前文所述,较之于族群政治方式,民族政治方式更有助于国家的整合。因此,泰国欲破除上述“国家整合”的悖论,解决南部动乱问题,就需要改变国家整合的方式,即采取民族政治方式。
首先,对马来族“去政治化”,对其进行“文化化”。泰国政府不应将马来族视为一种政治群体,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然、社会群体,淡化马来族这一族群的政治色彩。对于马来族特有的服装、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以及宗教,泰国政府应该秉持“文化多元主义”理念,将其视为文化、社会现象,并且尊重它们。泰国政府不能强制推行带有浓厚同化色彩的国家统一的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而应允许和保留马来族自己特殊的教育。当然,泰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对马来族进行族群识别,没有必要刻意去实施特殊教育以保护马来族的文化与宗教,而应该让马来族自然存续。
其次,泰国政府应将包括马来族在内的所有族群成员视为平等的国家公民,平等享受各种应有的权利,包括政治参与权利。泰国政府应该允许马来人参与到国家的政权生活中去。对于马来人作为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泰国政府应该从公民的角度给予保障,针对每个马来人的具体情况以个案形式予以处理,尽量不将他们视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政治群体。
最后,积极推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充分提供公共服务,切实保障和维护泰国南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与马来族群相关的各种问题不是以马来族群为单位的政治问题的形式,而主要是以马来人个体的社会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政府再通过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行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积极将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向南部等一些落后地区倾斜,同时动员和提倡发达地区对南部等落后地区的对口支援。当然,泰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应不是针对马来族这一族群的,而应是针对全国范围内所有贫困者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
总之,泰国政府不应再采取族群政治方式,而应采取民族政治方式进行国家整合。通过马来族的“去政治化”、“文化化”,将族群身份归于非政治领域,按照公民身份角色来保障马来人的各项权利,给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淡化他们对马来族群的政治认同,以便塑造起马来人对泰国民族(泰族)乃至国家共同体(泰国)的认同,从而形成可持续性的国家整合态势。
[1]陈衍德等(2008).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傅增有(2005).泰国南部“4·28”事件的成因及其影响.东南亚研究,1.
[3]郭忠华(2006).民族国家的三大矛盾——来自吉登斯的启示.现代哲学,4.
[4][英]安东尼·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陆继鹏(2004).试析文化差异与泰南四府民族问题.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孟庆顺(2007).泰国南部问题的成因探析.当代亚太,6.
[7]朱振明(2006).泰国:独特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8]Chen,W.K.Man(1990).Muslim Separatism:The Moros of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of Southern Thai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Dulyakasem,Uthai(1984).Muslim-Malay Separatism in Southern Thailand:Factors Underlying the Political Revolt.in Joo-Jock Lim & S.Vani(eds.).Armed Separatism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0]Dulyakasem,Uthai(1987).The Emergence and Escalation of Ethnic Nationalism:The Case of the Muslim Malays in Southern Siam.in Taufik Abdullah &Sharon Siddique(eds.).Islam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