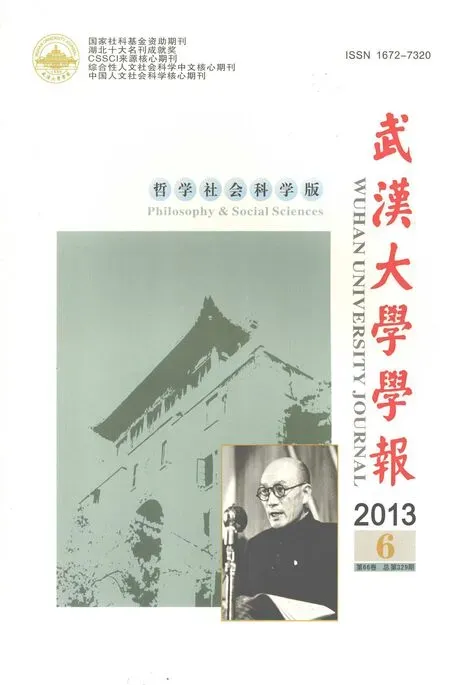第三人致害侵权责任的合理认定
2013-03-18邢宏
邢 宏
一、问题的提出:经营者在第三人侵害行为介入时承担侵权责任的特殊性
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确立,是有着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的。侵权法学者对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分析①如周永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刘文杰:《德国侵权法上的一般注意义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李昊:《交易安全义务理论研究——德国侵权行为法结构变迁的一种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借鉴了普通法中的“注意义务”②如廖焕国:《侵权法上注意义务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熊进光:《侵权行为法上的安全注意义务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并总结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③如张谷:《不作为侵权:消法18条的义务还是交往安全义务——评肖某诉石广饭店及其休闲中心人身损害赔偿案》;载张民安主编:《民商法学家》第2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刘言浩:《宾馆对住客的保护义务——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损害赔偿上诉案评析》,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安全保障义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首先得以确立,此后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时最终由立法机关采纳。
任何一种法律规范都必须在实践中得以正确的执行,方可实现立法之初的良好愿景,真正体现其法律控制功能。更重要的是,源自于德国交往安全义务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由法院在审理具体司法案件中创设并不断发展的一种特殊义务。正因为如此,安全保障义务的生命源于司法判例,也必然需要在具体的案件中得以检验和丰富。
特别是在第三人侵害“介入”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法》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只是责任认定的前提,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经营者在第三人侵害介入时的全部问题。美国的一些法院认为,经营者所承担的保护顾客免受第三人侵害的“注意义务”是一种“模糊”(vague)的义务。在具体案件中,经营者是否负有预防和制止第三人犯罪的义务,或者预防和制止犯罪的限度如何,均需要结合案件发生之时的各种特殊情况,综合评判、个案解决。这需要结合一系列因素,诸如风险、可预见性、损害的可能性以及被告承担责任的后果等等,经过一定的法律分析后才能确定①Gen.Electric Co.v.Moritz,257S.W.3d211,pp.216~18(Tex.2008)(指出在某种情形下,行为人行为的合理性应当在具体的过失规则认定下确定,而不是由保护义务的存在而确定).。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实质上规定的是经营者在特定情形下的作为义务,否则即构成不作为侵权。而第二款规定与第一款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在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情况下,经营者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顾客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否则,即使经营者并非直接侵害人,受害人的损害并非直接由经营者造成,也需要承担补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在第三人侵害的特殊情形中,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后果不仅是一种不作为侵权,同时也构成一种间接侵权。
不作为侵权构成的重要前提是行为人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在先行为具有作为义务。因此,作为义务的存在与否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特别是在经营者与受害人之间并无合同约定的情形下,经营者是否负有为一定行为而保护受害人免受损害的法定义务,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理论与司法的难题。随着安全保障义务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中的最终确立,这个难题已经迎刃而解。但是,在第三人侵害行为介入因素存在的情况下,除了要求侵权人履行作为义务,还需考察作为义务的不履行或者履行不当,是否间接导致损害的发生。
当然,在不存在第三人介入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并非不重要。只是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了不作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顾客因为商场地面湿滑而滑到摔伤,那么商场未能排除商场地面的安全隐患是导致顾客受伤的最主要原因。无论是从一般常理,还是从法律规则角度出发,这种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则上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当第三人侵害行为,特别是犯罪行为介入后,经营者未能预防或是制止犯罪行为对顾客造成的损害,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如何,经营者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显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间接侵权案件中,作为义务的合理界限以及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司法审判中的关键与难点。事实上,相对清晰和务实的责任认定规则,对于避免经营者陷于模糊的保护义务而面临不确定的风险,是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的。在这一点上,美国侵权法通过可预见性规则认定注意义务和因果关系的做法,值得我们分析与借鉴。
二、美国侵权法上对第三人侵害行为介入时经营者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
在美国侵权法中,经营者是否应当或者在何种范围内承担第三人侵害直接致害的侵权责任,同样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经营者从无责到有责、从有责到适度有责的过程,反映了判例法应对社会难题的务实与灵活。
(一)无义务规则(no-duty rule)的弱化与变革
传统上,普通法并不倾向于要求商场对于因第三人的犯罪而导致商场的顾客人身损害承担责任。美国法院的一个不成文规则就是,“个人对于他人遭受的第三人刑事犯罪侵害没有法定的保护义务”②See Walker v.Harris,924S.W.2d375,377(Tex.1996);Centeq Realty,Inc.v.Siegler,899S.W.2d195,197 (Tex.1995);另见Lefmark Management Co.v.Old,946S.W.2d52,53(Tex.1997).。这通常被称为无义务规则(no-duty rule)。这种规则可以追溯至美国侵权法上不法行为与不作为的本质区分(Michael,1979:735)。普通法非常重视个人权利与行为自由,并不主张将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
然而在近30年来,法院对于经营者或者房东保护其顾客、租客免受第三人刑事犯罪侵犯义务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Glesner,1992:684)。在1970年的 Kline v.1500Massachusetts Avenue A-partment Corp.③Kline v.1500Mass.Ave.Apartment Corp.,439F.2d477,482(D.C.Cir.1970).一案中,上诉法院一改传统普通法中的豁免原则,认为房主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房客处于犯罪危险之中,而且意识到房客有可能遭受进一步的犯罪侵犯时,房主对于房客存在一定的安全保护义务。这个案件几乎完全颠覆了普通法中房东对于房客被第三人犯罪行为侵犯后的损害可以完全豁免的原则(Olin,1982:102)。自Kline案之后,美国许多州都极大扩展了房主保护房客免受可预见性犯罪侵害的法律义务。同时,也将这种作为义务扩展到了经营场所领域内。
这种变化和修正直接反映在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344部分以及评论F(Comment F)的规定中。根据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第344部分的规定:“为经营目的而占有土地并向公众开放的土地占有人应当承担公众在其占有土地之上因事故、过失以及第三人或者动物的故意导致的损害,而且占有人未能充分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去发现这些行为的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或者向顾客给予足够的警示以避免损害或者是保护他们免受损害。”评论F补充道:“虽然经营者并不是访客安全的保险人,但当他知道或者有理由知道第三人行为发生或即将发生,那么经营者一般性地负有保护义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判定,来源于过去的经验,例如第三人行为有可能危害顾客安全的可能性,即便他并不期盼这样的结果发生。如果该场所或者经营业务的特性以及过去的经验,都可以使得经营者能够合理判断第三人犯罪、过失行为的发生,那么他有义务提示这种风险,并且提供合理数量的人员给予合理保护。”①Restatement(Second)of Torts§344,Comment F(1965).一些法院也认为经营者,例如酒店、商场的经营者应当向他们的顾客提供合理的安全保护义务,以避免顾客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这种义务源于一个特定的事实,即顾客向经营者移转了部分的、合理的控制经营场所范围内保护自身安全的控制力。作为场所的实际控制者,经营者、房主有能力规范安全设备的使用,也有能力了解场所周边的犯罪状况。因此,他们是最能够预测和应对旨在伤害顾客、房客的犯罪风险的人。
(二)可预见性规则在经营者责任认定中的重要作用
即便如此,法院对于经营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问题仍心存疑虑,认为第三人犯罪行为的发生阻断了受害者损害的其他可能性原因,因此禁止原告的损害与房主、商场经营者不作为之间成立近因关系②参见Kline v.1500Mass.Ave.Apartment Corp.,439F.2d477,481(D.C.Cir.1970)(提到了之前的法院按照因果关系原理拒绝判定土地占有人对犯罪攻击致害承担赔偿责任).。其他法院也纷纷援引公共政策合理性以拒绝认定责任的存在,包括保护公共安全的义务是政府的职责;考虑到经济层面,扩大化的安全保护义务将会给经营者强加过重的经济负担③参见 Goldberg v.Housing Auth.of Newark,186A.2d291,pp.297~99(N.J.1962).。然而,最为常见的一种观点则是,通过扩展安全保护义务至对第三人犯罪行为的防范,实际上是将房主或者经营者置之于一种公共安全保险人的境地,这显然是不公平的④参见Scott v.Watson,359A.2d548,553(Md.1976)(讨论强加保护义务使得土地占有人“充满危险”地成为了访客安全的保险人);Feld v.Merriam,485A.2d742,746(Pa.1984)(提出要求土地占有人保证访客安全的不公平性问题).。为了合理地平衡经营者的行为自由与顾客安全保护这两种利益与价值,在第三人犯罪行为介入的情形下,犯罪能否作为一种可预见的不合理风险,成为了商场经营者等拥有或可以控制某个场地的主体应否承担保护他人免受风险的安全义务的重要条件。
1.通过可预见性规则来认定经营者是否应当负有注意义务
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通常会分析风险的可预见性,以认定经营者应否承当相应的注意义务。在Timberwalk Apartments,Partners v.Cain一案中,田纳西高等法院分析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后,认为产权人未能保护访客免受犯罪行为侵害应当承担责任。法院在判决意见中写道,“犯罪行为经常是随机而且暴力的,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并拒绝承认存在一般性的注意义务,以随时保护顾客或来访者,因为这样的一种义务“将会过于宽泛”⑤Timberwalk Apartments,Partners v.Cain,972S.W.2d749,751(Tex.1998).。如果要求经营者承担这种责任,通常都是建立在过失的基础之上的。过失的前提则是经营者是否能够预见到具体的犯罪风险的存在。在Staples v.CBL &Assocs.,Inc.一案中,田纳西州高等法院认为,“当经营者知道或者有理由知道在其经营场所内存在针对顾客的犯罪危险之时,而且这种而风险是能够被合理预见到的时候,那么经营者对顾客就负有安全保护义务”,且“可预见性与损害程度必须与加之于经营者提供保护的成本负担相平衡。”⑥Staples v.CBL & Assocs.,Inc.,15S.W.3d83(Tenn.2000).由此可见,可预见性是判断经营者注意义务的重要标准。
2.可预见性规则在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影响
在实践中,可预见性不仅决定了经营者注意义务的存在与否,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因果关系的认定。为了证明被告责任的成立,原告除了要证明犯罪行为是被告所能预见到的、被告有义务去保护原告、被告违反提供保护措施的义务,还必须证明这种违反义务的行为是原告损害的近因,即被告所提供的保护不足是损害发生的原因,或者说如果不是因为被告的过失,原告的损害就不会发生。在Baley v.W/W Interests一案中,受害者在夜总会发生的抢劫案中被杀,受害者的家属(原告)诉称夜总会未能提供充分的灯光照明和安保措施,存在过失。陪审团认定夜总会存在上述过失,但并不认为夜总会的过失与死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上诉法庭维持了原判决,也认为没有证据表面更亮的灯光或者更完善的安保可以有效防止侵害的发生①Baley v.W/W Interests Inc.,754S.W.2d313(Tex.App.-Houston[14th Dist]1988).。
一般而言,在第三人犯罪介入的情形下,因果关系的存在需要证明两个基本因素:事实因果关系以及可预见性。事实因果关系指的是,过失行为是导致损害发生的实质原因,如果没有经营者的过失,那么损害就不会发生。原告必须证明,“如果不是因为被告的行为,原告的损害不会发生。”原告无需排除损害发生的所有可能性,但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导致犯罪事件发生的更大可能性。而可预见性,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则意味着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预见到危险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第三人犯罪侵害是不可预见的原因,这减轻了过失行为人的责任。但是,当犯罪行为是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经营者的过失是不可排除的。
可以说,可预见性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营者间接侵权责任认定中义务前提与因果关系判定两大难点,不同法院在审理具体侵权案件中又不断修正和发展出了可预见性规则的具体判定标准,诸如有限义务、类似事件、总体环境、第一防线以及目标风险标准,使得可预见性规则更具有操作性。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三人侵害行为介入时经营者侵权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认定、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与原告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影响经营者侵权责任成立与损害赔偿比例确定的关键因素。然而,“义务限度”和“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却存在很大的缺陷与不足。
(一)对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分析与观察
以董德彬等诉启东市吕四聚鹤大酒店等旅店服务合同案②董德彬等诉启东市吕四聚鹤大酒店等旅店服务合同案,(2005)启吕民初字第0175号,载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6年商事审判案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176页。(下称“聚鹤酒店案”)为例,犯罪人绑架原告之女后,用虚假姓名登记并于凌晨入住被告酒店,原告之女于当日下午在被告酒店被犯罪人杀害死亡,犯罪分子被抓捕后依法判处死刑,因没有附带民事赔偿的能力而未能对原告进行赔偿。原告认为,被告未能按照《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依法审验、登记犯罪人的身份证件,致使公安机关未能及时通过查房而解救受害人原告之女,属疏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并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聚鹤酒店案,是法院依据最高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审理第三人犯罪介入之时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具体案件。法院判决中体现了此类案件的一般审判逻辑:法院在判决中首先认可聚鹤酒店的经营者的确未能按照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审验登记入住者的身份证件,属未能履行最高法人身损害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对经营者不履行义务与原告之女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法院肯定地认为:原告之女被犯罪人绑架进入酒店,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非属正常入住酒店的客人,这一特殊情况严重影响了被告能否防止和制止损害。而且,原告之女的被害结果属于犯罪人预谋之下的必然结果。即便被告按照规定登记犯罪人的真实身份,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原告之女死亡的发生。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法院认为酒店经营者未审验登记入住的行为与受害人死亡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在判决的最后,法院认定酒店经营者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构成过错,这种不作为与原告之女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彻底予以排除。考虑到原告的弱势地位以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存在替代性和平衡性的特点,判处被告聚鹤酒店经营者承担原告10%的损害。
本文无意深入探讨安全保障义务以及补充责任的立法追求和价值导向,因此对于聚合酒店案中审判法院的相关态度不作评价。但是,通过审判实践中的这一真实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三人犯罪行为介入的情形下,法院在适用安全保障义务、认定经营者间接侵权责任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判决的事实分析、法律适用与判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对因果关系认定这种“技术性”难题采取模糊处理和选择性回避,简单衡量原被告双方的地位并对所谓的“弱势”方做出有利判决,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判决结果不足以令人信服。
(二)相关理论探讨在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的有限作用
事实上,侵权法学者为了使得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更具有操作性,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有学者将安全保障义务细化为软件与硬件两大方面的具体标准,试图将义务具体并规范化,如果经营者不能达到这些具体标准,则可以认定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张新宝、唐青林,2003:84-85)。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有学者认为在营业时间和营业场所内,经营者应当保证进入场所主体的安全(汤啸天,2004:123-124)。至于经营者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当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判定,很多学者也承认了其中的困难①对此,冯珏在其《安全保障义务与不作为侵权》一文中,引用张民安教授的说法,认为法院基于因果关系的考虑,否定了原告要求经营者就第三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对自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请求。参见:冯珏:《安全保障义务与不作为侵权》,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张民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兼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6期。。考虑到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证明问题上的差异,以及第三人侵害有可能中断侵权责任认定链条的特殊因素,通常认为在防范和制止侵权行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中,责任构成的因果关系应当是间接因果关系(杨立新,2010:175),适用高度盖然性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即可。
但是,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法院的具体审判之时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安全保障义务起源于具体的审判案例,本身就缺乏抽象性和概括性,实难通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去判断与适用。在实际案件中,经营者未能防范第三人直接侵害的情况千差万别,也不宜简单地套用某个标准去判定经营者的责任。人为地设置各种具体的指标很有可能破坏经营者与顾客的动态利益平衡,也存在义务与归责的泛化之嫌。
就本质而言,法律并不要求经营者对所有发生在经营场所内的犯罪行为负有预防和制止的义务。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经营者不应以旁观者自居,但也并非要求经营者作为绝对安全的保险人。因此,经营者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法院应对具体案件时,也应当详细充分地解释说明经营者是否合理应对第三人犯罪以及在该案件中“合理”概念的界定。在第三人犯罪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况下,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基于公共安全政策予以特殊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在相对统一的原则之下充分考量个案的特殊性。
四、结 论
在第三人直接侵权介入的情形下,普通法将可预见性规则灵活运用于注意义务和因果关系的认定,为我们破解现有难题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尤其是法院将“模糊”的义务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得以具体化,在可预见性规则指引下的弹性审判推理分析,更多地体现了司法的能动性而非僵化呆板。
对于经营者是否履行了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是否适当、以及间接因果关系判断问题,法院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方法予以明确:首先应探讨的是第三人致人损害是否具备合理的可预见性,经营者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预见到这种特殊风险;其次,法院应当探究经营者是否有能力预防危险的发生或者控制事态的发展;再次,通过第三人侵害风险的可预见性判断经营者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与顾客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与否;最后,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公平、正义和合理,其主要的评判标准是衡量经营者义务负担与损害风险孰重孰轻,而不是比较原被告双方的经济实力大小。例如:在第三人犯罪导致损害发生后,通过比较经营者履行义务的成本与损害发生的程度大小,来判定经营者是否充分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如果经营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去避免危险的出现与发生却并未作为,那么经营者应当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反之,则不应过多地要求经营者超出其自身能力而过多地承担社会公共安全的职能。
[1]冯 钰(2009).安全保障义务与不作为侵权.法学研究,4.
[2]廖焕国(2008).侵权法上注意义务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3]刘言浩(2001).宾馆对住客的保护义务——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损害赔偿上诉案评析.法学研究,3.
[4]汤啸天(2004).经营场所安全义务的合理界限.法律科学,8.
[5]杨立新(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6]张民安(2006).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兼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中外法学,6.
[7]张新宝、唐青林(2003).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学研究,3.
[8]周永军(2008).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Glesner,B.A.(1992).Landlords as Cops:Tort,Nuisance & Forfeiture Standards Imposing Liability on Landlords for Crime on the Premises.Case 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42.
[10]Michael J.Bazyler(1979).The Duty to Provide Adequate Protection:Landowners’Liability for Failure to Protect Patrons from Criminal Attack.Arizonal Law Review,21.
[11]Olin L.Browder(1982).The Taming of a Duty:The Tort Liability of Landlords.Michigan Law Review,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