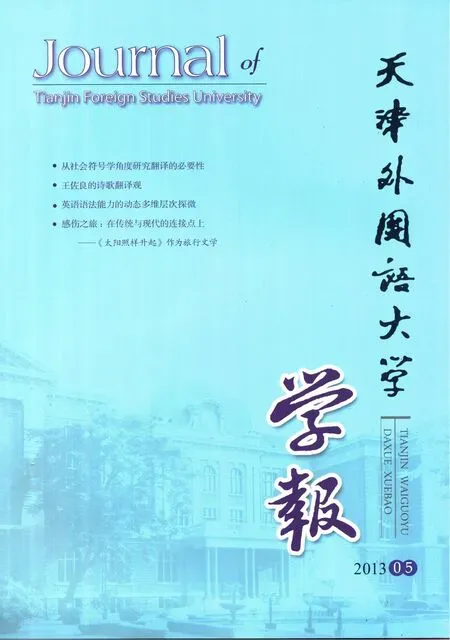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必要性
2013-02-14佟颖
佟 颖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4)
一、引言
从人类有语言开始翻译就存在,但翻译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时间并不久远,翻译家们仅仅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对翻译作简单的分析与论述。二战以来,翻译活动本身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也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向上快速向前发展(柯平,1997:49-55)。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翻译理论成型,翻译的多学科研究已蔚为大观,其中语言学方面的理论占主导地位。Kade(1968),Neubert(1968),Nida 和 Taber(1974),Reiss(1976),Newmark(1981),Hatim 和 Mason(1990),Nord(1991)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翻译。语言学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各种有效的指导原则。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翻译中存在大量的非语言因素,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传统翻译观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于是,翻译界开始对传统翻译观提出质疑、批评,甚至认为这种翻译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探索翻译研究新途径的过程中,符号学逐渐引起翻译界的关注。他们认为,符号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传统翻译观解决不了的问题。翻译作为人类最复杂的脑力劳动之一,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探索也是必然的。
二、翻译的符号学研究概述
现代符号学由索绪尔和皮尔斯分别从语言学和逻辑哲学角度提出,经由叶尔姆斯列夫、巴特、莫里斯等人的发展完善,并逐渐与各种现代学科结合后,逐渐发展成为跨学科性质的新学科。纵观符号学发展的历史与变迁,我们发现,符号学中出现了很多分支学科,而这些分支学科在不同的时期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翻译的语言符号学研究
受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影响,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这种翻译理论使翻译活动从神秘走向客观和科学(费国萍,2003:4)。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派对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划分为历来存在的直译与意译之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经过符号学家们的发展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可以相应地理解为形式与内容。直译与意译之争就是围绕文本的形式与内容展开的,前者较多关注形式,而后者认为内容更重要。在翻译实践中两种语言的接近程度、文本的体裁类型和译者的目的等都会影响译者对内容与形式的关注度,从而影响对直译与意译的选择。
索绪尔对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性的论述对翻译研究意义重大。符号的任意性指的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可用不同的能指来指称同一所指,这使翻译具有可行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虽然人类生存的世界共同性大于差异性,但异质性仍然存在。这种异质性使各民族语言的世界图景不同,不同的世界图景再加上符号的任意性,各民族语言中就会出现表达本民族特有事物的词汇以及表达特有思想的独特方式,这些都使翻译工作困难重重。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些困难,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孤立地看某个词,而应该把词放在其所在的词组、短语、句子或更大的段落、章节,甚至整个文本中来分析。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符号的意义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产生或决定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关注聚合关系,也要关注组合关系。
2 翻译的皮尔斯符号学研究
皮尔斯将符号界定为在某方面对某人来说代表某物的东西,他的符号包括三项: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翻译家戈雷和雅各布森等都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分别提出翻译的三种等值和翻译的三种分类方式。莫理斯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提出了符号学三分野说,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Bassnett(1980:27)受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的影响,认为翻译等值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句法等值、语义等值和语用等值,且语义等值优先于句法等值,语用等值影响并调节着前二者。什维策尔(ШBейцер,А. Д.)也具有类似的观点。皮尔斯认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有理据的,语言对现实世界具有模拟性,而人类生活的世界共同性大于异质性,因此,不同民族语言符号之间的翻译是可能的。
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来看,意义是一个符号对另外一个符号的解释,寻求意义的过程是一个生产出无穷多解释项的意指过程,每一个指号过程都会揭示出指称对象的部分相关信息,从而不断逼近事物的真相。Gorlee(1994:61)根据皮尔斯符号过程的观点,指出“翻译是一个符号过程,为了给符号常新的生命,符号过程是而且必须是永无止境的、目标确定的持续过程”。我们认为,把翻译过程完全等同于皮尔斯的符号过程是有问题的。皮尔斯的符号过程指的是一个符号的解释项还可以再作为符号加以解释,这一过程是线形的、永无止境的,有不同的解释对象,而翻译过程中的解释对象是固定的,就是原文,因此翻译过程是以原文为中心的,发散的符号过程,某一著作或文章被译介到别国,而后又由该国译介到另一国的情况则另当别论。虽不能将翻译过程简单地理解为符号过程,但戈雷的提法给我们重大启示:一个符号经解释后还可以再解释,即符号总是会有新的意义。一个符号在不同的指号过程中意义不同,不同时期的人会对同一符号做出不同的解释,这就是对文本不断重译的重要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无论是语内翻译、语际翻译,还是符际翻译,都不再是原文的复制品,而是突破了原文的束缚,产生了与时代、社会和文化相关的新意。皮尔斯符号学引入解释项概念,但解释项并非解释者,因为在他看来符号系统是自产的,符号互相解释从而产生意义。莫里斯引入了解释者概念,但由于其哲学基础是生物行为主义的,导致了他所谓的解释者只是普通生物或生物的人,而不是社会人(郭鸿,2008 :54)。
3 翻译的其他符号学研究
Lotman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对很多翻译理论家影响重大,如Bassnett,Toury和Even-Zohar等。从符号域思想出发,Lotman(1990:125)认为,文化文本在可译和不可译之间相互作用,而文化也由于受进入中心文化外来的、不对等的和附带文本的影响不断重组,其中翻译发挥重要作用。
解析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这个概念的提出与解构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文本的互文性是指原文和译文都像马赛克一样,由很多与其他文本相似的文本块粘合而成。从解析符号学来看,原作没有权威性,译者具有创造性,而译文具有创新性,译者和译文的地位明显高于作者和原文(郭建中,2000:178)。Lawrence 受解析符号学思想影响,反对通顺的翻译策略,提出异化的翻译。
文化符号学和解析符号学共同催生了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使翻译研究从语言的内部层面走向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层面,由此,翻译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Niranjana运用解构主义的理论,结合有关帝国主义和文化的研究,把翻译看作被用来维护各种民族、各种人种和各种语言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政治行为,颠倒了以往的西方翻译史(郭建中,2000:178-179)。
文学符号学指出文学语言符号的特性是自指性,即文学语言符号的意指过程是开放性的、永无止境的诠释活动,文学文本没有终极的、最准确的、绝对的意义,文本真正的意义在符号无限衍义的过程中。将文学符号学用于文学翻译,使研究者注意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文学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虽不能像巴特说的“作者死了”,但文学文本经过读者的阅读往往会获得新意。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应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使译文像原文一样,具有自指性。这样,读者才能通过积极的阅读发现和感知作品的意义(费国萍,2003:7)。如果译者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作者并通过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就限制了译文读者思考的权利,有时甚至堵塞了译文读者接近作者并理解其真正意图的通道。
三、翻译的符号学研究途径分析
从语言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解析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等角度对翻译加以研究,改变了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使翻译跨出了对纯语言的研究,进入了符号系统的对比关系和文化比较研究中。符号学将翻译真正纳入科学范畴,从科学和客观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理论加以论述。
由于符号学各分支学科所固有的特点和理论上的局限,翻译的各种符号学研究途径并不能客观、准确地描述所有翻译问题,也就不能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如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虽为翻译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为翻译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角度,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研究动机导致该符号学理论在真空状态下研究语言符号,将符号视为完全封闭的系统,摒弃了与符号相关的所有外部因素。皮尔斯符号学派克服了语言符号学派静止的、封闭的观点,指出符号过程的无限指称性,使翻译过程具有动态性,为原文的不断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皮尔斯符号学派提出的符号三位一体观、解释项和解释者等概念将人纳入整个翻译过程,打破了对语言符号(文本)的真空研究状态,使翻译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皮尔斯符号学中的解释者是生物的人,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得这种研究途径只能在较小范围内应用,不能解决翻译中与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社会以及文化有关的问题。文化符号学强调,翻译除考虑文本的语言符号外,还要考虑文化因素。以Lotman的文化符号学为指导的翻译研究者们都关注翻译文学对文化的影响,并指出对文本的功能方面的比较也应该作为翻译评判的一个标准。但文化符号学对译者的分析显得很不够,解析符号学弥补了文化符号学的这一缺陷,给译者足够甚至过剩的权利,完全否定了原作者的地位,似乎有点过犹不及。解构主义关于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译文与原文关系无相似性的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郭建中,2000:187)。文学符号学考虑到文学语言符号的特性,并从符号学角度来剖析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本质。可见,这种研究途径强调译者和读者的同时,并没有贬低原文和作者的地位。但由于其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只关注文学作品,因而其作用范围相对狭小。
现存的翻译的符号学研究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翻译观解决不了的问题,但目前的符号学翻译理论还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文本和两个主体(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对比关系上,不是以原文和作者为中心,就是以译文和译者为中心。但我们知道,翻译活动不仅涉及客观存在的文本,也不仅是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争权夺势,而是一种涉及众多社会人的社会符号活动。文化符号学和解析符号学虽涉及翻译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但并未对二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做详细的阐述。另外,现有的符号学翻译观也没有将翻译中各主体(作者、原文读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已有的符号学研究途径没有突出翻译活动是人类跨文化和跨社会的交往活动这一本质,也没有突出社会中主体之间的互动。实际上,翻译的产生和发挥作用都离不开人类社会,它应人类的交际需求而产生,同时也能成为人类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仍需从更全面、更贴切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社会符号学有可能是这样一门学科。
四、翻译的社会符号学研究途径
1 社会符号学的本质特征
社会性是符号的本质属性,确定符号的完整意义要借助于使用该符号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从符号的本质特征——社会性出发来研究符号正是社会符号学的主旨。从本体论来看,社会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社会意义的理论,从认识论来讲,主体间性是其主要特征。认识论指认识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发展等。我们认为,社会符号学的主体间性不仅仅局限在韩礼德所说的社会学范畴,还应进入认识论和本体论范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主体间性只涉及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但社会符号学关注主体与主体关系的同时,也关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主体作用于客体,反过来客体也作用于主体,二者之间是和谐共处的关系。从方法论来讲,社会符号学从生物体间的角度、功能进化的角度,并以本能论与环境论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语言符号。生物体之间的方式指的是社会符号学研究语言符号时除了将语言符号看作活生生的、主体间的社会符号之外,还关注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关系。功能进化的方式指的是语言符号的产生、作用、发展和保持都源于自身已经发挥或即将发挥的功能,且这些功能是在社会人相互作用中,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进化使然。本能论与环境论互补的方式指的是人类(特别是儿童)对语言的掌握受本能和环境两方面的影响,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2 社会符号学研究途径的优势
社会符号学融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于一身,它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结合的典范。通过对社会符号学本质的阐述分析,我们认为,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有如下优势:第一,从符号的本质属性出发,为翻译提供立体的研究维度,扩大了研究视野。无论是索绪尔、皮尔斯,还是韩礼德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符号具有社会性,符号的意义与社会关系密切。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语言符号系统,必须把符号放在一定的社会情景和具体语境中,将其作为主体间的、社会的符号加以考察,从而把握符号的真实含义,社会符号学恰恰是用这种方式研究符号意义的。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就会以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为背景来考察整个翻译过程,透过静止的语言系统对特定语境中的符号的意义进行动态的立体分析。第二,关注文本中不同层面的意义和功能,注重主体间的关系,为翻译研究提供全方位、动态的研究视角。翻译活动的主客体都具有复杂性,作者在创作原文时,会受到其所处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自身的心理和社会等因素也会在文本中有所体现。译文文本除了传递原作的信息、意义之外,译者和译文读者自身的很多因素,如性别、年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也会对所读信息有所影响。翻译过程是一个从对一种语言的透彻理解到用另一种语言比较完美表达的言语行为过程,也是社会人透过两种语言进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很多因素,因此,应该从符号、社会、文化、人类、语言等综合角度来考察。社会符号学,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以及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能考虑到所有有意义的符号活动、语言主体和外部世界,并从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过程的角度对信息和意义进行解释,对符号的意指过程进行分析,译文的最终意义是上述社会人共同认知的结果。第三,社会符号学研究途径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方式之一,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两个不同社会的文化系统。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影响信息的传递,完全的等值就不可能实现,有时还会出现不可译的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两种文化通过翻译行为相互作用,译文中往往体现出两种文化的杂合状态,这样,社会符号学为翻译研究做了客观的且具有未来性的描述与分析。
五、结语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20世纪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两大思潮的碰撞使得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学科都从单一强调客体走上主客体并重的道路(蓝峰,1988),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应该且必须沿着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这是文化发展的趋势,科学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翻译发展的趋势。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就要考虑到翻译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如文本内的语言符号、主体、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并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分析,全面地解释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使翻译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从理论上来说,社会符号学应该是研究翻译的有效途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他符号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为翻译研究提供多维动态的研究视角。
[1]Ba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M]. York : Methuen, 1980.
[2]Lotman, J. M.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3]Gorle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M].Atlanta: Amsterdam Atlanta, 1994.
[4]费国萍. 符号学在翻译领域的历史性扩展[D].南京师范大学,2003.
[5]郭鸿. 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6]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7]柯平. 论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A]. 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翻译教学研讨会演讲会议论文集, 1997.
[8]蓝峰. 科学与艺术之争——翻译研究方法论思考[J]. 贵州大学学报, 19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