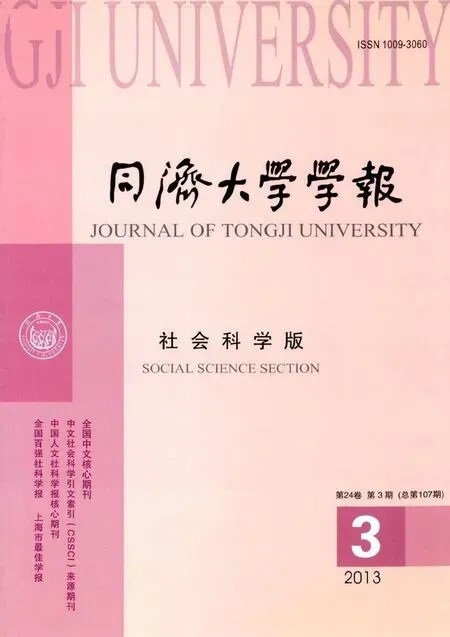香港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题材电影改编论
2013-02-14赵庆超刘晓鑫
赵庆超, 刘晓鑫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 吉安 343009)
作为承载先民恐惧情结和混沌意识的重要认知符码,飘忽不定而难觅踪迹的鬼怪群像曾一度放大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初想象,并以历时性的多样化形态延续着代际相传的文化记忆。千百年来,这些腾跃在文学世界中的生命个体以虚幻而鲜活的形象元素充当着创作主体的重要心灵镜像,传递出他们隐秘曲折的精神吁求和审美冲动。到了清初,《聊斋志异》则笼括进神鬼仙怪等多种超现实的艺术形象,凭借其灵动诡异的神奇世界成为中国鬼怪叙事的集大成者,隐现出作家个人借乌托邦化的文学想象弥补现实生存困境的精神脉动,复现了清朝初期遭受民族压迫和科举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寻求解脱与超越的想象之梦。
鲜活的形象个体和独特的叙事建构使得《聊斋志异》不断被后世者纳入改编学的再创造视野,表现在香港这一地缘文化相对驳杂而独特的区域,则早在1926年,黎民伟内地制作、香港上演的《胭脂》就获得轰动性影响,之后陶秦的《冷月香魂》(1954)和《丑生》(1964)、李翰祥的《倩女幽魂》(1960)和《辛十四娘》(1966)、李晨风的《湖北盟》(1962)、鲍方的《画皮》(1965)、严俊的《连琐》(1967)、周旭江的《鬼屋丽人》(1970)等作品则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把聊斋题材电影的改编引向深入,显示出香港影人虽遭受殖民语境的多重制约但仍深深眷恋着母语文化,对古典文化传统中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神鬼仙怪文学资源的倚重与借鉴。
更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和大众文化的成熟,另有一大批改编者继续撷取聊斋原著的思想审美元素,并填充进关于新时代的“现实”精神,建构起中原文化、岭南文化、西方文化互融共渗而更富香港地域特色的聊斋电影。程小东的3部《倩女幽魂》(1987、1990、1991)、午马的《画中仙》(1988)和《灵狐》(1991)、胡金铨的《画皮之阴阳法王》(1993)、吕小龙的《狐仙》(1993)、余立平的《阴阳判官》(2003)、徐小健的《鬼妹》(2005)、陈嘉上的《画皮》(2008)和《画壁》(2011)、叶伟信的《倩女幽魂》(2010)则代表了这方面的成就。目前学界针对这一阶段香港聊斋题材改编电影的整体研究的成果还非常缺乏,笔者试考察此类电影改编表现重心的迁移状况,揭示聊斋小说的审美元素和文化精神在香港特定历史时空的影像中的流动轨迹与嬗变特征。
一
虽然先秦典籍《山海经》曾牵引出中国神话传统的书写源头,但儒家文化泛道德教化和“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排挤阻隔这一文化传统的承袭与延展,“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生命信条使得神鬼仙怪等形象符号长期隐现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吮吸着中国传统神秘文化的精华元素,《聊斋志异》改变了《西游记》式的神话书写重心而转移到鬼怪狐妖等另类形象的书写层面上,以简约蕴藉的文言形式扩充和光大神话与鬼怪叙事的文学版图。
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故事和札记中,涉及神鬼仙怪的作品就有三百三十多篇,洒脱超逸的神仙、活泼开朗的狐女和凄迷哀婉的怨鬼游走在蒲松龄个人化的审美视野里,既掺杂着精雕细刻的人性真实,又笼罩上诗意朦胧的神秘之雾和梦幻之纱,构建出与现世界遥遥呼应的神仙之国与鬼狐之乡。在赋予这些异类形象以人性化的精神内涵的同时,作家还注重通过彰显故事的气韵和场景的氛围来凸显情节叙述的神秘性和奇观性,充满凶险的做恶与惩戒、缠绵悱恻的跨界情缘、来去无踪的通灵法术都与日常生活构成强烈的离间张力,日暮、傍晚、月夜、雨天等阴盛阳弱之时与旷野、荒宅、坟地、古寺等人迹罕至之地烘托出异类出没人间的阴森与诗意。欧洲文化中的鬼怪形象多为与现世之人对立存在的异物,众所周知的吸血鬼和古堡幽灵更多是与恐怖和怪诞相关联的象征符号,昭示着死亡的神秘力量,较少具有现实认知与道德评判的价值功能。而《聊斋志异》中的鬼怪形象则应传统思维阴阳两分又共通互转的文化观念氤氲而生,虽包裹在阴气浓郁的“他者”世界却具有多重的阳世人间的现实指涉和伦理寄寓功能,较好地做到了人性与鬼性或狐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在自己的研究专著中,张稔穰认为“《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构成的首要特点,就是从‘人’和‘物’(他们的本体是动物、花木、鬼、仙,本书将此统称为‘物’)的二元性达于‘鬼狐形象’的一元性”[注]张稔穰:《〈聊斋志异〉艺术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页。。蒲松龄没有专注于鬼怪造型的详细刻画,而是通过对他(她)们虚无缥缈、如影随形、夜出昼没、可隐形、通意念等功能特性的勾勒揭示其作为异类的来源出身,把更多的笔墨放到他(她)们幻化为人、与人共处的生命过程的描绘上,被赋予的复杂的人性内核改变了人们关于鬼怪的青面獠牙、吊舌凸眼或貌美如花、心似蛇蝎的符码化想象,聂小倩、婴宁、连琐、长亭、小谢、莲香、娇娜、宦娘等女性人物一起被赋予“聊斋奇女子”的称号,“奇”与“女子”的身份特征使得这些形象以光鲜照人、卓尔不群的个性化存在成为古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重要集合,她们改变了《西游记》神怪对立、女性之妖沦落为“他者”陪衬的性别言说形式,在与书生为主体的平凡世人的情感接触中点燃生命的烛火。幻化为美女的鬼怪异类与现世界的书生们之间的情感演绎成为《聊斋志异》的重要叙事生长点,她们与人类的生命共通性有效地消解了有关鬼怪形象的恐惧能指,以诗化或美化的精神情怀成为时代现实的审美镜像。
鬼女和狐女是《聊斋志异》异类书写的主体群落,蒲松龄剥离了传统观念赋予她们的狡猾、淫荡、阴险、媚惑、残酷等负面价值指向,使她们由男人们堕落丧命的生命克星变为报国无门、经济潦倒的书生们浪漫艳想的精神救星。鬼女、狐女在阴气上升的傍晚黑夜主动降临荒宅书房与书生互通款曲,帮助他们获取性爱、子嗣、功名、金钱等方面的满足,就带有男性文化中心主义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色彩。有人认为“蒲松龄反复讲述的总是一场男人的圆满美梦”[注]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5页。,处于现实受挫的人生困境之中,作家以文学虚构的想象来缓解被心灵挤压的紧张与不适,这些召之即来的异界女子就具有使作家生存现实得以改变和拯救的“神奇”功能,是作家“穷而后幻”的文学产物。于是,白日梦式的虚幻建构一方面揭示了作家身陷现实泥淖而不得挣脱的抑郁和无奈,另一方面又透露出蒲松龄寻求精神疗救和现实超越的人生愿望,虽然《聊斋志异》关于鬼狐女子的“翻案”式书写流露出男性本位的封建文化立场,使得她们在一定意义上充当着男性作家的精神缓冲剂和替代性的赏玩对象,而更多地处在功能论意义上的客体位置上,但鬼怪异类的群体出场以及与书生之间上演的真挚情感故事无疑助推了文学叙事的传奇性和超越性功能,开拓出神秘瑰丽而又诗意盎然的审美空间。
因此,传奇性与超越性成为《聊斋志异》形象塑造和叙事建构的重要艺术亮点,深植于文化传统又对传统模式进行改造创新的扬弃式书写使《聊斋志异》既达到陌生化的离间效果,又完成现实预设的隐喻功能,从而确立其“短篇巨制”的文学史地位。《聊斋志异》“豆腐块”式的文章格局和含蓄多义的文言“布白”方式为后人的填充改写提供了便利。如果说李翰祥的《倩女幽魂》和胡金铨的《侠女》等影片以彰显古典美学意蕴的影像风格,体现出老一代影人在与内地相对隔绝的社会背景下,来强化民族认同感并抒发精致典雅的文化乡愁的话,1980年代以来的香港聊斋题材电影在多元语境的合力作用下则表现出由鬼怪彰显向情感填充的重心游移。
二
自1979年始,香港影坛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新浪潮”运动,徐克、许鞍华、章国明、严浩、刘成汉等一大批青年影人携带着由新观念、新技法支撑的影片进入文化市场,使香港电影进入多元化创作新时期。虽然这场运动到1980年代中期即宣告结束,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其融入世界潮流的创新向度和初显身手的青年影人对之后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引领着1990年代的香港电影格局。其实鬼怪灵异片也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产物,构成了香港电影市场的重要一“元”,从1980年许鞍华的《撞到正》,到之后的洪金宝的《鬼吓鬼》、午马的《人吓人》、刘观伟的《僵尸先生》,再到1990年代林正英的“僵尸”系列,鬼怪形象在科学理性昌盛的香港一地大受欢迎,以奇观化的影像元素刺激着人们的观感神经,并深深影响到该阶段聊斋题材改编的电影作品。
同《鬼吓鬼》、《僵尸先生》等鬼怪灵异片一样,这时期的《倩女幽魂》系列、《画中仙》、《灵狐》、《狐仙》、《画皮之阴阳法王》等影片也通过造鬼捉妖的声像展现追求一种奇观效应,《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画皮》、《长亭》等小说仅仅是导演们抓取灵感素材的重要来源,他们往往看重的是原著小说中的一个或几个元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延展拉长,从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作品。《倩女幽魂》第一部《妖魔道》在人物和情节构成上还较为贴近原著,第二部《人间道》成了第一部的后传几乎和小说《聂小倩》没有关联,第三部《道道道》在情节模式上向原著回归但人物命名基本另起炉灶;《狐仙》除主要人物名字来自原作《长亭》外,情节、主题等其他文本元素已与原作相去甚远;作为胡金铨的最后一部作品,《画皮之阴阳法王》一改其《空山灵雨》、《侠女》时期的轻灵典雅的美学风格诉求,在武侠与魔幻之间往来奔突,追求商业片市场操作的“软着陆”,早已脱离蒲氏《画皮》的神韵。虽然把聊斋小说的文字语言形式转变为导演自己的声画影像形式,必然要加以多个向度的“改”与“编”,但这些电影作品在凸显正邪对立和鬼怪元素等情节和形象奇观的同时,更多地陷入一种轻视精神感悟的浅思维制作套路。
作为正派力量的对立面,邪派妖魔的形象和法力一再被影片大肆渲染。小说《聂小倩》主要突出老妖害人的神秘快速,对其形象仅仅以“欻有一物,如飞鸟堕”、“电目血舌”[注]蒲松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244、179页。等语句交待,《倩女幽魂》系列中的树妖姥姥、狰狞巨尸、蜈蚣精国师、魔幻鬼王和《画中仙》中的九尾狐狸不仅以怪异丑陋的画面造型引人注目,而且凭借法力无边的操纵能力把人界、仙界与鬼界搅得天翻地覆;《画皮之阴阳法王》则把小说《画皮》中显形之后“卧嗥如猪”②蒲松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244、179页。的厉鬼之恶转移到胁迫尤枫害人的阴阳法王身上,借王生尸体还魂的法王与道人之间的疯狂斗法而强化了鬼戏元素;《灵狐》、《鬼狐》所改编添加的怪兽天君和蛇精混云魔王以残酷的手段虐杀善良无辜的叛逆者,在与捉妖者的对立中掀起阵阵血雨腥风……影片中大量的邪派妖魔除《灵狐》中九尾琵琶精还闪现出些许复杂的人性内涵外,大部分流于扁平化和符码化,被单薄地钉在邪恶势力的耻辱柱上。而另外一些由鬼、狐或蛇幻化而来的美女叛逆者——小倩、小卓、莫愁、尤枫、雪姬、长亭们在与书生演绎现世情感时,浓墨重彩的身体影像在彰显其妖艳妩媚的异类出身时,更多地遮蔽了她们心灵世界的复杂性,除了《倩女幽魂》第一部较多地刻画了小倩欲爱采臣而不得的痛苦之情,其他影片中的女主人公都相对单薄,多沦为符号化的被看尤物。
因此,鬼怪形象的强势“在场”成为这些改编影片的重要艺术征候,它受到西方恐怖片注重细部雕琢的影像生成传统的影响,改写着之前的聊斋小说和电影通过彰显故事气韵和场景氛围揭示神秘的外在世界和微妙的内在心灵的表现定势。“中国的鬼戏,不同于西方影剧中的鬼怪场面,它不是以具体的恐怖取胜,而是以浓重的阴气包装。鬼戏在叙事与抒怀相交织的运作中,构成了一股股渗浸于一部部鬼戏叙事空间、时间内的深层情绪化的潜流。”[注]肖向明、杨林夕:《古代文学“鬼”文化之流变》,载《学术界》,2007年第2期,第254页。如果说李翰祥在其《倩女幽魂》中多运用色调变化、光影对比、声音元素来表现鬼怪场面而仅在故事高潮时正面显露姥姥的獠牙狰狞面目突出鬼戏格调的话,那么这种贴近原著小说的叙事维度几乎在程小东、午马、吕小龙等人的聊斋题材改编电影中消失殆尽,造型不一的鬼怪元素点缀在火爆绵延的正邪打斗场面中,有效地延宕着叙事时间流的自然流转,以影像空间化的展现优势推动着传统电影向奇观电影的叙事转换,有力地印证着电影改编者在汲取古典文化审美元素的同时靠“装神弄鬼”招徕受众眼球的商业美学策略,流露出鬼怪叙事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新气象”。
虽然鬼怪叙事也从属于神话讲述的题材范畴,但《聊斋志异》中书生与鬼狐女子的传奇故事更加注重生活的私人性和世俗性的一面,即使写到嫦娥也不像《山海经》中的女娲、夸父、后羿、刑天那样以英雄壮举和史诗行为气吞山河,而是在一个较小的叙事格局中写出了个人情感的曲折与温暖。这种“小叙事”形态被电影中降鬼捉妖的正邪二元对立的宏阔场面取代之后,其独特的故事韵味已在密集的戏剧化影像噱头中四散飘零,而让位于新时代香港镜像的话语包装和审美猎奇。“由于工具理性构成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流行的公共意识形态。所以,当代神话比较注重利益、感官、本能等因素的欲望叙事,古典神话的超越性原则和诗意精神一定程度上有所缺席”[注]颜翔林:《当代神话及其审美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74页。,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美女还更多地是作家生存困境中的个人诗化想象的产物的话,那么20世纪80、90年代香港聊斋改编电影中摇曳多姿的鬼怪形象主要是为大众造梦而设,更多满足的是受众潜在的猎奇心理和观淫欲望,甚至在《阴阳判官》、《鬼妹》等新世纪的香港聊斋电影中依然能够找到这种创作思维的余绪,从而印证着当代神话创编的消费主义特征和实用主义倾向。
三
伴随着1997年香港主权的顺利交接,香港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前途未卜的大限”,又越过了“患难意识的地平线”[注][美]丘静美:《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唐维敏译,见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终于在几度波折之后安全着陆,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出台为香港电影走出“非典”疫灾阴影的低迷状态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规定中港合拍片主要演员中只需三分之一的内地演员配额就可以国产片形式在内地发行。这种合拍片的生产力度在之后几年进一步加大,两地电影文化资源的互补性态势越来越明显,形成了所谓的“合拍片美学”,《赤壁》、《投名状》、《画皮》、《倩女幽魂》、《画壁》等影片既改变了香港电影偏重借鉴西方电影美学的追随主义道路,又有效地扭转了《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中国式大片”重影像奇观轻精神启悟的不对称倾向,在与传统美学的艺术接轨中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
大陆与香港之间合拍片风潮的蓬勃涌起带来的是中国传统价值和文化趣味得到进一步的充分彰显,为寻求内地接受市场的票房生长点,港人导演的合拍片特别是古装题材影片较多地呈现出回归民族国家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冲动。《画皮》、《倩女幽魂》、《画壁》等取材于聊斋小说的合拍大片不仅强调商业美学的趣味性,还更加注重精神传递的认知性,鲜活生猛的鬼怪形象依然在明暗相间的影像角落神秘出现,但大多逃离了单向度的符码化能指,成为情节因果链和人物形象谱系中的有机元素,而与含蓄蕴藉的影像画面自觉融为一体。比如《画壁》,为抓取受众的观影注意力,改编者塑造出性格各异的花仙群落和神奇精怪,并以高造价的实体建筑和一千多个特效镜头力图呈现根据《桃花源记》想象而出的神奇幻境,但整部影片的表现重心已不再是描魔与生幻,“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的说禅主题和救赎灵魂、寻求超越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亦成为影片的重要思想风骨。虽然伊芙特·皮洛曾一度认为:“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注][匈]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68页。但这些影片改变了上一阶段的聊斋影片中群魔乱舞的表现重心,而游移到传统文化怀旧和时代精神填充的内容层面上来。
《画壁》中的画面和场景设计主要受到的是东方传统美学的影响,在接受采访中,陈嘉上认为自己是从许多古籍和古画(特别是敦煌壁画)中找到灵感的,美术设计则参考了吴哥窟[注]罗雨田:《陈嘉上访谈:我曾想放弃〈画壁〉》,载《大众电影》,2011年第18期,第18页。,他的另一部影片《画皮》和叶伟信的《倩女幽魂》也试图把高科技合成的魔幻元素融入到古色古香的影像话语中,力图在扑朔迷离的人生幻境中捕捉和复现聊斋文化的神秘性。更重要的是在叙事密度的布局上,这些影片都注意强化的叙事的紧凑性,并适当拉长叙事的长度来防止奇观化、缀余性的影像场景对情节进程的空间阻隔,人物的性格与心理亦随着情节的自然推展而发生变化,呈现出个体世界的内倾性特征,凸显其心灵所指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而避免沦落为漫画式与妖魔化的异类符号。《画皮》中的小易(蜥蜴精)、《倩女幽魂》中的青蛇和白蛇、《画壁》中守卫画壁的武士(猫头鹰)等次要形象尚是如此,更不用说九霄美狐小唯(《画皮》)、乖灵狐精小倩(《倩女幽魂》)、芍药仙子(《画壁》)等主要形象了。改编者不管是把男主角书生换成武将(《画皮》),还是把“人鬼恋”改为“人狐恋”(《画皮》、《倩女幽魂》),甚或是强化异界类群的多元性(《画皮》、《画壁》)和展现捉妖团队的复杂性(《画皮》),都凸显或拉长聊斋原著小说穷困书生与异类女性之间的情感叙事图式,在多重形象之间的复杂纠结中完成对现实生存世界的镜像隐喻。
显然,这些大片的情感叙事模式及其彰显的主题意义带有鲜明的时代消费色彩。它们抛弃了聊斋小说中书生与一个或数个貌美女子书斋欢爱的个人浪漫艳想,而以更为复杂的多角爱情模式加以填充,所以“鬼片”和“魔幻大片”往往是制作者影像宣传的重要卖点,情感主题才是支撑其话语内容的主要材料,因此影片演绎的是披着古装外衣的现代戏,更多地揭示了现代人在爱情、婚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危机。《画皮》中小唯以第三者身份介入王生、佩蓉夫妇的情感生活,无疑映照着现代社会的婚外情问题;《倩女幽魂》中铺垫小倩与燕赤霞之间的爱情“前史”并与宁采臣形成的三角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冲出封建“铁闺阁”的新女性情感抉择的复杂与艰难;《画壁》中朱孝廉与芍药、翠竹之间的情感关系显示出当下人关于爱与被爱、情与理的悖论存在真相的深沉思索……总之,改编者在拉长、增删原著故事情节的同时,故意“搅浑”人物之间的多重关系,凭借所填充的夫妻之情、兄弟之义、人狐之恋或妖魔之道来暗示人性的复杂性,精微独到的细部刻画有力地透视出人物主体的情感世界,在看似虚假的故事框架里编织着饱含真诚热泪的情网去迎合与满足大众的情感消费需要,寻找思想与娱乐之间的平衡点来完成商业与艺术的联袂成功。
陈嘉上在揭示《画皮》的主题时说:“其实妖就是妖,人就是人,妖术肯定比人强大,所以真正能战胜妖魔的力量只有一种,那就是真爱的伟大力量。”[注]陈嘉上:《〈画皮〉是中国魔幻大片的新“起点”》,载《中国电影报》,2008年8月28日。其实靠爱欲、救赎、信仰等精神元素的输入来完成对现实的艺术转喻是这些大片的重要生成策略,这种创作倾向在《画中仙》、《灵狐》等上一时期的香港聊斋电影中已开始崭露苗头,但真正走向成熟还应是在中港合拍大片蔚为大观的新世纪。《画皮》、《倩女幽魂》、《画壁》纷纷抛弃了之前聊斋电影色彩纷乱、光影纵横、构图繁复、剪辑凌厉的过火癫狂的影像美学范式,采取放慢剪辑节奏以回归传统的持重端庄的中庸原则呈现银幕“怀古”的真实感,并因其情感反思的厚重与鲜活刷新了人们遭受内地大片奇观影像轰炸而审美疲劳的观影记忆。这种雅俗共赏的经验积累的对缝合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提高影片自身的审美品格、增加商业票房收入均可带来有益的启示。
通过对香港1980年代以来聊斋题材电影改编电影表现重心迁移状况的梳理,笔者认为可以引发以下几个向度的思考。首先是传统性的当代承袭与彰显问题。尽管古代文学经典会随着时代语境的迁移而可能产生接受上的偏差,但由于其富于自足性的思想艺术魅力而对改写行为具有强大的免疫性,因此改编者如果仅仅抓取经典原著的审美元素加以放大扩充而忽视其独特性的精神韵味,就会在“去传统性”的创编行为中造成文本之间对话的“短路”。严肃的经典改编不应该把“源文本”看做向传统“招魂”的符码,而应注重对传统文化底蕴的借鉴与彰显。其次是时代精神的补充与融注问题。传统文学资源在另外的时空段落中被“故事新编”,改编而成的文本无疑会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呈现出传统与时代多重对接的艺术印痕,“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被融注到改编文本中依然应该遵重古典原著的艺术生成逻辑,否则就会掉入“大话”式的舍本逐末的“二皮脸”生硬拼贴陷阱之中,那种过分迎合消费主义文化口味而追求武侠、言情、灵异、闹剧等元素相混搭的游戏历史主义改编,是一种投机性的文化误读与时代遮蔽。最后是文字与影像之间跨媒介转换的互文与通约问题。个人性色彩较强的文学作品改编为集体协作而成的电影文本,意味着可以反复咀嚼的、富有纵深感的线性阅读接受被光声影像转瞬即逝的复合感觉冲击所取代,可能造成文字的叙述灵韵和个人启悟难以顺利转换,但影像仍然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艺术生成技巧在对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适度把握中进行“尊古”与“戏古”的辩证转换,这种互文通约性在《画皮》、《倩女幽魂》、《画壁》等“港式大片”中表现得更为流转圆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