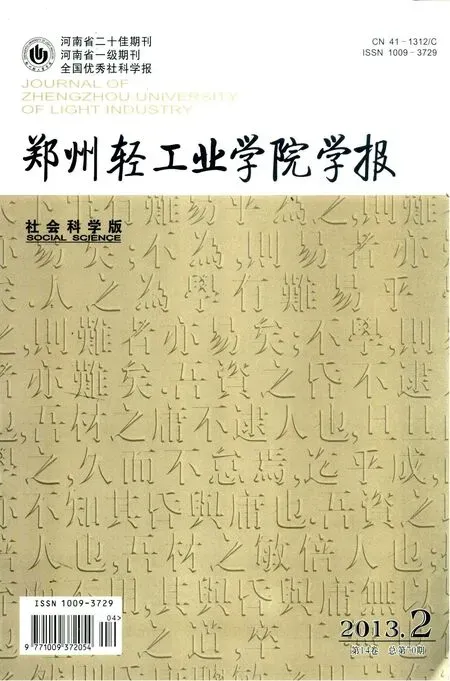明清中原理学家文学成就初探
2013-02-01赵秀红
赵秀红
(郑州轻工业学院 中韩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明清时期,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北移,中原地区失去其有史以来就确立的国家核心地位,中原文化也发生蜕变,使其在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审美取向等方面表现出地域文化特征。对这一文学现象及其深层文化成因的探讨,将有助于丰富中原文化与河南文学研究。目前,学界对中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多为哲学思想方面的探讨,很少涉及其文学成就。本文试图对河南理学家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等作一概略分析,探寻明清时期河南文学生成的原因,以期为中原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文学视角。
一、中原理学家的文学理论主张
明清时期,中原理学适应时代发展,形成了调和理学与心学兼容并包的特点。这种状况影响了明末清初中原文人的处世原则及思维方式,也对其文学主张及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文学理论体现出融合开放、经世致用的特点。
曹端(1376—1434),字正夫,号月川,今河南渑池人,是几乎与明王朝同时诞生的理学家兼文学家,为学重“躬行实践”,把人伦日用之间“可见之施行者”编订成书,名为《夜行烛》,把孔孟之学视为夜行路上指引人前进的火烛。他在提倡程朱理学的同时,也注重心性的涵养与实践,注重知行合一。曹端的著作多以阐释儒家经典为主,像《夜行烛》《语录》等文学类作品不多,其仅存的7篇序文、16篇诗歌,质朴平白,不假藻饰,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风格与独特的书写方式。
明朝前中期,台阁体文风充斥文坛。荡涤台阁体文风的是以中原作家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为首的“前七子”(其余4位是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永宽认为:“‘七子’的两位领袖人物(李梦阳、何景明)都不约而同地舍盛唐而青睐风雅之音、汉魏之诗,正说明他们复古的目的,不在于模拟盛唐之诗,而在于以先秦、汉魏诗歌的高古之格摧毁雍容而无生气的台阁之体,以真情勃发的风雅之调一扫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诗坛之音,以古人之精神接今人之心目。”[1]此论评价公允,很有见地。
“七子”之一的王廷相是一位知名的理学家,在文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初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兵科给事中,因不阿附宦官刘瑾、廖镗都等人,先后被贬,曾入狱,历任松江府同知、湖广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等职。王廷相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在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王氏心学刚刚兴起之际,他批判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倡导“有用之学”和“治己之学”。王廷相主张为学为文态度应该认真求实、注重实践。他在《与彭宪长论学书》中指出:“若曰出于先儒之言,皆可以笃信而守之,此又委琐浅陋,无以发挥圣人之蕴者尔,夫何足与议于道哉!齐客有善为鸡鸣者,函关之鸡闻之皆鸣,不知其非真也。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矣。”[2](P510)他认为,做学问、写文章都要有认真求实、独立思考的精神,否则只能如“函关之鸡”,人云亦云。
文学创作上,王廷相提出“文以阐道”与“文出自然”。王廷相要求首先把“道”即内容放在第一位,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所说的“道”是指孔子的“帝王仁义礼乐之道”。他认为道寓于六经,而魏晋以后的文章几乎全是“文”而没有“道”,只有大力提倡载道诗文,才能廓清文坛积弊。在重视文章内容的同时,王廷相也认识到作品之艺术形式的作用,主张“无意于为文”,文学创作要自然而然。
浚川游于蜀者三年,得所著诗文杂说几三百余首,萃为帙而橐之。门人问曰:“群品效材,万象呈美,何若是多?子将以言示于世耶?饬旨摛辞,归综于道,何若是严?子将以贤示于世耶?”浚川子不答。
门人退而思之,三日而再见,曰:“感于天机,万物皆入吾之会,虽言之而非溢言耶?存乎道符,言也举不畔其则,恐淆乱于外,而卓守其贞耶?夫子殆不得已而言,非乎?”浚川子不答。
门人退而思之,又三日而再见,曰:“得之矣。云之生于山,气机也;升于太空,其象为峰峦,为水波,为白衣,为彩锦,为人物,为花卉。其变也,云何尝以意而为之?龙之乘乎云也,自适其性尔,感而为雨,泽彼下土,不几于神乎?使曰龙之致之,虽问于龙,龙亦不知。夫子之为文,以是求之,可乎?”浚川子辗然而笑曰:“有是哉!”[2](P413-414)
这则笔记生动表现了王廷相的文学创作主张,即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也不是不得不做的表白,而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强烈感受后的性情的自然流露。王廷相崇古而不囿于古,其“文以阐道”和“文出自然”的文学主张为当时的文坛开辟了新的思路,体现出中原理学人士在文学理论上的独立人格精神。
崔铣(1478—1551),字仲凫,一字后渠,又号洹野,世称后渠先生,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等职,著有《洹词》和《彰德府志》。崔铣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其诗论主张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诗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夫物生而有情,情而思宣之,斯生言矣。”(《刻文章正宗序》)又说:“诗发乎情,情感乎时,治则乐则颂,衰则忧则刺,乱则恸。”(《刊陶诗后序》)在评论李梦阳与何景明的文学理论时,崔铣说:“其时北郡李梦阳、申阳何景明协表诗法,曰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二子抗节遐举,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学者尊如李、杜焉。”(《胡氏集序》)另外,崔铣最早将《水浒》与《史记》相提并论。作家李开先在《一笑散》中说:“崔后渠(崔铣)……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这些都表明,崔铣持重包容的文学观正是中原文化精神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体现。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原为保定府容城县人,后迁居河南辉县夏峰村,世称夏峰先生。孙奇逢并不以文学成就著称,但其诗文创作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作品以求真写实、直抒胸臆为特色。如《沙河战士歌》写清兵围攻容城、沙河村村民杨可正率领家人及乡亲与清兵浴血奋战的事迹:“谁云兵锋不可挡,只缘胆裂手脚忙。杨氏可正称无敌,携子慷慨护其乡。以绳缚虎如缚兔,四面受敌神愈王。”接下来分写其大儿、小儿及其乡亲们与清兵的战斗,最后以歌颂义士们“纵死犹闻烈骨香”结束。像这样直接描写与清兵的战斗、歌颂抗清义士的诗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孙奇逢的诗文创作平实质朴,不事藻绘,叙事抒怀情真意挚。虽然孙奇逢没有直接提出文学理论,但他以创作实践印证了其求真写实的文学主张,体现出中原理学家之文学理论重实践、求真实的思想特色。
明清时期中原理学家的文学理论具有融合开放、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思想特色,蕴含着中原人文精神。白一瑾指出:“前七子并不仅仅是依照某种诗学取向和思潮组合而成的文学团体,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籍贯还是诗学主张,这个文学团体都带有极为浓厚的北方地域文化色彩。”[3]这一“北方地域文化色彩”无疑与明清时期中原理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中原理学家的文学创作
1.以明道、忧国为主题取向
曹端现存诗16首,多陈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礼与忠孝节义,不假修饰,全无文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端诗皆《击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质直朴素,不以章句为工。然人品既已醇正,学问又复笃实,直抒所见,皆根理要。”
孙奇逢创作了许多阐道诗。如《读许鲁斋集》云:“我读公遗书,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运,民彝已无主。公等二三辈,得君为之辅。伦理未全绝,此功非小补。不陈伐宋谋,天日昭肺腑。题墓有遗言,公意有所取。众以此诮公,未免儒而腐。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又如《书感》云:“我来千余里,思见英雄人。胸中罗今古,万物待其新。人也而天游,钓渭与耕莘。不然隐君子,山水乐相邻。丘壑适吾意,皎洁不染尘。二者俱悠邈,斯道竟沈沦。乃知古人出,尧舜其君民。退处林泉下,坐使风俗淳。仁可覆天下,亦可善此身。此字不分明,痛痒总不亲。庸众是非泯,英雄好恶真。此是经纶手,千古无等伦。”
中原理学家论道旨在经世致用,而非空言心性。在“阐道”思想指导下,作品普遍表现出儒家浓重的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王廷相提倡文学“感时愤世,忧在天下”,其诗多写世事维艰、人生无常、奸臣祸国、小人得志等,表现了深切的忧国情怀。如《西山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宦官横行不法的累累罪行,“卖官何止金为堂,通贿能令鬼上树”,“熏天气焰侔天子,嘘之者生啐者死”。又如《西京篇》挖苦谩求神仙的荒唐举动,“羡门子晋终不至,蓬壶方丈难相通”。
2.内容以注重性情、富有机趣为特点
在晚明重情思潮影响下,注重性情成为文坛创作的普遍倾向。虽同为注重性情,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派与中原理学家的重情,在内容、表达形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概而言之,性灵派注重的多是男女之情,而中原理学家更注重伦理亲情及朋友之情。
曹端现存16首诗多写夫妇、兄弟、父子之情。如其《兄弟》诗云:“堪叹今人这样愚,亲亲兄弟各分居。陈褒畜犬犹知义,何乃为人反不知。”其《诫子诗》云:“越奸越狡越贫穷,奸狡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狡得,世间痴汉叹西风。”虽然质朴有余而诗味不足,且全是说教,但它反映了作者对伦理亲情的重视。
何塘(1474—1543),明代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明史》将其列入《儒林传》,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品相当丰富的文学家。他早年初为官而离家时,写了一些充满人伦亲情的思亲怀乡之作。如其《癸亥杂诗八首》其二云:“故园门巷枕黄河,散乱牛羊草满坡。两岸夕阳行客棹,一犁春雨老农蓑。拨醅酒熟尊颜醉,击缶声喧稚子歌。一别天涯几芳草,梦回茅屋月明多。”对故乡的怀念化为宁静、自然、优美的意境,如一幅山水画印在作者心中。《冬日杂兴四首》其一云:“重衾不成寐,展转冬夜长。神疲一合眼,忽已升高堂。衣裳问燠寒,拜跪陈酒浆。梦觉鸡乱啼,渺然天一方。草芥视天下,感念焚中肠。却忆过庭训,儿当佐虞唐。”这是在写作者刚出外为官时对父母的思念,情感真挚,意境高远。
何塘文集《柏斋集》里有大量的友朋赠答之作。如《赠通渭王应祥》:“三十年前旧弟兄,一樽相对眼偏明。云山此去依春陇,车马何时复帝京。世易蹉跎男子志,老难离别故人情。关中知己如相问,报道新来欲避名。”
在王廷相、孙奇逢、汤斌等人的作品中也有大量亲友赠答的作品,感情真挚,表现了中原理学家注重人伦性情的一面。不仅如此,在中原理学家的文学作品里多能见到展现作者丰富审美情感且富有机趣的文字。
王廷相对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民歌民谣非常重视,认为民歌朴素纯真,格式自由活泼,值得借鉴。如《江南曲》诗:“采蘅金陵江,往来石城道。不问江南人,安识江南草。江上杨柳花,袅袅不肯住。随燕入帘栊,因风复飞去。”其写景抒情小诗也雅秀可观,如《春草谣》:“塘上草离离,照妾春罗衣。待君君不来,满庭萤火飞。”诗意凄迷婉转,令人遐思无限。
孙奇逢诗中也不乏超然物外、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机趣之作。如《述怀》诗:“五月羊裘公,平揖抗天子。岂非济川才,所志乃如是。”“我本抱瓮人,荣华淡如水。饥溺不关身,脱然何所累。”既有慷慨的胸怀,又有超然物外的洒脱。《山居》之“溪声环枕上,月色入怀中”,《春日独坐》之“白云宿户满,明月映篱斜”,《友人出游不及从赋此》之“云横不渡山容媚,雨细初停花气鲜”,《饮马玉笋尊五楼》之“天阔尚容翔野鹤,楼空正好贮孤云”等,清新怡人,富有机趣。
汤斌(1628—1687),河南睢州人。他虽是理学家,实际上是“以词科入翰林”,所以他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赋杂文,亦皆彬彬典雅,无村塾鄙俚之气”。其作品既有雄浑峻逸之作,也有清婉自然的小诗,清新动人、意境高远。如《题画》诗:“秋林不厌静,高士能自闲。尽日茅亭下,开窗对远山。”诗情画意,清雅娴静。他也善于写词,有《潜庵诗余》卷传世,词风典雅秀丽,展示了这位廉吏、理学名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三、中原理学家文学风格成因探析
1.兼容并包,博采众长
明清时期,天下学术不在程朱便在陆王,多有门户之争。中原理学家在如何对待这两派之争上,表现出鲜明的不拘门户之见而兼采众长的学术胸襟,从曹端、何塘、王廷相、吕坤到孙奇逢、汤斌、耿介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曹端在提倡程朱理学的同时,注重心性的涵养与实践,注重知行合一;王廷相在批判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同时,倡导“有用之学”和“治己之学”,保持了独立反省和思想批判的立场。
清初,朝廷出于统治需要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科举考试沿用明制,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家的疏解为标准。清初至雍正年间,出现了一些独尊程朱的理学家,他们反对王学,力倡朱学,受到统治者赏识。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汤斌论学却不主学术论辩,而是兼采理学与心学之长,试图以两家互补为学术寻找新的出路,显示出中原学者持重包容的胸襟。对于明末以来学界的空疏不实之风,汤斌认为责任不在王守仁而在王学末学之流弊,在挽救朱学、返本归原上王守仁功不可没。他说:“后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训诂,泛滥名物,几于支离而无本。王守仁致良知之教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流弊,然或语上而遗下,偏重而失中,门人以虚见承袭,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王畿四无之说出,益洸洋恣肆,失其宗旨,其流弊有甚焉者。”[4]他认为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都是圣人之道的嫡派真传,完全可以形成互补关系。
中原理学家一贯的文学主张源自中原文化的为学求实、兼容并包、兼采众长的学风,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文人的处世原则及思维方式,并对明清之际的士人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2.文化正统观念与经世致用主张
宋代以前,中原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人文精神在中华文化中居于正统地位,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精神。[5]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面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和曾经的辉煌,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并没有随之丧失,中原文化精神中的积极因素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中原士人将各家之长统一于“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之中,与清初的启蒙思想息息相通。曹端为学重躬行实践,何塘反对清谈、主张务实,反对记诵词章之学或坐谈心性,汤斌更是把“躬行”作为调和理学与心学的法宝。如关于理学是非的问题,汤斌认为:“理学者本乎天理,合乎人心,尧、舜、孔、孟以来总是此理,原不分时代。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在躬行,近人辩论太繁耳。”[6]汤斌的回答巧妙地回避了关于理学内部不同观点的是非之争,从“学以致用”角度强调了理学“重在躬行”的意义。
中原理学家多注重实践和事功,促进了明清之际学术研究由理学及王学末流向实学的转型,显示了中原理学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这种重视事功的实学传统使中原士人形成了积极的从政为民意识,文学创作上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
3.革除旧弊,树立新风
中原理学家在文学主张上大多遵循儒家传统的诗教理论,并进行适当的革新。王廷相的“文以阐道”与“无意于为文”、崔铣“诗发乎情”的诗歌理论主张等,既没有脱离传统儒家诗教范围,而又能自出新意,在继承传统中熔铸众长、革除旧弊。他们在自觉的匡世救弊思想指导下,既有着正统性和保守性特点,又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
慷慨激越的中州士风是中原文人的典型特征。“前七子”皆为进士出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林风气非常不满,文学创作上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文风和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李梦阳从登进士到被罢官20余年间,官不过四品,却被免职4年、下狱4次,表现了他为官刚正、宁折不屈的斗争精神。何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明史·文苑传》)。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三事》中刻画的那位严正清明、不徇私情而又不乏正义和同情心的王翱形象,正是中州士人理想人格的化身。王廷相在陕西任上因严厉打击阉党势力而被构陷下狱,孙奇逢直面清军入关的血腥,这些典型都是鲜明的中原人文精神的体现,这些中原理学家的文学作品里有大量批评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他们以刚健质朴的中州风骨和雅正中和之美的追求,自觉抵制、矫正文坛的低俗、情欲泛滥等各种流弊。总之,无论作家本身还是其文学创作,明清中原理学家都表现出了特有的中原人文精神。
[1]王永宽.河南文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683.
[2]王廷相.王廷相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白一瑾.北方“正统”与江南“变体”——论明七子在清初传承的两条主线[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80.
[4]汤斌.汤斌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9.
[5]王宝国.文化纽带与国家统一——以中原文化为中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36.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2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4:1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