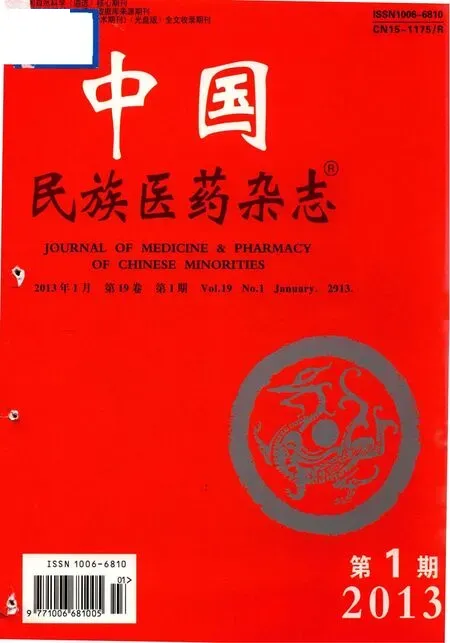蒙医传统肠疗剂对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浅析△
2013-01-24布图雅
布图雅 双 梅
(1.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2.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
蒙医药是祖国民族医药的组成部分,是在蒙古族游牧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具有蒙古特色的传统医学。其核心是基于阴阳学说的整体论〔1〕。该指导思想在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诊治中仍贯穿始终,不仅临床疗效满意,且通过动物实验也得以证实。下面,我们就UC、蒙医肠疗以及肠疗剂进行简要述评,以探讨蒙医肠疗对UC的治疗作用。
1 关于溃疡性结肠炎
1.1 西医研究概要
1.1.1 病因病机: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未明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病变多从直肠开始,逆行向近端发展,可累及全结肠及末端回肠,呈连续性弥漫性分布。病变常局限于黏膜和黏膜下层。临床表现为血便,可有腹痛和腹泻,重症患者可有全身症状。部分患者有肠外表现,包括口腔溃疡、关节炎、脊柱炎、肝胆管炎、眼葡萄膜炎及皮炎等。目前,认为其发病机制可能是由于环境细菌等因素作用于具有遗传易感性的宿主引起的肠黏膜或系统免疫紊乱和炎症反应〔2〕。所以,细菌、免疫紊乱、炎症反应是关键因素,肠黏膜损害是最终结果,血便、腹痛和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
1.1.2 治疗:西医治疗通常根据疾病的活动性、严重度与病变范围“对号入座”地进行选择,主要应用氨基水杨酸(5-ASA)、糖皮质激素(GCS)和免疫抑制剂(IS)等3类药物,采用不同的途径给药。重症和顽固性UC涉及IS和生物治疗剂的使用,以及外科手术,对轻中度UC口服加局部治疗的常规治疗方案仍行之有效,治疗的着眼点主要是临床症状[3]。
近年研究发现,症状治疗使40% ~50%的UC仍常年持续活动;随病程延长累及癌变的可能性增加,10年为2%、20年为8%、30年为18%;由于慢性活动和各种并发症导致20%以上的UC采用手术治疗[4]。而治疗的迟延和持续的炎症导致不可逆的黏膜损伤和肠功能减退,即使强力的治疗也无济于事。因此,现代治疗的目标是在疾病早期尽快控制发作、不用激素维持缓解、内镜下黏膜愈合、降低住院率与手术率,以提高生活质量[5]。正因为如此,有关其病因、发病机制以及治疗药物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6]。而随着人们预防保健意识的日益提高和对大肠生理功能的深入研究,肛肠途径给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1.2 蒙医研究概要
1.2.1 病因病机:UC属于蒙医学“结肠型宝如病”范畴,通常称为“呼日穆拉病”(聚合病变)。是在外因的作用下,体内三根七素平衡紊乱所产生的恶血伤及胃,形成该病的热性条件。或在胃内进行的食物初级清浊分化过程受到影响致使巴达干增多,影响“血”的正常形成,由此产生的恶血重返至胃形成该病的冷性条件。热、冷条件所致恶血从胃达小肠,与希拉聚合,再达大肠与赫依结合,最终形成由血、巴达干、希拉、赫依等多重病因所致的“结肠型宝如病”[7]。所以,血、巴达干、希拉、赫依是发病关键因素。
1.2.2 治疗:蒙医治疗以调和体素、消除赫依血热后遗为基本原则辨证论治。根据病情,施以清热、调和赫依血相搏的“土木香-4味汤”、开郁顺气、化滞消胀的“奥鲁盖因阿纳日-13”、杀粘止痛的“嘎日迪-5”、清肝凉血的“格旺-9”等蒙药进行治疗,同时充分注意协调病变所累脏腑功能,从整体上调和三根七素和脏腑功能。
除内服药物治疗外,还有酸马奶疗法、天然阿尔善疗法、温针疗法、放血疗法、灸疗及萨麻真疗法、图力摩疗法等。其中尼如哈疗法效果显著[8]。
2 蒙医肠疗-尼如哈疗法
“尼如哈”为梵语音译名词,由下排除之意。是由肛门注入药液,进行保留灌肠而引病外出,从而达到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作用的一种外治疗法。
有资料显示,早在3~4世纪,埃及人观察一种神鸟发明了“灌肠疗法”。此疗法逐渐被人们认可并风靡一时,17世纪被誉为肠疗世纪。蒙古族人民在很早以前便使用泻下法即通过肠道排毒治疗疾病。最初的尼如哈疗法是将药液注入牛、羊等动物的胃或膀胱内,其口与铁或铜制的根部可容拇指、尖部可容豆粒大小的牛尾形十二指长细管固定进行操作。应用于食不消、肠疾、温病、胃病、结肠病、痞、尿闭、中毒、妇科疾病(孕期疾病除外)、老年病等临床诸科疾病的治疗,积累了可贵的临床经验。随着现代蒙医学的逐步发展与完善,运用蒙医尼如哈疗法结合蒙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报道屡见不鲜[9][10][11][12]。
3 蒙医传统肠疗剂解析
传统肠疗剂分锐剂、中剂、柔剂三型。由于我们在动物实验中采用的是柔剂,故本文仅对柔剂进行解析。柔剂由诃子、枇杷叶、茜草、大黄、藜芦、秦艽花、牛奶等组成。
3.1 现代研究
3.1.1 洗肠排毒:自古至今,中西医皆有“大肠是百病之源”的理论[13]。通过肠疗可将滞留在大肠中的粪便软化、排出,较彻底地清洁肠道,必然起到了洗肠排毒、保护肠黏膜的作用。
3.1.2 抗炎、抗菌、抗病毒:诃子是蒙药方剂最常用的药物,为药中之王[14]。现代药理学认为其提取物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多种药理活性[15]。另外,方中枇杷叶[16]、茜草[17]、大黄[18]、藜芦[19]、秦艽花[20]等也具有抗炎、抗菌、抗病毒作用。而Hermon-Taylor和Bull研究提示,副结核分枝杆菌与UC有关系,副结核分枝杆菌在巴氏奶中存在,在UC患者当中感染率也很高,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UC的发生和肠道内的菌群情况有很大的关系[21]。
3.1.3 免疫调节:研究证明,方中茜草、大黄、秦艽花3味药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而在人巨细胞病毒(HCMV)诱导的自身免疫导致的炎症性肠病(IBD)中,细胞毒素CD13被认为可能是IBD的一种特异性自身抗体,在HCMV-IgG阳性UC患者血清中其阳性率约占66%,重度UC中可达85%;在UC患者肠、眼、关节等处均可发现CD13,而正常对照组中没有发现[22]。说明UC的发病与免疫密切相关。
3.1.4 抗氧化:方中诃子、枇杷叶、茜草、大黄的抗氧化作用会在增强机体免疫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促进UC的转归。
3.1.5 止泻: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是UC的主要临床表现。方中诃子、茜草具有止泻功效。而大黄有致泻和止泻的不同功能,这种作用表现在用于人体时,常因剂量不同而功能不同,应用大剂量时(5g以上)出现泻下,而小剂量(1g以下)则主要出现便秘[23]。
3.1.6 止血:黏液脓血便是UC的主要症状之一,也是诊断的重要指标。重症UC或病情持续活动,可由于血便而导致贫血、低蛋白血症等。所以,止血尤为重要。而方中茜草具有止泻、止血双重功效。
3.1.7 敛疮止腐:UC患者结肠黏膜表层有不同程度的糜烂与溃疡形成。研究表明,藜芦、大黄可敛疮止腐,促进伤口愈合。
另外,牛奶具有丰富的营养,并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B1、维生素B2、钙以及人体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3.2 传统认识
3.2.1 诃子:药味:《论述医典》载:诃子除咸味外其他五味兼备。《八支》载:诃子味淡,消化后味甘。药性:较热。药效:具备强壮补命脉,助消化,健胃等作用,治龙(赫依)、赤巴(希拉)、培根病(巴达干)[24]。
3.2.2 枇杷叶:药味:苦[25]。药性:凉。药效:清肺热、肾损伤热。
3.2.3 茜草:药味:苦。药性:凉。药效:清肺热、肾热、伤热。
3.2.4 大黄:药味:苦、酸。药性:凉、平。药效:清热解毒,治六腑热,培根病。
3.2.5 藜芦:药味:苦、辛。药性:温。药效:引吐、泻诸病。
3.2.6 秦艽花:分白、黑两种。药味:二者均苦。药性:二者均凉。药效:白者清腑热、胆热;黑者清胆热、脏热、消肿、燥黄水。
3.2.7 奶:是蒙医认为,奶是龙(赫依)病饮料之首。而且,红母牛尿、粪、奶、酸奶、酥油和蜜五药配制叫“五味黄牛油丸”,可治旧肝病,龙性热症,黄水病,浮肿[26]。也有“牛奶治肺疾…是滋补之上品”等记载[27]。
4 讨论和总结
4.1 肠疗治疗UC是蒙西医公认的具有良好疗效的治疗方法。
4.2 现代研究证明,蒙医传统肠疗剂具备了消炎、抗肿瘤、抗氧化,止血,调节免疫等多重功效。通过分析,方中大部分成分具有抗炎、抗菌、抗病毒作用,其次是免疫调节和抗氧化功能居多,止泻、止血、敛疮止腐功效成分较少。而细菌、免疫紊乱、炎症反应是UC关键致病因素,肠黏膜损害是其最终结果,血便、腹痛和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所以说,传统肠疗剂主要是通过去除UC病因,缓解其主要临床症状而起到治疗效果的。
从传统认识角度分析,传统肠疗剂成分味苦性凉成分占了绝大数,说明该方偏凉。而且,清热、清脏腑热尤其清肺、肾、肝、胆热之功效显著。蒙医将UC按病程分三期,病初期热、中期寒热相搏、晚期寒。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传统肠疗剂之柔剂更适合于UC初期的治疗。其次,肝营血,肝胆为相应脏腑,从解剖位置到生理病理改变关系密切。而血是UC的主要病因。从五行学讲,肺和肾呈母子关系,而肺又和大肠相应。近年来,关于分泌型IgA(SIgA)的研究逐渐揭示了呼吸道黏膜与肠道黏膜的内在联系,从而赋予了“肺与大肠相表”新的内涵[28]。概括讲,传统肠疗剂是针对UC主要病因和病理改变,注重脏腑的内在关系,从整体出发,调平寒热、协调脏腑关系而达到治疗效果的。
4.3 如今,蒙医以清浊代谢为核心基于阴阳学说的整体理论备受医学界关注和认可,而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的疾病诊治优势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而且,蒙药源于自然,毒副作用相对较小。所以,蒙医肠疗治疗UC是大有可为的,值得研究推广。
[1]宝音仓等.苏荣扎布老师临床经验研究〔J〕.2012年国际传统医学继承与发展论坛论文集,2012,07:31.
[2]宋璐,夏冰等.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及其诊断〔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0,30(11):1056.
[3]欧阳钦.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目标与方案的变迁〔J〕.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2010,3(15):152.
[4]Langholz E,Munkholm P,Davidsen M,et al.Course of ulcerative colitis:analysis of changes in disease activity over years.Gastroen - terology,1994,107:3 -11.
[5]Sandborn WJ.Current directions in IBD therapy:whatgoals are feasible with biological modifiers?Gastroenterology,2008,135:1442 -1447.
[6]于小华,刘晓华等.肠安宁胶囊对大鼠溃疡性结肠炎的实验研究〔J〕.中国药科大学学报,2010,41(6):563-567.
[7]苏荣扎布.蒙医内科学〔M〕.第一版.呼和浩特:民族出版社,1989:143.
[8]布图雅.蒙医尼如哈疗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方药证治规律研究〔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0,7(7):39—40.
[9]龙梅.蒙西医结合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160例体会[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4,6623.
[10]阿若娜.蒙医辩证分型配合灌肠治疗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23例[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0,6(3)13.
[11]呼日乐.蒙药内服与保留灌肠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1,7(2)38.
[12]恩和巴图.尼如哈疗法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77,3(增刊 )44.
[13]杜平,梁仲惠.结肠水疗的临床应用[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18(3):339.
[14]罗布桑,等.蒙药正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124.
[15]杨永康,格桑索朗,吴家坤.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的植物分类研究和药学特性综述[J].中国医学生物技术应用杂志,2004,3(1):14 -25.
[16]Shin T Y,Jeong H J,Kim D K,et a1.Inhibitory action of water soluble fraction of Terminalia chebula on systemicand local anaphylaxis[J].JEthnopharmacol,2001,74(2):133—140.
[17]杨胜利,刘发.茜草的药理作用及应用实例[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5,8(8):588.
[18][19]张永祥.中药药理学新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61.195.
[20]徐泽红.中药秦艽的研究进展[J].中国医药导报.2008 ,5(6):29.
[21]关军丽.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因研究现况[J].山西医药杂志,2010,39(10):944.
[22]孙贵张,卜平,孔桂美.溃疡性结肠炎免疫学发病机制进展[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08,17(4):266.
[23]邓毅.中药的优势一双向调节作用[J].内蒙古中医药,2010,13:108.
[24][26]罗布桑,等.蒙药正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2:125.440.
[25]白清云.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07:393.
[27]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编译.蓝琉璃(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08:212.
[28]靳桂春,王晞星,冯玛莉,等.中医肠疗理论体系构架初探[J].中华中医药杂志(原中国医药学报)2011,26(11):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