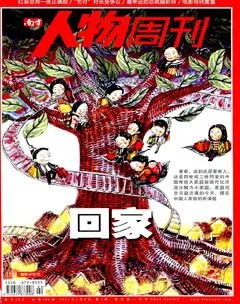“乞讨”村长
2012-12-29张蕾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2期


2011年12月20日,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白家寨村村长白彦民在郑州街头铺上一大块白纸,上书“为村里修路借钱”字样。他在白纸上跪了几个小时,讨到135块钱,其中100块还是来采访的记者给的。
一个中年路人嗤着鼻子,说:“当村干部能没有钱?你们村政府就把你逼到这个地步?骗谁啊?你拿回去这个钱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
白彦民随即咬破手指,只流出很少的血,写在纸上的“永不贪污”显得那么虚弱。他把冻僵的手指咬扁了,依然不出血,他不觉得疼,却突然嚎啕大哭。
“就是心疼,我猛然觉得心里压力过大,对政府、社会,对有钱人、干部那种情绪就发泄出来。”白彦民趴在那块“情况说明”上,嚎了半分钟,声音特别大。两分钟后,血稠稠地流出来。围观的老年人都说“别写了”,胆小的年轻人则跑开。
“村长为修路街头乞讨”的视频传到网上时,作者截掉了白彦民嚎啕大哭的场面。
被乡镇政府劝回村子的白彦民,一张口说话,村民觉得他哑巴了,只当他是为修路上火嗓子发炎,没人知道是哭哑的。
白彦民扯着嘶哑的嗓子,在村部广播喇叭里、电话里、铲车边、搅拌机旁,继续指挥修路。
“骗子”
从郑州刚回到村子时,白彦民听说,村里人看到电视里的自己,男男女女都哭。
“1976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哭,那是真的哭。这以后,我们村里人除了自己家的事,没有为哪个干部哭过。”白彦民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死了,也很满足。
12月29日这天,南小勇(化名)一直在白彦民家守着,不吃不喝,只睡觉。21号的时候,白彦民打电话对他说,欠他的3万块有眉目了,政府会管钱的事。南小勇兴冲冲赶回来,白彦民手一摊,说,政府只管这次的,以前的欠款,还是填不上。南小勇气得绝食,又不知道拿这个村长朋友怎么办。
晚上,在白家中间堂屋,白彦民和他的债主之一南小勇团在后者借来的电暖气旁。白彦民张开手烤火,右手食指尖上结结实实少了葡萄干大小的一块皮。
白:“那天白天的时候疼得不是很厉害,晚上时指头头两节肿的跟大拇指一样粗,疼了一个晚上。”
南:“你不应该乞讨的。”
白:“没办法……说是‘乞讨’,但这个说法很别扭。我只是用跪的方式希望大家借给我钱。在中国的文字里,‘乞讨’应该是以讨饭为生活方式的,如果牵涉到一些大家利益的事情……就像民工跟老板要钱,如果有些什么动作(下跪),并不是乞讨,只是要的方式不同而已。”
南小勇把头扭向记者,改用普通话说:“你感不感觉他的这种解释有点像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
大伙都笑。
村里人称白家寨为“塬上”。通俗地解释,“塬”就是土包。在这个塬上,地里钻出烟囱,地下便是村里人以前居住的窑洞(有些窑洞现在仍有人居住)。白彦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的这块地盘——“安史之乱”时,叛军从函谷关来,唐朝军队从西安来,在这里交锋,兵马死伤最多也是在这,所谓“安禄山史思明兵败大西塬”就是此地。
白家寨在涧河西塬上,地势比邻村高,土质和光照没有邻村好。人家是灵宝的葡萄养殖基地,而白家寨只能种苹果。要命的是,种出来的便宜苹果,运不出去。2006年,一辆载重20吨的山东货车开到村口,在距离村子20米处的十字路口,拐不过弯,回身,空着走掉了。
这件事对白彦民震动很大,修路迫在眉睫。2008年他当选村长后,便把进村的路修通,2011年他又一次当选,第三天就开始着手修路。
此番乞讨,白彦民只准备讨借3万块,为了修两段路,加起来270米的土坡坡。3万块只是这270米路一半工程的钱,白彦民想先付上一半,余下的明年再想办法。
270米中,有110米左右是村子的主干道,白彦民把它修成“人字形”,“再大的车都可以随意回车”,下雪下雨村民走路也不会摔倒了。
可白家寨村委会杨书记却认为,白彦民的修路行为没有通过村委会、支部会、村民代表大会,也没有通过“4+2”工作法程序的确定,属私自行为。
白彦民承认自己“不开会”是不对的。2008年修村头那条南北向的路之前,他就这样考虑过:从80年代到现在,关于这条路开的会不下十次八次,每茬干部三五年,至少经历过三任干部,开会开半天也说不出结果,大家互相推诿,最后一点劲头也没了。08年村委会和支部委员会的意见也可以想象:因为没有钱,路肯定修不成;即使有钱,村干部都盘算着自己没有利润,也不会去修;更何况修路要清理沿途的果树,折树的村民不满,修路得罪人。
“村委会和支部委员一共5个人,一个人是中间派,3个人(一起的)不支持,还是我一个人,你说开会怎么办?3个人反对,一个人弃权,我一个人同意,这是无效的呀。”于是白彦民决定,要修路,就不能开会。
“这个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并不完全正确。”
钱是白彦民借的,矛盾是他去调解的,过程还算顺利。
把路弄平了之后,有人埋怨白彦民:修路是好事,本来就能弄成,应该先开个会,开了会也能弄成,还名正言顺。
白彦民打着哈哈,说:“对呀,确实是应该开会的,我错了,我下次开会。”其时他心里想,一辈子能修几条路,开什么会啊。
“我这么做,有点像张作霖,说一套,做一套。但我是为了村里人做事,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做成了,凭你到哪里去问,老百姓没有人说我错的。”
回村后,杨书记教育白彦民说:“你看,最后还是政府给你处理问题,不是政府出面,不是三门峡广电局(对口扶贫单位,为白家寨出两万元修路),谁能给你要出钱?你看吧,你要是不去,这钱也还是政府给出。”
三门峡广电局颁发扶贫款那天,村部来了二十多个科级干部,镇长也在场。面对领导、老百姓和媒体,白彦民鞠了3个躬。
“我要道歉。确实,我为灵宝、三门峡政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今天你(三门峡广电局)捐了2万块钱,虽然跟我们所需要的钱还是相差很多,但还是能把这条路修起来。我愿意道歉。……首先是给老百姓道歉,我是村长,做这个随意了,没有经过村民大会,没有经过所有老百姓同意,我就跪下来,也就是对我们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嘛。……也给杨书记道歉,你们没给村里什么钱,是你们当干部的方式,也不是什么大的罪,就算是大罪,也不应该由我在公众和媒体面前说三道四,我说了,对你们不好,为了工作,我想给你们道歉。以后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为村里做事。”
之后,白彦民还在杨书记的几番劝说下写了检讨并保证书,即以后“尽量不增加村里负担;尽量跟党支部保持一致,开会研究;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起码不能采取过激行为”。
白彦民希望这种保证能换来上级政府对修路款的接管,但目前乡镇只将这270米的一半路款即三四万元到账,白彦民之前所修的3.9公里巷道和村路所欠下的三十多万元,还是没人埋单。
南小勇说白彦民,“你这个人啊,可怜,可恨。可怜,是因为确实为村民做了很多事,但太穷,搞得自己日子都过不成。可恨,是因为你赊人家的钱不还,人家还要过日子不?”
“一开始我修路(赊钱),不是骗人家,不是不打算还人家。”
白彦民说自己当时对还钱方式是有着美好设想的,但“计划可能有些莽撞”。
“我的想法是这个路修好了,我就有权威了,然后我就可以从某些地方拿到钱去搞生意和企业,(还)这几十万算什么。想得特别美。那是一个泡影,不可能的事。现实是,路打成了,‘骗局’形成了。”
2009年4月底,修好进村路后,白彦民到灵宝市新区开了一个“中医自然疗法培训学校”,争取到6万元的投资,却因为有讨债的上门,不得不抽出两万先还债了。余下4万元,两万用来买学校所需物品,然后,“资金链就断了”。债主收回摊子,白彦民也没了法子还欠债。逢年过节便只能出门躲债。
“我不知道我能给老百姓干多少事情,但是我希望我能像过去的周总理那样,夜以继日不分昼夜地,能干多少干多少。尽管像有些人说的我是骗子,骗子就骗子,这能让老百姓有益处。”
麻烦制造者
110米的“人字形”村路主干道修好后,白彦民指挥村民赶修另外160米的土坡路。村民们都知道白彦民为了修这路,付出了什么代价,他们这样议论村长:
赤眼佬:“他是我们民族英雄啊。”
高个儿:“这个白主任确确实实是为农民办事。他本身也是个农民啊,家里的活他都不干,都让媳妇干,他就专门就为村里干活,专门就当村主任。要为农民,这个人真是不惜一切代价,不往自己兜里装一分钱。”
赤眼佬:“某些人把我们村长歪曲了,出难题,不协调工作……”
高个儿:“他求你办事,你能办就给办,不能办他也没有礼给你送。不会送礼,这是他的一个缺点。”
可在乡镇领导那里,白彦民的名声不好,总是跟麻烦制造者沾边。这次乞讨事件后,他又多了一个外号,“王帅第二”。
2009年,灵宝的大学生王帅在网上发帖诉说家里的土地纠纷,遭到当地政府跨省追捕,引发舆论关注。此后王帅被释放,但据说已经举家搬迁,在灵宝市没有留下一点踪迹了。
2008年以前,白彦民也是个经常上访的主儿。1999年,他了解到国家政策是“种苹果树的地收特产税,种小麦的地收农业税”,而当地两税都收,他就带着村民抗税。他也曾在2002至2005年做过一任村长,把村里的“假党员当上支部书记”的事情捅到了省委组织部;村里没书记,乡里要指派代书记,但乡干部愿意来白家寨跟白彦民共事。此外,他还有诸如试图跳楼之类的过激行为,饱受诟病。
“确实有这回事,(但)首先我没有直接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对准政府。每一次都是正义的,但老是过激,因为我穷,我没有关系,我想达到目的我没有办法,只有采取过激的行为。但都没犯法。”
白彦民家穷。自家院子的土门5月时被连日的雨水冲垮了,至今就敞着院子。家里有个硬沙发,是5块钱买的二手货。
房子是2004年盖的,半边墙砖还裸着,未糊上水泥。白家原本是土房,没钱盖砖房,只因为那一年乡里开会时,有乡干部不点名地说:有些村干部自己连简单的一个房子都没有,怎么能带领群众致富呢?
白彦民被刺痛,但也无从辩解。他去城里干活,给人拆房子,剁下来的废砖运回家,卖一半,剩下一半自己拿来盖房子,到朋友家借点沙子水泥,地板砖是捡人家的,木是自家的,只有天棚和瓷砖是新的,3间房子总共造价5000块。
从2008年再次当选到2011年成功连任,白彦民总不忘“口头培训”村干部:“当咱们村的干部是要吃亏的,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吃亏给村里办事的干部。你可以去领工资,但我不用你。3年很短,再选举的时间,老百姓把你选下来,你就会很惨。大家都知道你这么坏这么不负责任。”
他便很负责任。村委会的公章他时刻带在身上,走在路上碰到村民有事需要处理,他就掏出来。有乡干部取笑他,“成天带着‘屁股章’。”
村书记杨维星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白彦民“性格有问题,想到啥就干啥,从来不顾及同行、领导感受”。
有一天,白彦民骑摩托车碰到邻村的一个干部。“他看见我以后,跟平常的脸色不一样,我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他就是很生气,不吭声。”白彦民这样解释这个“对不起”:“我给村里干点事,我们村越干得多,周边村子的群众就越骂他们的村干部。所以所有的村干部,只要不是像我这么做的,也要恨我。”
村部里的黑板上,二十多天前选举的计票栏还没有擦去,白彦民得213票,另一个候选人得125票。不知为什么,白彦民的名字上面却被打了个大叉叉。
村部门口原本挂着3块牌子,从左向右依次是村民监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党支部。如今,独独中间那块牌子也不知被谁给摘走了。
“文化人”
白彦民想着自己要做事,便不在乎旁人的目光。
他在火车站口等记者时,电话eFZY4uSGj4oPesfQwuAuaLkgcdOZvGY4qEnAlxQcu7w=里强调自己的特征是“戴着一副眼镜”。
这一点的确很容易辨识。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戴眼镜的人。
他48岁,微胖,谢顶,脸是农家黑,鼻头似乎尤其黑。大概是因为他自诩“中华鼻书第一人”,自创“鼻子写字”,用鼻头蘸墨汁导致的。
农村人都不戴眼镜,即使眼睛花了看不清,也不戴。白彦民不怕别人挖苦他“洋气”,反而觉得这眼镜是必要。
他左眼视力正常,只戴平光镜;右眼是小时候受过伤,没东西止血便抹了一把面粉,弄得眼底浑浊,有些散光。
“我戴眼镜(的原因)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是因为)戴眼镜,说话做事不粗鲁,有文人气息,自我控制,做事稳重。提醒自己做事要比农村人观念更新、超前,要有文人的思想标准。”
村民们聚在一起讲话,见到白彦民就夸:这是我们村的“焦裕禄”。白彦民也很自得,在他心目中,“焦裕禄”是当干部的标尺。
“我会武术,但我有文化,我知道不能用武的方法解决问题,要法律的手段,用自己做人的高的道德标准去征服别人。现在我很自豪,我征服别人了。”
白彦民热爱这种赞扬。
“人上世以来最大的特点是贪,每一个人都有‘贪’的思想,我其实是个很贪心的人。我贪权,本来应该开会,但我把书记晾在一边——可我贪权(是)为老百姓做事。”
2011年底的这次竞选,第三次当选的白彦民早已不像以前那样,挖空心思承诺,为村民描绘不着边际的美丽愿景。他觉得平时跟老百姓说话,就已经把承诺包含在里面。比如修路这事,一直跟大家说,那就一定得修,没钱就是“不要人格”乞讨也要修,否则没脸见百姓。
这次总算讨到了钱,但以后会怎么样,白彦民心里没底。他的盘算是,如果欠款还是没有着落,而乡镇那边又不高兴他当村长,那么或许只能学王帅举家搬迁。他惟一自信的是,自己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村长了,鼻子写字的技艺应该会得到更大的肯定,到时候养活家人乃至还债,都不成问题了吧。
在人字形路的尽头,陡峭的山坡断了去路。白彦民指着巨大的山沟的对面,说:“从这边看过去有个土岭,弧线下去,到对面靠阳光的地方有个沟,如果我们打一个两公里半的土坝,就能把通往县城的路,从25公里,缩短到8公里。而且这两公里半下去,直接可达河边的一条高速通道的入口,那大道可宽,有50米。我们的路打通了,可以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还可以增加我们村的车流量,大家卖东西、上县城,都方便。这两公里半周遭也是我们村的土地,可以利用起来,盖商品房,盖工厂,那时候我们就跟城里连起来,成为郊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