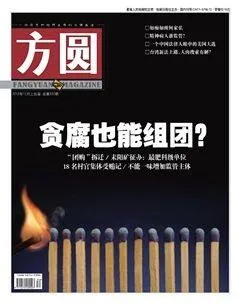不能一味增加监管主体
2012-12-29邬佩怡
方圆 2012年23期
【√】根治组团贪腐首先需找准病根,一味地增多监管主体、加强监管力度只会让雪球越滚越大,使组团贪腐的链条越延越长,只会让组团贪腐向丛林化、生态化发展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名论断,也是《方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在谈及组团贪腐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认为“有权力,即有腐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对“人性本善”的莫大挑战,但却又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近年来,媒体报道过的关于组团腐败的案例层出不穷:“郑筱萸腐败窝案”、“耒阳市矿征办窝案”、“古井贡腐败窝案”、“重庆绿化市政腐败窝案”、“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广州白云区棠溪村岗贝经济社腐败窝案”等等。
从政界到商界,从医院到学校,从高层到农村,组团贪腐发生的领域之广、涉及的人数之多、产生的影响之大都令人触目惊心。究竟,怎样做才能让权力不被滥用?怎样做才能让监管制度不再形同虚设?
立法是否存在空白
“法不责众”是很多组团贪腐者抱有的心态,因此,很多人认为目前刑法有明文规定的组团腐败只是涵盖了现实生活中一小部分组团腐败行为,而大部分组团腐败现象没有被纳入刑罚的规制之中,致使相当多组团腐败的涉案人员只能受到纪律处分,所以他们都呼吁《刑法》能对组团贪腐“重拳出击”。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我们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助理李惠明告诉《方圆》记者。对某些成员采取纪律处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犯罪这个级别的危害性,而不是因为刑法有漏洞致使他们成为“漏网之鱼”。
在李惠明看来,现在社会公众对腐败现象都深恶痛绝、“恨之入骨”,组团贪腐可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容忽视,呼吁刑法“重拳出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就草率地修改刑法,在刑法中添加一些罪名。
“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原则。简单来讲,这个原则要求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在定罪量刑时还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刑法对贪腐领域这一块的犯罪已经规定的比较完善了,组团贪腐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罪名,对集体的每个成员的具体行为都能在刑法中找到处理方式。”李惠明说。
“凡是经济发达、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较为成功的国家,无不设立有严密的权力监督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应的具体制裁措施,从而因腐败犯罪发生诱因的减少而在腐败犯罪的防治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所以,对于集体贪腐的综合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作用,尤其是刑法的作用。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过分夸大刑法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田宏杰认为,刑法“重拳出击”虽然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治“标” 之效;但监管机制的完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在环境对行为人贪欲的诱发和刺激,进而通过犯罪意念的遏制而见治“本”之功。
莫让监管成为一种反作用
“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应当从制度层面着手,去提高犯罪成本,增加涉案人的心理负担,起到一种切实的威慑作用。”在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晶看来,当惩罚成本大于腐败的预期收益时,组团贪腐的现象就会得到遏制。“根治组团贪腐必须要依托公正而可行的制度体系,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使执法者真正独立于特定的利益范围。”
“构建对组团贪腐的权力制约体系还需要从根源上着手,明确组团贪腐发生的原因,对症下药,这样才能标本兼治。”田宏杰认为,治理贪腐从制度层面上来看需要确立起切实的权力监督的体制,避免权力过度集中的运作模式,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前提的存在,即组团贪腐的病根真正被找到。
在孟德斯鸠“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的论断之后,还有一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然而,这样的制度构建却恰恰是贪腐者们“拧成一股绳”的根源所在。
“贪腐者们为什么要组团、为什么要同分一杯羹?原因很简单,因为权力之间是互相制约的,独木不成林,单个的个体妄图完成整个贪污行为几乎不可能,所以就必须建立共同体,让原有的制约不复存在。”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学教授杨建顺告诉记者,“用权力制约权力”这样的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起到反作用,当每个权力的结点都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分子时,所有的监督就会被切断。
“这时就会形成一道铜墙铁壁,内部的监督形同虚设,外部的监督无法渗入。”在杨建顺看来,一味地增多监管主体、加强监管力度只会让雪球越滚越大,使组团贪腐的链条越延越长,只会让组团贪腐向丛林化、生态化发展。对组团贪腐现象而言,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尝试,是一种“堵”多过于“疏”的选择。
做好该做的事
那么,组团贪腐的“医生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其实我们现在的监管不可谓不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设计也不少,为什么还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责任心。”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助理李惠明认为,倘若所有的执法者都能把自身的职责履行好,都富有责任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组团贪腐的链条就很难延伸。
许许多多的组团贪腐案件所透露的不仅仅是某领域内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不到位,更为可怕的是腐败机制在该领域内的形成。“预防集体腐败,重要的不是还要制定多少监督制度,而是应使日常的监督制度真正地运作起来,真正将治理集体腐败现象问责制度落实到底。”李惠明说。
在这一点上,李惠明与杨建顺不谋而合。杨建顺说,“组团贪腐的现象集中体现了长期以来实质的监督没有得到落实的困局。而造成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人心中错误的权力观和利益观,责任心的缺乏让通常的权力制约机制失去效力。”
让程序变“活”
然而,将现有的监管体制落到实处谈何容易?这无异于让一群人去看守一座可以源源生金的金矿,仅凭内心的坚守只会让监管陷入僵局。
“真正的构建行政程序和权力程序工作机制或许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权利的行使、利益的实现需要一个公开的、透明的、过程性的监督。”杨建顺告诉《方圆》记者,真正建立起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把整个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公开化,让它暴露在阳光下,让它接受来自社会、舆论等的监督,将有助于减少腐败的发生。
在他看来,监管职责的切实发挥需要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保障。“贪腐不能根绝,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加以约束。”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公开招投标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建立起相应的说明理由的制度。在招标时,要对所选单位的资质加以说明、证实,在评标时,要让大家知悉专家组的相关情况,要对专家组成的科学性、专业性和独立性加以说明。”
“行政审批领域是组团贪腐的重灾区,各色各样的吃拿卡要有时会被公开宣称为行业潜规则,切实强调程序的正当性、构建科学的政府公开制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些问题。”杨建顺说,“表哥”、“房叔”的出现同样折射出了机制构建的课题,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呼吁其实也是对构建科学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的呼吁。程序不应该停留于静态,而要“活跃”起来,成为极富“生活力”的制度。
“参与型行政”或许是解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我们现在的内部监管部门常常设在一把手之下,工作的时候常常要听从一把手的指挥,让下级去监督上级,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李惠明告诉记者,许多贪腐案件的发生大多都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作祟。一把手常常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一旦他主张,再公开、再民主的决议也只会是一把手的意志。
“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即是这样,校长在本校范围内,从工程发包到采购再到职务调动,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他们只要从票贩子手里买两张空白发票,就能以各种理由大肆报账贪污,几乎没人能管。“学校纪检部门去监督校长,是副职监督正职,效果可想而知。”龚滩中学一名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谈到。
“要解决组团贪腐问题,仅仅对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加以改善还远远不够,自律监管体制的设计同样重要。”杨建顺认为,制度的真正运转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有了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便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它要求建立经常性的、规范性的制度,使责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参与型行政的目标,也是政风建设的基础,是依法执政的基本内容。”
“将行政程序中的自律性规范加以设计,让公众广泛地参与到对行政程序的监督之中,尽可能地对现有监督体制加以完善,这样的设想也许不会立竿见影,但从长远来看是可以期待的。”杨建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