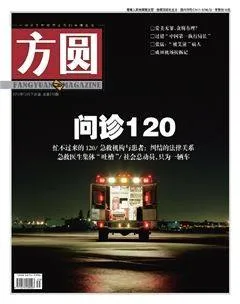我是城管,你是谁?
2012-12-29毛亚楠

周亚鹰说,对《我是城管》一书的争议,其实很大部分源于对城管的争议。所以写这样一本书,就必须解答什么是真正的城管,通过真实的片段,来重现城管所面临的现状的原因以及城管与商贩对立化的根源
12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大会上,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到场。那就是周亚鹰。
上午9时,当周亚鹰身着白衬衣、黑西装踏入大门、穿过人群,径直朝自己的位子走去时,几位文友前来主动与他握手,并拍着他肩膀对周围嘉宾介绍说:“大家看,城管来了!”
散文年会上,在有着梁晓声、王宗仁、苏童等人散文作品的备选行列里,周亚鹰的长篇纪实性散文《我是城管》脱颖而出,获得了中国散文界的最高荣誉“精锐奖”,被认为是此次评奖的最大亮点。
江西广丰人周亚鹰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称:“作家其实是我的副业,我的主业,正如你想象的,就是一位城管。不过,是城管局局长。”
新工作遭误解,写书为其正名
2010年8月16日,素以文化人自居的,担任过记者和文化局副局长的周亚鹰接到广丰县县委指示,从县国资委主任调往县城管局任局长一职。这是周亚鹰从未想过的事情。
在接触城管工作之前,周亚鹰对这项职业并不十分了解,闲暇时间上网,也总是看到网友对城管的负面评价,把城管同工商干部、收红包的庸医和上课不传道的教授统称为“新四害”。所以上任伊始,周亚鹰并无多少喜悦之感。
就任那天,周亚鹰在大街上查看路灯,收到得知他上任城管局局长消息的文友们陆续发来的开玩笑短信,有人甚至写出一幅颇有深意的对联:国资委调往城管局(上联),文明人学做野蛮事(下联),文不对题(横批)。
周亚鹰知道,类似这种评价和挖苦,可能才刚刚开始。
周亚鹰上任两个月以后,现为城管大队长的邓登铭来到城管局报到。邓登铭告诉周亚鹰一件事,让他感慨万千。
邓登铭的女儿以前认为爸爸的工作“很伟大很厉害”,因为“谁违反城市管理规定,都由爸爸带着同事去处分他们”。但是,学校语文模拟考试中的一次看图作文,彻底粉碎了这种形象。图中,一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飞起一脚,一位老年农妇惊恐地倒在地上,一个菜篮子被踩扁,篮子里的物品四散在地。而彪形大汉穿着的制服手臂上,赫然围着“城管执法”的袖章,作文题目是《你用什么去感化城管队员》。
这种将城管工作部分现象作为反例进行的妖魔化宣传,甚至运用到义务教育中,让周亚鹰十分痛心。他甚至开始怀疑,城管执法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实,对城管执法的误解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宣传的潜移默化之中,在城市各个角落,民众对城管的反感几乎随处可见。
一次县里集中整治流浪汉,周亚鹰在一家大药房门前的卷闸门下,看到一个疯疯癫癫的流浪汉,他随之跟同行领导讨论起城市对于流浪汉的收治问题。那个在破棉絮中冻得直发抖的流浪汉看见了,瞪着周亚鹰就骂:“跟老子玩?哼!我叫城管把你赶走!”
平常被那些对城管误解至深的民众数落也就罢了,可当听到这个意识不清的流浪汉口中说出“城管”二字的时候,周亚鹰被深深震撼了:原来社会对城管的认识可以扭曲到如此地步。
2011年8月,周亚鹰参加作协陕西采风之行,他再度面对众文友对其工作的打趣,那一次他下定决心,不再费唇舌解释城管工作的本来面目,他打算将城管的事情写出来。
“我写书,不是为城管做的部分不正确的事情作辩解,而是要通过记录城管工作之中哪怕很小的日常之事,来客观公正地展现给大家、告诉大家,到底真正的城管是什么?以及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城管执法。”周亚鹰告诉《方圆》记者。
为城管写书引争议
在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周亚鹰为城管著书立说,并大声喊出:“我就是城管!”自然迅速吸引了很多关注的目光。
周亚鹰向记者介绍说:“一看到《我是城管》的书名,质疑声和咒骂声便不由分说地砸了过来。”周亚鹰甚至在其新浪博客里“收集”了这些攻击他的声音,汇成一篇长文,名为“这个社会怎么了?——城管人不准写书吗?”
其中,中国江苏网一名时政评论员写文批评周亚鹰著书立说是在“鸣冤叫屈”。文中写道:“周亚鹰局长的文章,急于证明‘城管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质就是无视自身问题的存在,只是利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来为城管撇清责任、鸣冤叫屈,显然不是真正想‘挽回城管形象’,反倒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让人更加反感。”
更有网友直截了当“拍砖”,说这是“王婆卖瓜”、“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个叫“红唇美酒”的网友愤愤不平:“看到你说的那些话,我就非常激动想骂你,说我们妖魔化了你们,难道那些事情或图片都是假的?”
所谓“书名就是生产力”,很多网友开始调侃《我是城管》的书名。《方圆》记者看到,在网易新闻“江西一城管局长著书《我是城管》为中国城管呐喊”后不乏此类回帖:网友“石门一只眼”说:“这个书名不吸引人。我推荐个:《力拔摊兮气盖世——我的城管生涯》。”一位湖北武汉的网友则建议直接用《让小贩飞》这四个字来表达城管牛气冲天的“本事”。
诸如此类半戏谑半责难的评论,在周亚鹰的意料之中,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曾自信地表示:“骂我的网友多半没看过我的书,而是看到‘城管’两个字就进来评论,真正看过这部书的人,都对城管工作有了重新的认识。”
周亚鹰在《我是城管》书中提到一件事,他在调进城管局之前,也曾认为城管所没收的物品会被队员们私下瓜分,因此他甫到城管局就立马询问主持工作的副大队长丁武实情是不是那样,想不到丁武说得斩钉截铁:“周局,冤枉啊!要是我们的队员吃过一个西瓜就烂舌头!所有收缴的物品凡能吃的全部送到敬老院,不能吃的全部堆在仓库,集中处理。”周亚鹰说,在了解城管真实形象的人来说,有些外界的质疑根本不值得相信,这也是他写这本书的目标之一,“让人们知道城管局里真正发生着什么。”
正如周亚鹰所说,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王宗仁在其为《我是城管》写的评论文章《现实生活绽放的散文之花》中坦诚道:“我对城管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之心,真心讲,还是读了周亚鹰的散文《我是城管》之后。”
作家梁晓声则评论此书:“《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书。”作家阿城、蒋建伟、陈奕纯、贾凤山、高尔纯等人也先后为此书作出了肯定的评论。
周亚鹰的作品出版以后,要给这本书拍电视剧的有,开展作品研讨会的也有。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最让周亚鹰感动的,还要属它的读者。
周亚鹰告诉《方圆》记者:“我知道宁波有一个小学生,看了这本书之后,让她的家长想方设法与我取得联系。她告诉我,读我的文章是她暑期最大的收获,但看完后她觉得我写书肯定会得罪不少人,她担心我人身受到威胁,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据《方圆》记者了解,11月17日,周亚鹰在江西南昌举办的新书发布会现场,聚集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通过在场媒体记者的采访,不少人皆透露,平时对城管的印象极差,买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到底城管是个什么样子。
周亚鹰说,对《我是城管》一书的争议,其实很大部分源于对城管的争议。所以写这样一本书,就必须解答什么是真正的城管,通过真实的片段,来重现城管所面临的现状的原因以及城管与商贩对立化的根源。
体制不健全是矛盾的根源
“城管职业为什么会变得让人如此憎恶?我认为是大家的思维定式限制了对其的认识,人们心中的城管定义仅仅为:管街上小贩的那些人。”周亚鹰告诉《方圆》记者,这是大家普遍走入的误区。
周亚鹰说:“其实管理街道的那支队伍叫城管执法队,只是城管的一个小分支。真正的城市管理是管理与服务一体的。从字面意思来讲,城管,顾名思义是城市的管理者。在一个城市区域范围里面,从事城市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都可以称为城管。它包含园林绿化、路灯亮化、环卫净化、市容市貌、煤气燃气、道路维护、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以及城管执法在内等等众多职能。”
那为何人们对城管执法的印象要强于其他方面呢?
“这是由于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周亚鹰坦诚道,执法容易产生矛盾。
谁愿意接受别人的管教?摊贩们都有自己难念的经,不是生活所迫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但城市管理是公共领域,抵触者就要受限受罚,所以必须要有一支执法队伍来维持秩序。说白了,城管执法就是要去得罪人。
周亚鹰在《我是城管》中写道:人管人是最难管的,尤其是那些占道经营的底层弱势群体,当城管队员与小摊小贩发生冲突时,舆论当然会去同情“弱者”,指责之后的结果便是如今这般:城管就是管占道经营小摊小贩,就是踢摊翻篮拗秤打人,就是欺负普通百姓——名誉就是这样被毁的。
“由于目前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不高,执法不当确实是普遍现象。自己不争气,败坏了城管执法形象,我认为是重要原因。”周亚鹰认为首先应当从自身队伍质量中找原因。
而与此相对应的,城管执法的对象缺乏法律意识,亦是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因素。
在《我是城管》一书中,周亚鹰写过一篇《她说城管打她,原来是她打了城管》的文章,将某中年女摊贩柴某同城管巡逻队冲突的始末如实记述下来,当时这篇文章还改变了江西当地媒体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其实现实中,部分小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暴力抗法”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周亚鹰表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的博弈背后,应该重视体制的原因,从体制的不健全去看待矛盾的产生。
周亚鹰在书中指出,我国的城市管理者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到目前为止,连一部完整的关于城市管理的法律都没有,这导致了城管执法缺乏强有力依据的现状。这样一来,城管执法的具体职能未能理顺,各个地方城管职权范围也不统一,谈何有序执法。
更加让周亚鹰担忧的是,部分地区的城管队员居然不具备执法资格。以他所在的广丰县为例,他们的城管队员是不具备执法资格的,“我们广丰县的城管执法主体是建设局,城管局只是建设局的一个派生部门,因此类执法问题难搞又无利可图,就推到城管局里。部门间协调工作情有可原,可要是市民哪天跟城管局一较真,每一起执法官司都必输无疑。”
除了可能出现的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尴尬以外,周亚鹰还认为,城管执法的处罚程序值得探索和完善。他告诉《方圆》记者,一般的执法程序应该是分三步走:说教、下达处罚通知书、出具处罚决定书。但这个流程实施起来颇有难度,许多城管执法都会跳过上述流程直接进行处罚,这样也为日后处理纠纷埋下隐患。“如果人家跟我们打官司,也可以说我们城管‘执法程序不到位’。”周亚鹰说。
这几年的城管工作,周亚鹰认识到,城市管理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体制很难一时之间捋顺,需要长时间地慢慢调整成熟。而在此期间,改善现状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意识层面上进行纠正,向普通民众宣传应有的“城市意识”。
“中国的‘城市病’患得不轻,县一级尤其严重。”周亚鹰表示,中国城市化速度太快,导致“城市病”现象严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政府在物质上没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是民众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准备。
“试想,如果城市没有城管,会是什么状况?城市不能缺少城管。如果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不提高‘城市意识’,谁来当城管都是一样的结果。”周亚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道,“我希望看过我书的人们,能够在书中那些看似很搞笑的交锋故事中反省一些事情,我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市民,或者我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城市管理者。”
周亚鹰向《方圆》记者吐露,以广丰县为例,他希望广丰县能成为“光阴文化”之城,这个设想源自唐末五代十国诗人、广丰县第一位进士王贞白的千古绝句“一寸光阴一寸金”。周亚鹰认为,一座城市应当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标志,一个地方一定要具备它自身的精神向往,没有精神的城市会变得庸俗。这跟他对城管的真实看法不谋而合:“城管要有精神向往,最重要的一点,要有一颗恻隐之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周亚鹰叹了口气,说:“其实每次罚完了他们,我心里就会难受很长时间。他们首先是值得同情的。”
推荐者:周亚鹰
周亚鹰,法学爱好者,《海外文摘》和《散文选刊》签约作家,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精锐奖”得主,著有《我是城管》等作品。
《危机》 艾学蛟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行政艰难推进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污染、矿难、疫病、火灾、血案及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突发事件,无论是普通人群还是社会组织乃至于政府,都很难预防与控制,不仅如此,还因人为的如隐瞒真相、逃避责任等因素而导致事态扩大和危机蔓延,最终产生无数法律问题并致使政府公信力发生严重危机,当这样的危机越集越多时,就可能发生社会断裂。
本书是一部关于政府官员如何防范与控制危机发生,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危机蔓延和危害程度的教科书,被称为最实用的突发事件应用宝典,位居公职的人们应该手有一本。
《官德》 梁衡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通过大量真实、生动、典型的案例,围绕官权与官员的个人修养、从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坦荡、淡泊等十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强官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振聋发聩地提出: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
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不良民德必失,育民德必先修官德。官德高度决定一个法治程度,官德水平决定政权的兴衰成败。十八大之后反腐大旗高举,这无疑是一部官员必读的上好教材。
《美国的崛起》(三部曲) 高国伟译
[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
在中国人提出伟大的“中国梦”的今天,不妨看一下美国是怎样实现“美国梦”的。
本书通过解码美国的公众生活与法治进展,系列地向我们解说了三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上半叶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最终“日不落”英国?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与袖手旁观的政府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美国梦”与时代精神有着怎样的逻辑关联?
本书没有将重点放在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描写上,而是刻意把目光聚焦于公众生活与法治制度的变化上,这是本书优于其它历史类著作的原因。读完这本书,你一定会获得启迪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