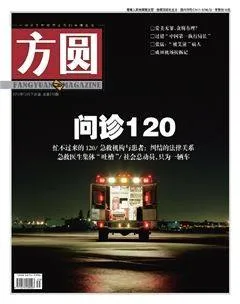张猛:“被艾滋”病人
2012-12-29冯建红

虽然他反复说已经决定将过去放下了,要好好生活。从其言行以及他亲友口中都能得知,这个37岁的东北“大老爷们”,仍纠缠在过往4个月里的种种负面情绪之中,难以脱身
12月10日,是北京市民张猛被“艾滋针”扎伤的第112天,也是女友离开他后的第111天。
自今年8月21日乘坐出租车被艾滋针扎伤后,张猛陷入可能感染HIV病毒的巨大恐惧中,女友离开,工作无法继续,不断吃着大量令人呕吐的阻断药品。在这一百多天里,陪伴他的只有不安、躁动,和难以压抑的怨气。在与《方圆》记者第二次见面并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里,他无时不像一只惊弓之鸟,显得敏感和脆弱。有时即使是很简单的一句安慰,他也会多想,会瞬间暴怒。
自从11月收到医院的检测报告,证实自己并未因针扎事件患上艾滋以后,张猛的正常生活总算是恢复了一部分。
但是,虽然他反复说已经决定将过去放下了,要好好生活。从其言行以及他亲友口中都能得知,这个37岁的东北“大老爷们”,仍纠缠在过往4个月里的种种负面情绪之中,难以脱身。
突如其来的针扎事件
1975年出生的张猛,来自东北边陲的佳木斯,京漂12年,一直从事销售工作。其间,他推销过安利的营养品、倒卖过化妆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销售行业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从一个小推销员,干到销售总监,曾带领过上百人的团队,“是一个干销售的将才”。
经过多年的积累,今年张猛终于全款在老家买了房子,交往了半年的女友,他也打算过年领回家给父母看看,随后也许就张罗着结婚了。但张猛没有想到,一场灾难突然到来。
8月21日晚上,张猛从南京出差回到北京。他下了火车,辗转地铁,在东升派出所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女友住所。出租车行驶到一个拐角,张猛习惯性地跷起二郎腿,但腿抬起一半,忽然被副驾座位左后侧装杂志的塑料筐处的一个尖锐物体扎了一下。
“我觉得很疼,于是喊了司机停车,然后我在塑料筐底部摸到一个尖锐物体,用力拉出来,才发现是一个连着针头的医用注射器。”张猛回忆说,当时他就着路灯的光线,发现针管里面还有一点残留的液体。
张猛的腿部被扎的地方开始出血,和司机协商,司机带他去了京城医院检查。张猛急切想知道针头里的是什么液体,有没有毒。但京城医院做不了这项检查,值班医生提议他们到北医三院看看。
“到了北医三院,医生说应该马上到地坛医院检查,如果是艾滋病HIV病毒的话,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打针和吃药。”张猛说,他开始害怕,怕最担心的事情会发生。
从北医三院出来,出租车司机打了电话报警。
到达地坛医院已是半夜12点,张猛又被告知负责此项检查的医生不在班,让他第二天早上再到皮肤性病科。随后,简单处理下伤口,张猛便回家了。
出租车公司拒绝出面帮助
这一晚,张猛彻夜未眠。装有淡黄色液体的针管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针管里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是不是HIV病毒?
8月22日早上6点,前一晚乘坐的出租车所在的北京华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安排了一位白班司机带张猛又回到地坛医院。但值班医生称依然不能检测,因为他的情况比较复杂,属于意外事故,需要法医鉴定中心来做检测。医生建议张猛先按照是HIV病毒的情况来治疗,服用阻断药物。
张猛拒绝了。“我身体很健康,还要工作,不能等,也没有理由先服药。”张猛说,他站在医院门口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
赶到的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值班民警表示,要申请法医鉴定,必须先立案。他建议张猛找出租车公司,由其出面联系出租车驻地公司派出所,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指定相关机构进行液体检测。
张猛一直惦念着北医三院医生告诉他的24小时期限。从昨晚出事算起,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于是,张猛随同司机迅速来到位于朝阳区窑洼湖附近的华泰公司。
张猛与华泰公司的交涉并不顺利,公司高层拒绝为其提供帮助。
“当时我很愤怒和委屈。他们是经过交管部门正规注册运营的出租公司,乘客在他们车上受了伤,可以不管不顾吗?”
张猛离开华泰公司,只好又一次找警方帮忙。在民警的帮助下,张猛拨打了法律援助热线。一位专家推荐他去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检测。
到达已是下午3点多,距离24个小时仅有6个多小时。
朝阳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待了张猛,随后对他带来的注射器中的残留液体进行了快速检测。但检测结果已经不可能赶在24小时以内出来了。
8月24日,朝阳区疾控中心通知张猛,快速检测结果显示:针管内的残留液体为HIV抗体,阳性。
三天两夜没能安睡的张猛听到检测结果,瘫倒在电话前。“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张猛回忆说,只感觉大脑猛地一片空白,完全蒙了。
当天下午6点左右,在朝阳区疾控中心建议下,张猛前往了地坛医院打针吃药,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张猛的情况当天也被报告给北京市疾控中心。
“从地坛医院拿了药,我一股脑吞进肚里,感到全乱套了。”张猛说。
一下子“出了名”
8月25日,东升派出所联系到张猛,让他到派出所走一趟。原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警队的技术人员和刑侦人员已经介入此事,张猛被艾滋针扎事件正式立案。一同被通知去了解情况的还有事发当晚的出租车司机。
张猛一下子“出了名”。当晚便有5家媒体就此事轮番采访了他。
比起其悲惨遭遇受到关注,张猛更关心的是,自己到底有没有感染HIV病毒。医生告诉他,确定无误的检测结果将在11月出来,但是9月会先出一份初步检测结果,有90%以上的可靠性。
在初步检测结果出来前的这段时间内,张猛每天要服用抗HIV病毒的阻断药物,这种药物副作用非常大。“吃了药整天呕吐、头晕,睡不着,视力模糊,身上起大片大片的红点子。”张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了不忘记吃药,他每天左右两手都攥着药片,时刻提醒自己时间。“医生说,必须严格按时间点吃,12个小时一次。因此即便我睡一会儿,手里还是攥着药片儿。”
身体的不适还好克服,张猛更大的压力来自于恐惧,还有便是孤独感。“在医院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狗。或者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们都告诉他不一定会患上艾滋,但交往中却会对他故意疏远,小心翼翼。
回到住处,张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白天关着窗帘,晚上也不开灯。张猛住的是那种房东自己加盖的水泥房,一层楼里住了8户。因为住得久,和邻居彼此都很熟悉,出事以后,张猛没敢跟任何人提起,“怕他们不理解。”他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抽烟似乎成了张猛唯一解压的方式。他在家没事就不停地抽烟,最多的时候,一天抽了四盒。
张猛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告诉了所在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让他先处理此事,暂时不用上班。张猛自嘲说,这么多年来,自己第一次有这样大把的时间可供挥霍。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调整情绪,9月1日,张猛回了东北老家。
张猛已经六年没有在家过年了,他和父亲的脾气有些“不对付”,但和母亲感情极深。回家见到母亲,对张猛来说多少是个安慰。
回家后,为了不让父母看出异常,张猛找了个理由没和他们住在一起,只身一人住在自家老屋。老屋后院空地上是母亲种的各种蔬菜,还有自发盛放的野花。张猛喜欢这些蔬菜和野花,用手机给它们拍照,总共拍了好几百张。他说,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暂时忘记身体的难受,精神得到放松。
在老家待了19天后,9月20日,张猛从黑龙江回到北京。根据医嘱,张猛把抗HIV的阻断药物暂时停了,还有几天就能看到检测结果。
这几天最难熬。回北京后,张猛依然过着“避世”的生活,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整日整夜颠倒梦乡。有时候屋子里安静得令人恐惧,张猛便打开电视、电脑,刻意制造一些声音。
初步检测结果分两项报告,第一项24号出来了,张猛没有到医院去取,他说要等到第二项报告出来一起拿,免得遭受两次的刺激。
9月28日,第二项报告出来了。张猛来到医院,说明情况以后一名护士递给了他检测报告。他匆匆扫了两眼,看到“阴性”两字以后,攥着右拳猛砸了一下桌子,几乎要跳起来。“阴性!你确定?”“是,阴性,你没感染。”拿着检测报告,张猛连问护士好几遍,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在几十名候诊患者好奇的目光中,张猛拿起检测报告单兴奋地冲出了医院大楼。
应当有人为此事故负责
9月的这份报告,基本确定了张猛没有感染HIV病毒。对张猛来说,这个结果带来的释放,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
1个月零7天,他的体重从148斤降到了122斤。“没人能够想象,过往的一个多月里,我经历了怎样的起伏跌宕。”张猛说,检测结果出来以前,他做过最坏的打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猛曾不止一次强调,即便真的被感染了,他即使“了结自己”,也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更不会报复社会。
两个月以后,最终检测报告出来了,张猛被告知感染艾滋的可能性已彻底排除。
但事情对于张猛来说还没有结束。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之余,张猛认为,自己三个多月以来经受了许多痛苦,应当有人为此负责。
“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药物反应让我感到莫大痛苦,经常想到死亡,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女朋友因为这件事也离开了我,我精神上承受了极大伤害。”张猛说,让他愤愤不平的是,从拒绝帮助联系鉴定机构开始,出租车公司没有人给过他最起码的问候,“仿佛这件事和他们无关一样。”
10月29日,张猛向海淀区法院递交了起诉书,状告当事司机和华泰公司,要求当事司机和出租车公司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余元。
张猛告诉《方圆》记者,他提起诉讼后,有一次去法院查看案件进展时曾遇到当事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经理。在他向前打招呼时,出租车公司经理言辞冷漠,这更坚定了他打官司的决定。
张猛经过多方咨询,还辗转找到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炜衡所)为其代理此案,出于公益的考虑,该律所只象征性地收了100元代理费。11月29日,张猛与该律所正式确定代理关系,他表示将会追加诉讼请求,“一定要让对方公开道歉”。
炜衡所律师张志东告诉《方圆》记者,目前法院只是下发了立案登记通知,正式立案还得再等通知。记者问及是否存在立案难的问题,张志东表示肯定可以立案。
张志东解释说,乘客上车后,就与出租车所有人形成了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302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出租车司机是出租车公司的雇员,开车属于职务行为,出租车公司也应承担管理责任。“据规定,公司有责任和义务要求司机进行检查,提供卫生安全的乘车环境。”张志东说。
“出租车公司首先要承担合同违约赔偿,另外,出租车有保证乘客人身安全的义务,但他们却未能发现安全隐患,造成乘客受伤,根据《侵权责任法》,当事人还可以申请人身损害赔偿。”张猛的另一代理律师郭泽长表示。
维权难度大但具判例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副所长宋朝武认为,像张猛这种情况下,要求出租车赔偿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赔偿多少的问题,特别是精神赔偿这一块,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超过5万。而类似艾滋针扎事件,对受害人的精神伤害恰恰是最大的。
据一些艾滋病专家表示,像张猛这种有过“被艾滋”阴影经历的人,未来还有可能患上恐艾症状。
现实中,患上恐艾症状的人并不鲜见。2011年3月24日,广东《新快报》以一则“阳光下的怪病”曾报道了59位“怪病”患者的生活情况。随后,网络开始流传其为“阴性艾滋病”。短时间内,该流言大量蔓延。同年4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辟谣,“阴性艾滋病”只是恐艾症状,根本没有什么未知病毒。
艾滋病专家、杭州市第六医院时代强教授对此解释称,有一种心理病叫“费滋病”,该病与艾滋病的症状完全相似,但艾滋病检测却为阴性,无生命危险。这种病也叫“假性艾滋病综合征”,是由于病人强迫认为自己是感染者而导致出现一系列的类似艾滋病感染的神经官能症状,其实并非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张猛告诉记者,听别人说HIV病毒的潜伏期是10年,虽然现在的检测结果是阴性,证明自己没被感染,但内心里仍旧有一丝不安,或许此次事件的影响,将伴随自己很多年。
目前,公开资料中没有任何类似艾滋针扎的维权案例,但因为艾滋事件受责的单位是有先例的。
2011年8月,台湾大学医院发生一起重大医疗事故。院方误将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的器官移植给5名病患,导致5人均有感染艾滋病毒之虞。原本沉浸在获得器官重获新生喜悦中的移植患者和家属,全都傻了眼。5名患者不得不接受为期1个月至两个月的艾滋药物治疗。事后,台大医院向受害者和公众公开道歉。同年10月,台湾卫生主管部门公布了调查结果,5名患者检测呈阴性,并未患上艾滋病。责任单位台大医院以及负责医师则被处以30万新台币的罚款。
“维权难度很大,因为首先需要证明他(张猛)是在出租车上被扎伤。当时没能留下证据,举证存在难度,但这个案子值得代理。”张志东表示,之所以接这个官司,是因为“第一,我也打车,这事可能发生在每个打车人身上;第二,放在大环境下看,这是人人都会面临的公共交通安全问题”。
难以翻过的篇章?
刚从一场噩梦中苏醒不久的张猛,紧接着又掉入一场官司纠葛之中。
炜衡所律师团队告诉张猛,官司难度大,耗时时间会很长,“而且法庭上,需要你一次次揭开哪怕你不愿回忆的过往,还可能面对对方一些歪曲事实的陈述”,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
这场官司对于张猛来说也许是一次二度伤害。张猛在11月29日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决定打官司之前并未想到如此复杂,因为“事实很清楚,当时警察都做过好几轮的笔录”。张猛也做好了败诉的准备,赔偿也许会拿不到,但他的底线是对方一定要公开道歉。
12月10日,张猛决定重新开始。他坐上北京的特5双层公交车,沿着最熟悉的道路,走过了所有他与前女友曾到过的地方,他说想试试看能不能跟过去说再见。
次日,记者与张猛约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小饭馆里。在这个地方,他已经住了六年。一落座,张猛问:“你是以一个什么态度来见我?”面对记者疑惑的表情,他解释说,事情发生以来,他已经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有的记者形容他差点被HIV病毒逼疯了,他们经常觉得他不正常。
“我做销售12年,别人什么想法我看得出来。”张猛说这话时,低头点上了一支烟,深吸一口缓缓地吐出来。其实,在决定再次见记者之前,他已经表示了信任。此时他的质疑更像是一种条件反射。
张猛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女友因为这件事而离开。
“我对她很好,在一起后从未让她做过一点的家务,从来没有让她断过零食,连楼下商店的老板因为我老去光顾都认识我,我还替她规划好了未来的一切……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张猛让饭馆的伙计上了一些酒,历数着跟女友的往事。只言片语中,张猛流露出对这段感情的不舍。
这个1米76的强壮东北大老爷们,过去六年里几乎每天坚持爬山、跑步,体格十分健壮。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更难坚持长时间服用抗HIV病毒的阻断药物和精神上的打击。直到现在,张猛都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走出阴霾,别人是否仍把他看作“艾滋”病人,他也不确定。
采访结束时,张猛表情神秘地告知记者,法院会在下个月开庭审理他的案子。等待他的是怎样的结果,《方圆》将作进一步跟踪报道。
(应当事人要求人物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