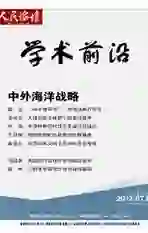明初海权扩张与朝贡体制重建
2012-12-29王日根何锋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年13期
摘要 明初,在朝贡体制重建过程中,明朝的海上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永乐帝通过纠正洪武帝在海上力量投向上的错误,使明朝海军具备了向南洋、西洋地区进行远洋投送和作战的能力,为将该地区国家纳入朝贡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同时得益于明朝海军的远洋投送与作战能力,才使明政府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控制了朝贡贸易的核心——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从而确保明政府在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
关键词 明初 海上力量投向 朝贡体制重建
洪武年间重建朝贡体制战略目标的确立与海上力量的错误投向
明朝初创之际,国势艰难。在朱元璋统治的31年时间里,虽然国家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国力也不宽裕,但这位皇帝却早早定下了重建朝贡体制的战略目标,试图通过确立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宗主国地位,来树立明朝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①但是洪武帝重建朝贡体制的行动明显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例如洪武三年九月(1370年9月),针对辽霫不来朝贡,朱元璋公然向对方发出了武力恫吓。“近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锁里、海外诸国,皆称臣入贡。……抑我师之未加,姑以为可自安耶?兹特遣人往谕,能番知天道,率众来归。官加擢用,民复旧业。朕不食言,尔其图之。”②但是这种武力威胁主要还是针对与明朝有陆地相邻关系的朝贡国家,对于那些南洋、西洋地区的海外诸国,更多的还是依靠派使臣宣谕和贸易利诱来促使其朝贡,但这种脆弱的朝贡体制很快就因明朝与爪哇的宗蕃权之争而告破裂。
洪武十三年(1380年),作为中国传统朝贡国的三佛齐遣使来华,希望朱元璋派使臣前去册封他们的新国王。朱元璋欣然应允,但没想到的是,派去册封三佛齐王印绶的明朝使臣全部被“爪哇诱而杀之。”③因为当时爪哇已控制了三佛齐,成为它的宗主国,而三佛齐传统上还是中国的朝贡国,因此明朝作为三佛齐的宗主国,向三佛齐派使臣去册封国王也是正常的。但是爪哇王觉得明朝此举威胁到了爪哇在当地的宗主权和地区霸权,故杀害了明朝册封使臣,以达到将明朝的宗主权排斥在南洋地区之外的目的。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得知了明朝使臣被杀的消息,大怒,“留其(爪哇)使月余,将加罪,已,遣还,赐敕责之。”④此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⑤洪武帝重建朝贡体制的设想大部分没有实现。
洪武时期重建朝贡体制的努力严重受阻,有两个重要原因都与海上力量有关。
一是明初海上力量建设不足。洪武初年,明朝海军虽然拥有3000~4000艘各型舰船,⑥但这些舰船主要来自于战争缴获,并且以内河舰船居多,适合远海航行的船只较少。客观上讲,洪武时期的明朝海军还处于初创期,只能担负从内水到近海区域的防御任务,海运业才刚刚恢复,适合远海航行的五桅海运船主要用来海运粮饷、保障京师物资供应,这些先天不足严重制约了明朝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基于洪武时期海上力量的现状,朱元璋为海军确立的基本建设思路就是:在沿海各冲要之地建立起一个“陆聚步兵,水具战舰”⑦的海上防御体系。后来出于防倭需要,于洪武七年春正月(1374年2月)对这一战略作了调整,成立远海巡防舰队,命靖海侯吴桢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所统在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漳、泉、潮州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⑧远洋舰队的巡逻区域最远到达琉球大洋,并与倭寇船队交火,给倭寇以沉重打击。此后每年春季,海军舰队出海巡逻,分路防倭,秋季撤回,成为一种常例。⑨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吴桢的远洋舰队主要任务是巡逻警戒,而且受制于大型远洋舰船的制造能力、人员训练水平和后勤保障等问题,这支舰队的远洋投送能力、作战能力和舰队自持力都不可能很强。客观上讲,用于远洋巡逻尚可应付,用于远洋作战则力所不能及。
洪武十三年爪哇杀害明朝使臣事件发生后,在相当长时间里改变了南洋地区的政治格局。爪哇成为南洋的地区性大国,三佛齐首先被爪哇所灭,更名为旧港,苏吉丹、碟里、日罗夏治、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腊等爪哇附近的小国被爪哇所阻,不再到中国朝贡,爪哇成为西洋、南洋诸国贸易的中心,明朝方面“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自入贡以来至今来庭。”⑩
从战略地理角度来分析洪武十三年后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朝贡国情况,我们发现,这些不再向中国朝贡的西洋、南洋地区的国家,在地理上均与中国远隔重洋,没有直接的陆地相邻关系。明朝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武装力量构成以陆军和步兵为主,这决定了对外施加军事影响力的地区只能是那些与明朝有陆地相邻关系的国家,只有这样,明朝对藩属国的军事威慑力才有用武之地,洪武皇帝对北元的征伐和对辽东霫族的武力恫吓就是明证。但是,海外诸国的地缘环境大不一样,他们与明朝远隔重洋,明朝陆军的威慑力对这些藩属国是鞭长莫及。朱元璋如果要对西洋、南洋的藩属国采取武力行动,则必须依赖明朝的海上力量。在这里,海上力量的远洋投送能力和作战能力就成为重建朝贡体制,确保南洋、西洋诸藩国臣服的关键。但至少在洪武年间,明朝的海上力量不具备这个条件。洪武时期的明朝海军不仅无法向南洋地区投送,就连跨过对马海峡,攻击近在咫尺的日本也办不到。例如,当洪武十三年所谓的胡惟庸通倭事件曝光后,朱元璋通过礼部向日本国王良怀(即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发去诏书,以表达自己的不满,诏书上写道,“今日本君臣,以沧海小国,诡诈不诚,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无乃天将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我至尊(即朱元璋)又不允,曰:……若以舳舻数千,泊彼环海,使彼东西趋战,四向弗继,故可灭矣。然于生民何罪?”洪武十四年(1381年)良怀亲自复书,表达了绝不屈服于朱元璋的强硬态度。“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朱元璋“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其实,朱元璋放弃派兵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明朝没有向远洋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在朱元璋看来,连空前强大的元朝海军都失败了,比元朝海军弱小得多的明朝海军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所以,当明朝面对爪哇阻断南洋、西洋地区的朝贡贸易时,朱元璋也无可奈何,到最后还不得不将爪哇的使臣放回国,发一封抗议信了事。南洋、西洋诸国也正是看到了明朝海上力量的不足以及爪哇的现实威胁,才会放弃到中国朝贡,从而导致朱元璋以武力为后盾重建朝贡体制的失败。
二是朱元璋在海上力量的使用上存在着严重的战略投向错误。朱元璋的海上力量建设思想基本上是一个近海防御型海军战略,同时辅之以远海巡逻制度,其目的一是防倭,二是执行海禁政策。而恰恰是将海军用于执行海禁政策,标志着明朝在海上力量的使用上存在着严重的战略投向错误。
海禁的提出最初是为了断绝大陆居民对方国珍、张士诚反叛余部的物资接济。但随着朱元璋巩固了在全国的统治后,继续借口“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而“禁沿海民私出海”,从军事角度上就解释不通了。其实,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间,平均每年发生的倭寇入侵事件只有2~3起,最多的洪武二年也不过7起,这些倭寇入侵事件在数量上远不及嘉靖年间,其破坏力也不大,甚至还比不上中国海盗对沿海居民造成的危害。所以,朱元璋以防倭作为实行海禁的理由,只能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做法。
海禁政策出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朱元璋的维稳思想。他一心想恢复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将农民重新固着到土地上,以便于控制管理。而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则会引起人员的迁徙与流动,使农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外部事物,这会从思想上打破小农安于现状的想法,更会引起对农民人身控制力的削弱。所以,朱元璋对充当小农经济破坏者的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心存恐惧,怀有敌视情绪。其次是朱元璋的报复心理,出于对沿海居民曾经大力资助过方国珍、张士诚的怀恨在心,他有意对沿海居民进行经济制裁和惩罚。最后才是防倭。事实上,从北宋晚期开始,中国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就越来越繁盛。政府通过市舶司对贸易加以管理,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维护了沿海居民的利益,官民双方在海贸问题上相得益彰。宋元时期,中国沿海也有海盗和倭寇的袭扰,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并未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朱元璋借口防御海盗和倭寇而实行海禁的理由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朱元璋以一己私念,凭借国家的行政权力来实施海禁,阻止民间发展海外贸易,应该说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不幸的是,这种基于个人好恶而产生的海禁思想却被后来的统治者视为“祖宗成法”,不可更改,使得个人意志逐渐变成国家意志,加剧了沿海居民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刺激了海盗、倭寇、私商的违禁行为。
在实施海禁的日子里,明朝的海军担负着两个基本职能:保卫海疆和稽查民间海外贸易。有趣的是,这两项职能在今天看来,其目的刚好是自相矛盾的。海军保卫海疆的行动,其根本目的应该是为本国的海上活动提供安全的外部环境,以利于海外贸易的开展。政府通过发展海外贸易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建设海军,促进海军的健康发展。但是我们看到,明朝海军却做着本末倒置的事情。按照朱元璋的逻辑,因为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所以海盗倭寇循利而来,引得海疆不宁。要使海疆安宁,就得查禁民间海外贸易,只要没人出海做生意了,倭寇、海盗就不会来侵扰了,海疆才会宁静。可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海军建设思想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很快,海盗、私商、倭寇重新活动起来,沿海居民也对禁海令置若罔闻,私自出海贸易的人数有增无减,并且海军将领也很快被腐蚀,加入到了海上走私者的行列。随之而来的是洪武皇帝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和禁海令,于是海军官兵为了自保性命,不问良莠、不管官民,对所有出海的船只都加以查禁,结果连正常的海运都无以为继。洪武二十五年秋七月己酉(1392年8月18日),两浙运司向皇帝上言说:“商人赴温州各场支盐者必经涉海洋,然著令军民不得乘船出海,故所司一概禁之,商人给盐不便。”朱元璋接到这个奏报后的尴尬表情可想而知,他斥责兵部官员说:“海滨之人,多连结岛夷为盗,故禁出海。若商人支盐,何禁耶?”随后命兵部移文谕之,要求海军巡逻人员对海运区别对待,不可一概查禁。在这场关于海禁的博弈中,正是由于朱元璋对贸易所持的错误想法和对海上力量的错误运用,才使得政府和民间都被这无谓的猫鼠游戏弄得疲惫不堪、两败俱伤。
海军是一个人数虽少,但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军种,其作战行动的成本是高昂的,但效果的显现却是长期的,这与陆上作战极不相同,这也正是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熏陶下的中国皇帝多数都不重视海军的一个原因。在明初海上力量的建设中,除了洪武皇帝个人权威所提供的支持外,训练、使用、维护、管理中央和地方舰队的费用是惊人的。由于朝贡体制未备、朝贡贸易不兴、私人海外贸易被禁,使得海军不仅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支持其发展的资金,反而还要中央和地方从农业税收中拿出大量资金来进行补贴,这自然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朱元璋的做法使明朝海上力量的建设和海军的运用明显违背了海军自身存在的宗旨——即海军是为贸易而生,而不是用来阻止贸易的。
永乐年间海上力量的远洋投送决定了朝贡体制重建的成功
到了永乐年间,明朝国势日趋强盛,完成重建朝贡体制的设想有了实现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这一时期,明朝拥有完善的海运体系,有强大的中央直属舰队和海岸警卫舰队,有专门用于防倭的远洋巡防舰队,有由卫所、水寨构成的完备海军基地,还有大批常年奔波在海上的水手和海军战斗人员。国内造船场已经能建造排水量从数千吨到上万吨不等的大型船舶,宝船、海运船、战座船、马船、快船、水船等适合远洋航行需要的各型船舶应运而生,功能上涵盖了一支远洋舰队所需的指挥、护卫、作战、后勤保障、通信联络等各方面,这一切技术条件的达成,为永乐皇帝推行向海外发展、完成重建朝贡体制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可能。雄才大略的朱棣夺取帝位后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共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从战争中夺取政权的朱棣很清楚空言恫吓与实力展示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要想避免重蹈洪武时期的覆辙,就必须大力加强明朝海军的远洋投送能力和远洋作战能力,用实实在在的军事威慑来保障朝贡体制的重建。
首先是重组远洋巡防舰队。远洋巡防舰队最初是在洪武七年春正月(1374年2月)组建的,朱元璋死后,明朝陷入长达4年的靖难内战之中,远洋巡防舰队的人员和船只也被交战双方抽来调去,损耗在各个战场上。到战争结束时,舰队已经名存实亡。朱棣即位后,要想重建朝贡体制,向海外宣示国威,必须要有一支能遂行远洋作战任务的海军舰队才行,因此重建远洋巡防舰队,为后续的海军远洋行动做准备,就成为实现重建朝贡体制这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永乐六年十二月(1408年12月),朱棣“命丰城侯李彬充总兵官,……统帅官军自淮安沙门岛缘海地方剿捕倭寇。命都指挥罗文充总兵官,指挥李敬元充副总兵官,统帅官军自苏州抵浙江等处缘海地方剿捕倭寇。”十二月庚子(1409年1月12日)又“命都指挥姜清、张真充总兵官,指挥李珪、杨衍充副总兵,往广东、福建。各统海舟五十艘,壮士五千人,缘海提备倭寇。如与丰城侯,仍听丰城侯调遣。”这样,在永乐六年十二月底的时候,朱棣完成了远洋巡防舰队的重建工作,并从编制体制上强化了对沿海各省海岸警卫舰队的控制和管理,明朝海军恢复了“远洋—近海—岸基”的三层防御体系。
其次是利用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对拒绝朝贡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打击,震慑其他国家,从而保证重建朝贡体制的顺利进行。当永乐皇帝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始向海外宣布国威,重建朝贡体制的时候,首先碰到了安南的挑战。安南权臣黎季犁在诛杀前国王后自立为王,公开与明朝武装对抗,试图摆脱藩属国的地位而独立。安南的行为严重挑战了永乐皇帝重建朝贡体制的雄心,这是他无法容忍的。在永乐皇帝的支持下,郑和这位有勇有谋、实战经验丰富的心腹内侍被选中,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远航西洋,去实现重建大明朝贡体制的梦想。而张辅则被委任为征讨安南的总兵官,率领数十万明军去征讨安南。
永乐三年六月己卯(1405年7月11日),永乐皇帝命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领27800多人出使西洋诸国。舰队自刘家港扬帆起航,经刘家河出长江口,然后“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航行。郑和下西洋的第一个任务是联络占城,配合张辅即将展开的征讨安南的军事行动。
此时占城正受到北部安南国的侵略,郑和舰队的到来给了占城国王占巴的赖极大的军事支持,这种帮助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占城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将安南军队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南边,从而迫使安南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郑和的舰队在占城一直呆到永乐四年五月(1406年5月)才走,随后七月份(1406年8月)总兵官征夷将军成国公朱能率大军讨伐安南(朱能病笃,实际上由张辅代行指挥权)。郑和在占城停留了10个多月,指挥他的人协助占城军队抵抗安南的进攻。当明朝的征讨大军即将出动时,安南不得不将侵略占城的军队从南线调往北线,以防御明军的进攻。这样,占城面临的军事威胁解除,郑和的第一个任务完成。由于还有其他使命,不能在占城久留,所以在稳定了该国的安全局势后,郑和舰队就顺风南下,经过20天的航行,于永乐四年六月(1406年6月)到达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在爪哇,明朝官兵遭到爪哇西王的伏击,170人被杀。郑和得知人员遇袭的消息后,立即组织大部队前去救援,并准备讨伐西王。永乐皇帝获悉此事后,“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六年再遣郑和使其国。西王献黄金万两,礼官以输数不足,请下其使于狱。帝曰:‘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悉捐之。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在明朝远洋海军的威慑下,爪哇自此臣服,从而丧失了对南洋、西洋地区的贸易垄断地位。之后郑和率舰队到达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向其酋长陈祖义宣谕,要其向明朝朝贡,但遭到海盗出身的陈祖义的武装偷袭。不过陈的武装反抗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陈祖义集团被消灭,明朝在旧港故地设立旧港宣慰使司,成为明朝在南洋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经过爪哇和旧港事件,明朝海军打破了爪哇和旧港对南洋地区海上贸易和海上商路的垄断控制,为西洋和南洋诸国直接与明朝开展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被纳入到明朝的朝贡体制当中,成为明朝的藩属国。
永乐六年九月癸亥(1408年10月7日),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与其国王亚烈苦奈儿发生了武装冲突。明朝指责亚烈苦奈儿贪财,欲劫夺郑和舰队的金银财宝。而锡兰则指责郑和欲夺取该国圣物“佛牙”和立碑,以强迫锡兰向明朝臣服朝贡。不管双方所持的理由如何,这场武装冲突以郑和的胜利而告结束,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被明军俘虏,锡兰士兵向明军投降。永乐九年夏六月乙巳(1411年7月6日),“郑和还自西洋”,将擒获的锡兰国国王和官员“献俘于朝”,永乐皇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即安南)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1412年12月18日),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在苏门答剌遭到了与苏门答剌新国王敌对的苏干刺军队的袭击。郑和指挥明军还击,大败苏干刺并将其活捉,永乐十三年七月(1415年8月)还朝后,永乐皇帝下令处死了苏干刺。苏门答剌事件后,郑和舰队到达暹罗国(今泰国)。当时暹罗国正致力于地区扩张,试图吞并满剌加(即马六甲)。郑和到来后积极干预此事,谴责暹罗,支持满剌加独立。在中国的军事压力下,暹罗承诺放弃吞并满剌加的企图。之后到达锡兰国,解决锡兰国王的废立问题。随后舰队北上印度东海岸,抵达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堡后返国。
在前三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以杰出的外交、军事才能有效阻止了在安南、爪哇、旧港、锡兰、苏门答剌、暹罗、马六甲等地出现的武装对抗明朝和妄图称霸地区的事件,还建立了海外行政机构和军事据点,保证了明朝重新建立的朝贡体制不被撼动,树立了明朝作为宗主国的绝对权威。这些事件也使南洋、西洋诸国切身感受到了明朝海军的威力,不敢再与明朝对抗。此后郑和再出使西洋就变得一帆风顺了,绝大多数西洋国家向明朝称臣纳贡,成为明朝朝贡体制当中的一员,中国在整个西洋地区获得了空前的声望,而这些威望的获得除了源于中国人的和平交往原则外,更离不开明朝海军所具备的强大远洋投送能力和战斗力,才使洪武、永乐两朝确立的重建朝贡体制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明朝朝贡体制的艰难重建过程再次证明了国际交往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平衡依赖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
远洋海军使明朝控制了朝贡贸易的核心
朝贡体制重建以后,明朝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遂成为永宣时期主要的海外贸易方式。通过朝贡贸易,明政府聚敛了巨额财富。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这些财富在皇帝内库和政府国库之间是按何种比例分配的,但永乐皇帝无疑从中大获其利,使他有兴趣继续推动远航事业的发展。那么,明朝是如何通过朝贡贸易来大获其利的呢?其奥妙就在于明政府在依靠远洋海军树立在南洋和西洋地区霸权的时候,不经意间也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贸易定价权。
首先是货币发行权。控制货币发行权的实质就是明朝要使本国的纸币成为西洋诸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时的一种结算单位。明初,政府继续使用纸币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但是汲取元代钞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发行的纸币有充足的贵金属做保证金,以保证纸币不贬值。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就曾经为表彰朱棣征讨乃儿不花的战功而赏赐给朱棣钞100万锭,可见明朝初期,国内的纸币供应量是相当巨大的。但是,纸币仅仅在国内流通还不足以说明朝的影响力超过前代,这也与洪武、永乐皇帝要实现海外诸国万邦来朝的志向不符。因此,朝贡贸易体制能否建立,朝贡贸易能否推行下去,重要的就是看朝贡国是否使用明朝的纸币作为贸易结算单位。就像宋代那样,中国的铜钱成为整个亚太地区公认的流通货币和结算单位。但是明朝的纸币与宋代的铜钱有个本质区别,那就是宋代的铜钱本身有价值,因此被国内外大量储藏、走私、熔铸和挪作他用,导致了严重的钱荒问题,极大消耗了宋朝的货币财富;而明朝的纸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只是一种货币符号或者信用凭证,明朝纸币的信用好不好,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因此,明政府不论是把纸币赠与外国,还是与海外诸国使用纸币进行贸易结算,实际上都是拿明朝的国家信用做交换媒介,与存放在国内的由贵金属充当的保证金无关,纸币的交易与流通并不会带走明朝国内的货币财富。
在纸币的使用上,西洋诸国面临着三种情况:一是明朝经济军事力量强大,纸币信用高时,向明朝臣服纳贡,使用明朝纸币进行贸易;二是明朝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纸币开始贬值,作为藩属国,被迫使用明朝纸币进行贸易;三是明朝经济军事力量严重削弱,纸币贬值,作为藩属国拒绝使用明朝纸币进行贸易,而明朝再也没有能力使用军事力量强迫藩属国接受纸币进行贸易。可见,明朝要长时间实现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让南洋、西洋地区的藩属国接受纸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第二、三种情况出现时,为了保证纸币在朝贡贸易中的结算地位不动摇,明朝政府就必须依靠远洋海军的军事力量来维持。
洪武、永乐时期中国国力强大,纸币的信用很好,几乎可以与等重量的白银相兑换,因此海外诸国也乐于接受纸币。例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中山来贡,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为门者所获,当入官。诏还之,仍赐以钞。”这件事说明当时明朝与朝贡国进行交易时是以纸币为结算单位的,而且也正因为当时明朝纸币的信用好,所以交易者愿意接受纸币。此外,从明朝对外国的赏赐中也可看到当时纸币的影响力在向国外逐渐扩大。明朝在回赠朝贡国的礼物中,除了赏赐个别国家少量的金银、铜钱外,大多数时候给的都是纸币。如永乐永乐四年(1406年)八月,冯嘉施兰酋长“嘉马银等来朝,贡方物,赐钞币有差。”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5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明朝朝贡,回国之际,明成祖赐给其国王的礼物中就含有“钞四十万贯”。1431年永乐皇帝给郑和钞10万贯以便在海外分发。明朝的纸币就这样随着对朝贡国的赏赐和郑和的远航,不断向海外扩散,从而导致使用明朝纸币作为贸易结算单位的地区和范围不断扩大,明朝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由于明朝的纸币本身并不是金属货币,因此,赏赐大量纸币并不会减少国家货币财富的持有量。同时伴随着郑和舰队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这些散发出去的纸币又通过朝贡贸易的渠道开始回流,从而使得藩属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不断加强了与宗主国的联系。
至于说郑和下西洋造成了国力耗费巨大,导致国家财政空虚,则有违事实。造成官员们抨击远洋活动耗费国家财力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内库与国库在朝贡贸易收益上的不合理分配比例。皇帝从朝贡贸易中获利颇丰,且收益大部分进了自己的内藏库,但政府却要从国库中掏钱出来为皇帝的朝贡赏赐买单,所以,就可能出现政府亏钱而皇帝赚钱的情况。皇帝赚了钱自然对远洋活动大力支持,而政府亏了钱当然对远洋活动大加批评。
在永乐前期,夏原吉掌管财政,明政府尽管建造了包括宝船在内的1700多艘远洋船只、组织了大规模的海运、赐予了王公和功臣大量重礼、支付了安南战争的费用,但仍未出现财政赤字。造成国家财政空虚的真正原因是迁都北京后大兴宫殿、远征漠北、宫廷的奢侈挥霍、对皇室成员的过度赏赐,以及官员的贪污腐败。因为,明初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以农业税为主,当大量的农业税收投入到上述行为中时,就会造成对财政收入的纯消耗,却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收益。长时间的收支不平必然导致财政空虚,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使得本已拮据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以造船业为例,政府官员从中大肆敛财,普通军民则必须忍受沉重的剥削和压榨。吏部尚书蹇义在向皇帝呈送的奏折中就说道:“在京各卫成造海船等件,所有物料虽是官给,然有匠作原计数少,或该科放支,斤两不足,率令军民赔补。头会箕敛,侵损非细。”
当大兴土木、远征漠北、挥霍无度、巨额赏赐和官员贪腐在纯消耗着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时,只有郑和建立的朝贡贸易体制帮助明政府赚到了钱,但这些钱多数进了皇帝的口袋,可能只有少数进入了国库。正是通过进入国库的那部分朝贡贸易的收益,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业税收的纯消耗,使得永乐年间明政府的财政收支大体维持平衡。所以,当永宣之后,中国航海事业停顿下来,朝贡贸易的收益没有了,而造成农业税收纯消耗的那些行为还继续存在时,明政府的财政就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境地了。
其次是贸易定价权。随着郑和下西洋建立起来了朝贡体制,朝贡贸易也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明政府从朝贡贸易中聚敛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并不完全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获取的,而是通过取得贸易定价权,进而通过垄断价格来获利的。可以说,贸易定价权的得与失直接关系着朝贡贸易是赚钱还是亏本,进而关系到朝贡贸易的存亡。而在决定贸易定价权的过程中,明朝远洋海军的军事威慑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贸易定价权在朝贡贸易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通过郑和舰队的远航,西洋诸国见识到了明朝远洋海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于是称臣纳贡,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从而接受郑和的纸币馈赠,同意使用纸币作为朝贡贸易的结算单位,并在朝贡贸易中按照明朝政府制定的不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易。当西洋诸国的朝贡使团来到中国后,明政府除了象征性地接受少量贡物外,一般都会从使团手中购买许多贡品和商品,主要以朝廷和皇室需要的高附加值商品和奢侈品为主,例如黄金、白银、铜、马匹、苏木、药材等。在购买时,明政府以朝贡体制中规定的低价购买原则购买这些高附加值商品。例如,明政府向外国使者购买黄金,一两黄金付给50贯纸币,一两白银付给15贯,而当时官方的兑换率是一两黄金值400贯,一两白银值80贯。又例如苏木,1433年之前的市场价是500克价值5~50贯钱,而明政府购买500克苏木仅支付半贯钱。这就是垄断低价。通过这种方式,明朝至少从朝鲜得到1000两的黄金和1万两的白银,从安南取得了1000两黄金和2万两的白银。 当使团离开时,明政府回赠部分礼物,使团也会购买大批中国商品回国,这些商品主要是技术含量高的丝织品、陶瓷、茶叶、铁器等工业品,这也是朝贡国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朝贡使团在购买这些商品时必须按明朝官方给出的价格购买,这个价格一般都会比国内市场高,于是形成垄断高价。即便在卖给朝贡使团商品时以市场价出售,但由于明政府在购买商品时控制着垄断低价,因此仍然从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所以,对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的控制,尤其是对垄断低价的控制,才是贸易定价权的关键。
通过皇帝回赐和郑和分发出去的大量纸币,最终为明朝换回来的是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财富,而明朝所付出的只是一堆印有花花绿绿图案的纸。伴随郑和舰队七下西洋的征程,明朝运用远洋海军的威慑作用,牢牢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使得明朝得以依靠不等价交换原则从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从而确保朝贡体制的有效运行。
永宣之后,虽然中国的远航事业停顿下来了,但朝贡贸易体制所确立的不等价交换原则因其制度惯性还存在了一段较长时间,明朝皇帝在这种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中还是能获利,只是获利不及以前丰厚罢了。而明政府则还要继续为皇帝的朝贡赏赐买单,却毫无收益可言,因此,明朝的皇帝与政府对朝贡贸易的兴趣都在降低。
远洋海军的消失导致朝贡体制在西洋地区的没落
虽然明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从朝贡贸易中获取了大量好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明政府对于这两权的认识和运用始终处于一种不自觉和无意识的状态下,并没有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朝贡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极端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远洋海军与朝贡贸易间反映出来的军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因此才有后来的弃远洋海军和贸易定价权如敝屣的行为。
郑和舰队的远洋航行为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和好处,而绝不是像一些官员所说的那样,远航耗费了巨大国力,导致财政空虚,民生艰难。洪熙元年二月(1425年2月)郑和舰队回国,新即位的洪熙皇帝朱高炽(即明仁宗)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以及他本人对明朝海洋权益的无知,于是命“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不许他再下西洋。鉴于永乐皇帝开创的航海事业和朝贡体制有夭折的危险,郑和向新皇帝上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但是明仁宗没有听取郑和的建议。明宣宗即位后,又听从朝中腐儒的清议,将海军和陆军从安南撤出,安南的独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威望一落千丈,朝贡体制甚至因此出现崩溃的危险。
自明朝海军第六次下西洋结束5年之久后,西洋诸国见中国海军长期不至,遂产生轻慢之情,向明朝的朝贡也不再积极。于是在宣德五年六月(1430年6月),宣德皇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为由,派郑和、王景弘率领舰队第七次远航西洋,到1433年郑和舰队才启程回国。当返航到古里时,63岁的郑和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7月),王景弘指挥着远洋舰队回到中国。从此以后,明朝的海上远航活动结束,郑和的航海日志被销毁,宝船被拆解,人员被遣散。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也逐渐失去了能够制造大型远洋舰船所需的技术、熟练工人、原材料供应渠道等,使得明政府在以后即便有心重建远洋舰队,但也因失去了装备制造能力而不得不放弃。失去了技术支持就不可能再建造出远洋舰船,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向海外投送军事力量。随着海军远洋投送能力的丧失,建立在不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朝贡贸易格局必将被西洋诸国打破,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的丧失也是迟早的事情。明英宗时期,中国更是经历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惨败,经济和军事实力遭到重创,明政府再也不能威慑西洋诸国了。
随着明朝国力的削弱和远洋海军的消失,国家信用也大不如前。明朝纸币此时已经贬值到不及票面价值的10%,即便是中国人也不愿接受纸币,因此外国人完全拒绝纸币,要求以丝、瓷和大量铜钱作为赏赐物品和报酬。对于外国使者带来的商品,再也不能强迫他们按明政府规定的低价出售,而必须按市场价格偿付。到了1453年,当500克苏木的市场价维持在5~8分白银时,明廷固定付给7分白银,此时,朝贡贸易对于明朝的皇帝和政府而言都已经无利可图,而且在事实上赏赐贡品还变成一种纯粹消耗政府财源的负担,明朝的皇帝和政府都失去了对朝贡贸易的兴趣。历经洪武、永乐两朝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此时已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但这恰好为民间海上贸易的兴起让出了广阔的空间。
注释
《明太祖实录》(卷254),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671、3672、3672页。
《明太祖实录》(卷56),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100页。
《明史》(卷324),列传212,《外国五,爪哇》,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02页。
何锋:《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2007年,第9页。
《明史》(卷126),《汤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54页。
《明太祖实录》(卷87),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546页。
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第203页。
《明太祖实录》(卷138),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175页。
《明史》(卷322),列传第210,《外国三·日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43~8344页。
《明史》,志第63,兵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3页。
高扬文、陶琦主编:《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页。
《明太祖实录》(卷219),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218页。
《明太宗实录》(卷86),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147页。
《明史》(卷304),列传第19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6~7767页。
《明太宗实录》(卷58),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852页。
《明史》(卷324),列传212,《外国五,爪哇》,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03页。
《明史》(卷6),本纪第6,《成祖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89、90页。
《明史》(卷304),列传第19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7~7768页。
时平:《论郑和海权的性质》,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111~112页。
《明史》 (卷323),列传第21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2、 8380页。
《明史》(卷325),列传第213,《外国六·满剌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17页。
[美]罗荣邦:《明初海军的衰弱》,原文载于ORIENS EX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