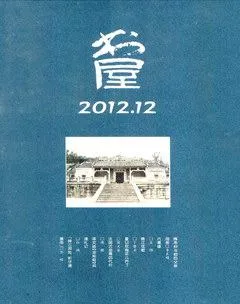夏日玫瑰花儿开了
2012-12-29陈文芬
我的童年在高雄前镇西甲西巷度过。
西甲西巷是条狭巷,两排二楼房屋对视而立。天候炎热,家家门户敞开。你的客厅面对我的客厅,彼此相看,入夜睡前才关门。
我家对门有一寡居婆婆,她不识字卖点香烟杂货。婆婆隔壁我的玩伴黄宝瑶妈妈是裁缝,她爸爸不知做什么工作,总之是在外遭遇了什么,断了脚拄拐杖,支了条板凳纳门口凉听广播。楼上林秋玲与我同年她爸爸开长途货车,很少回家。西甲西巷以及附近邻居大半是爱河尽头边上十三号码头的工人。傍晚男人们回家,多半拎了鱼,晚餐远近闻得到生姜煮鱼汤的气味。
西甲西巷背靠一米场空地,定时有卡车开来,载来满车的毛豆。巷弄的妇女老小全端着铝制的盆筒来排队,等着工人将盆子装满毛豆,剥一斤毛豆的工钱是五毛。妈妈剥了三年毛豆,还有一年的时间是盖纸钱金印,金印有锡箔粉,有股特别的粉香气。我爸爸住凤山部队,隔周放假回家,我跟他不熟。每月军用小货车到巷口来发军眷口粮,米、面粉还有两包陆军标帜骆驼的硬饼干,军车来时我跟姊姊去巷口等派饼干。只有拿到饼干时,我才稍微觉得当军人的小孩有点不同。
我迷上邻居的电视,向妈妈讨着要电视,我妈跟大舅借钱买。安了四只木头脚的电视机,我只看了几天,就能开口说国语,非常流利。米场对面的药房老板娘很疼爱我:“相招来看小芬说国语。”我会唱的第一首歌是陈兰丽的《葡萄成熟时》,她旋转兰花指还瞇紧眼睛笑,迷死我了。
我还会唱凤飞飞《可爱的玫瑰花》、《五月的花》。如今想来,我还不曾听过小孩该听的儿歌,哪怕是在那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儿歌《只要我长大》:“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家庭不要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我的童年就直接进入凤飞飞的歌艺世界,有种奇特的感觉,就像跳水选手,没有任何暖身预备动作,曲线笔直跳跃坠入水底,那对很多同时代台湾人的成长经验,也许不是很寻常。
妇女在家忙干活,小孩们约好了出去打工。我们当时兴奋无比,什么小工都做,起先是捡瓶盖、废铁圈,这只能跟着别的大孩子做。黄宝瑶跟我到隔壁巷一婆婆家里折卫生纸,一包纸每抽两张对折,再抽两张对折,搭成十字叠成一落,婆婆(我们叫阿桑)家里是个小工房,其他一些少女小姊姊也折纸盒,一边听唱机里的凤飞飞的歌。外面日头炎炎,婆婆拿把扇搧风,困着时,会被姊姊们一阵齐唱狂吼。“不知花儿落在谁家啊啊啊”惊醒一下,又沉沉地打盹。迭完一包或两包有五毛一块,哼哼唱唱“多美丽的玫瑰花,啊,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牵手去米场前小摊,买一支竹签串的黑轮丸子,吃饱了。那时候的凤飞飞扎两条辫子、戴小扁帽,像车掌小姐,人很帅气,唱歌甜甜的美丝丝的。不时又可以转腔吼将起来,那种豪情,一直使我想到在大马路上看车掌小姐,鸣哨子叫司机将公交车往后退、退、退,然后戴着车票本子,忽然跳上汽车,把一车子的人开往天涯。
弟弟出生不久,为了爸爸能回家照顾婴儿也为了我提早入学,搬到五甲一年。我刚入学,握笔僵硬。“我不要上学,我要当歌星”,我妈劝我歌星也要认字背歌词。我们住在二楼楼房,从窗外望去对面的三个孩子,或躺或坐在玩着积木还有撒了一地的拼图,那一幕我看呆了。我从没见过儿童在家里是那么轻松游玩、读书。我们在家里就是为了工作,出门也为了工作,这应该是世界的一切,虽然我也认为工作是非常有趣好玩,一点也不觉得苦。
一年后,我们迁回西甲西巷,林秋玲一家早搬走。楼上女工姊姊好漂亮,她的脸有点圆,人很精神大方的样子,见人总是未曾言语已经笑开来了;她有一头长发,就是这乌云一般地长发吸引了我,我从没见过成年女人的头发这么好看。我喜欢跟大姊姊交际,她回家来骑着百吉小机车,我们姊妹都会抢着上楼去跟她讲几句话,她也不嫌我们烦。假日时候她的男朋友来接她出去玩,晨起时她已经在楼上放了好久的凤飞飞的歌。我感觉整个高雄大街小巷都跟我家楼上的姊姊似乎都在唱《微笑》,“一个爱的微笑,忘不了,忘不了。多甜蜜,多美好,在梦里,常围绕”。我那时候害了一种儿童的风湿关节炎,关节疼痛,妈妈没空理我时,我一早起来就呆坐厨房哭得很伤心。女工姊姊拿了一台录音机给我妈:“等小芬一哭,就录音给她听。”这个办法对付我,挺有效用,听见自己的哭声我迷惑好奇又喜悦,渐渐忘了身上的疼痛。
我不知道姊姊的名字,却记得大家背地里叫她“蓓蒂”,是一些邻居坏男孩取的。姊姊在工厂做事,发生了意外,她的头发被转动当中的工厂机器不知怎地拖夹进去了,连头皮也掀掉大半,庆幸没有伤及胪脑。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她回到家来,戴着帽子遮掩。长发魔术一般消失了,光溜溜的脑壳上还有一条黑蚯蚓长的伤疤。那时候有部电影《光头蓓蒂》,于是那些半大不小的男孩就叫她蓓蒂、蓓蒂……
蓓蒂很少下楼,她待在家里的时间,多半在屋子里听凤飞飞唱歌。一天下了大雷雨,我想找黄宝瑶来家里折了纸船以后,到楼上丢纸船下来,看纸船在大雨滴狂舞跳跃;可是我终于没敢上楼。我一直听着歌声:“我默默在祈祷,希望再见那微笑,他不知道。一个爱的微笑,你来了,你来了,多甜蜜,多美好,在身边常围绕。”
蓓蒂姊姊的男友没有再来找她,她的头发始终没长好。大热天,她也戴着花布当发戴帽,我偶然看过她在家里,半边头发黑髶髶的,另半边还荒芜着。不久她搬走了。我们也举家迁到台北永和,离开我美好童年的住所。
而凤飞飞的歌声始终一路相伴。小学五年级作文课级任老师出题写作文:“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老师点名叫我起来念作文,我写的起头:“一道彩虹,挂在那天空,如痴如梦,照耀天空。”读到这里,老师要我停下来。我以为她要夸奖表扬我,没想到她说这是她见过最糟糕的作文,一个小孩不应该看没有意义的综艺节目。我的心灵没有受到甚么伤害,这只不过是高雄小孩比较直率不懂得台北儿童与老师之间那套江湖游戏而已。
毕业那年暑假,妹妹跟我独自回高雄。住在三民路舅舅的川菜馆跟餐馆的女工睡顶楼。我们又回到儿时小工生活,剪干辣椒、晒锅巴,在阳台唱歌。有一天我央求女工美兰姊姊早晨骑车带我去西子湾看日出,五点钟出发,海滩上我们唱“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们不烦恼。你拼命地追,我拼命地跑,跑跑追追情儿难了”。踏过微风卷浪的西子湾,吼唱着凤飞飞的《夏日玫瑰花儿开了》:“我要我要,天不荒,地不老。我要我要,爱的花开得好。”终于,终于呼吸了高雄舒爽、自由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