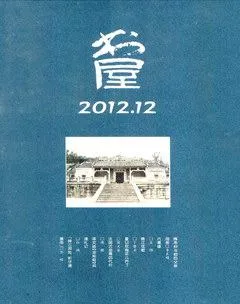马衡佚文与广西石刻展览会
2012-12-29张南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十九年,抗战期间,亲自部署、监运故宫国宝迁移西南,一路颠簸,备尝艰辛,丰功伟绩,载于史册。
近日翻检旧藏,于箧中检出一册《广西石刻展览特刊》(下文简称《特刊》),广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印,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出版。书中载有马衡《为广西石刻展览会进一言》一文,颇觉难得,旋即购来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之线装巨册《马衡诗抄·佚文卷》,查照对比,并无此文,且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中亦无此文,遂断定为佚文。文章不长,兹录于下:
为广西石刻展览会进一言
马 衡
往读叶昌炽《卧游访碑记》有云: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其次即五溪矣。良以南荒僻壤,为古名臣迁谪之所,而桂林山水甲于天下,居其地者,辄籍以游目骋怀,或托诸吟咏,以遣穷愁;或选胜留题,以志游跡。后之人低回景仰,地以人传,著之志乘,辉映山川。清嘉庆间谢启昆巡抚广西,继修通志,命胡虔遍征全省金石文字,仿《隶释》之例,录其全文,成《金石略》十四卷。刻以单行,于是广西金石始有专书。顾自晋至元,祗得四百八十余种。而桂林诸岩洞竟居十之八九,其他各县,殆多未备。今主席黄旭初先生主桂政十余年,思欲继斯而有作,历年蒐集,得千数百种,视谢之所收,殆已倍蓰。惜倭寇侵桂,向所著录,间有毁于兵燹者。顷承惠寄墨本四种,多为劫前所傳拓,其中如范成大鹿鸣燕诗刻,已付劫灰。良可慨也!夫金石之寿,有时赖楮墨以延之。是则此书之成,更不容缓。余护持文物,避居黔蜀者九年,以典守有责,终未能一揽桂林山水之胜,每以为憾!他日手此一编,以当卧游,岂不快哉。
文章三百余字,用文言写成,从三个方面说明桂林石刻的价值和举办展览、编撰《广西金石志》的意义。一,桂林为“唐宋题名之渊薮”,乃是因地处南荒,向为古名臣迁谪之所,这些仕途失意的才子触景生情,感慨身世,放浪形骸,寄托山水,多有题咏。二、清谢启昆撰《金石略》,为桂省金石第一书,然多不完备。三、今黄旭初先生欲效前贤,编撰《金石志》以补前人不逮,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最后期望“他日手此一编,以当卧游,岂不快哉”。文章一气呵成,文辞通达,寓情于理,酣畅淋漓。
我们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不仅风光旖旎,山水堪绝,其实桂林石刻也誉满天下。“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桂林石刻是广西石刻最集中地,它分布在市内各山岩名胜石壁之上,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千多通,这些题刻上起南朝,下至民国,延绵一千多年,其中以宋、清两代最多,形式多样,风格迥异,极具历史文献价值,同时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和珍贵的文化遗产。
那么,民国年间举办的广西石刻展览是怎么一回事?马衡先生又为何要作此短文呢?
严格地说,广西石刻展览应为广西石刻拓片展览。《特刊》编辑是时任广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文物专员的林半觉(1907—1983)先生,他在书末附有《广西石刻展览始末》一文,述之较详。文章较长,简述如下,不敢掠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桂系黄旭初(1892—1975)主政广西,“主席黄公,于政务纷繁之余,尤注重于文物之护持,民国二十九年命半觉收讨全省石刻拓本,筹编广西石刻志,冀存粤西一部史跡”。经过数年辛苦访求,收集到石刻拓片一千余种、三千余帧。“原订三十一年春,将所获墨本举行展览,以供学术研究,旋因不时空袭,以及种种关系,终至延误未果”。1944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桂境沦陷,全部拓本转移到乡下保存,幸无遗失。然历代石刻毁于战争者甚多,仅桂林一地就以百数计,如马衡在文中提到的范成大鹿鸣燕诗刻已在战乱中损毁,不可再睹,让人扼腕,故战前幸存的石刻拓本就更显珍贵,有的已成稀世珍宝。
抗战胜利后,全部拓片运回文化城桂林,又经过一年的筹备,从一千八百余种、三千多帧拓本中,遴选出三百七十一帧,装裱展览。这迟来的石刻拓本展览终于在1946年9月9日到12日,于桂林皇城内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展览厅举行。石刻展开广西历史文献资料展览的先河,一时成为广西文化界之盛事。四天内来参观的人数多达二万四千余人,其中教育文化界(含学生、公务员)占百分之六十,真可谓盛况空前。因反响强烈,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上半年,林半觉又携带拓片到广西柳州、南宁、梧州等地巡回展览,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各地军政及文教界头面人物带头观展,民众也趋之若鹜。
开展前三月,筹备组一面整理拓片,列目编号,一面向于右任、胡适、朱家骅等政界人物,马衡、傅斯年、徐悲鸿、简又文等专家学者发函征文。
毕生从事金石学研究的马衡,向来对桂林石刻非常重视,在其讲义《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即提到“唐时题名之风,较北朝为盛,宋元时尤多。今南北诸省,山巅水涯,随处皆是,尤以桂林诸山为最”。在《校碑札记》中,校正广西龙城的柳宗元刻石,“《校碑随笔》云:元和二年。衡(即马衡)按碑作元和十二年”。即可见马衡对桂林石刻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征文函以黄旭初的名义发出,文中有“夙仰先生博学好古,清望仝钦,敬恳赐撰鸿文,以光篇幅,大稿希于八月底惠下,不胜盼祷之至,即颂著安!”
抗战胜利后,马衡即着手督运因避免战火迁运西南的故宫文物回迁南京,这又是一番浩大工程,直到1946年6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北平,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千头万绪,日夜辛劳,加之年逾花甲,体力不济,但仍拨冗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桂林举办石刻展览题词作文。其深厚的学养以及其爱护文物,弘扬祖国文化之情可见一般:
旭初主席勋鉴:
奉读翰教,欣譒广西石刻搨本展览会,将于下月举行,缅怀我公爱护文物,发扬文化之热忱,无任钦仰!兹奉上题词及字条各一,敬希赐教,承惠赠搨片四份,珍逾璆琳,拜领嘉貺,至深感谢!肃覆,並颂勋祺。
弟马衡拜启,卅五年八月廿一日
从回信可看出,除题词(即为广西石刻展览会进一言)外,还赠予展览会字条一幅。这是根据石刻拓本录写的范成大桂林鹿鸣燕诗刻并作有题识:
维南吾国最多儒,聳观招招赴陇书。
竹实秋风辞穴凤,桃花春浪脫渊鱼。
月宫移种新栽桂,江水朝宗旧凿渠。
况有龙头坊井在,明年应表第三闾。
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太守范成大赋诗以劝驾云。
右范石湖诗,刻在桂林伏波岩,前年倭寇侵桂,此石已毁,闻广西石刻展览会,犹有劫前拓本,盍谋重勒以存胜跡,亦抗战历史中一段故实也。
卅五年八月鄞马衡并识。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南宋著名诗人,主桂期间,共创作诗歌五十五首,这些诗赋予桂林山水以文化内涵,提升了桂林山水的品格。
范成大鹿鸣燕诗刻是桂林最珍贵的摩崖石刻之一,今仿刻在伏波山还珠洞内,石刻高一百二十二厘米、宽九十厘米。“鹿鸣”为《诗经·小雅》的篇名,是宴群臣嘉宾所用的乐歌。鹿鸣燕又称“鹿鸣宴”,为乡试后官府招待由州县选出来应试科举的士子所设的宴会。范成大的这首诗,为勉励桂林学子而作。诗中借桂林历代才子夺魁和本地朝宗渠修浚之事,来激励本地读书人发愤进取。其中的“月宫移种新栽桂,江水朝宗旧凿渠”二句,是范成大为桂林做的两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一件是在桂林种植桂树,从此以后,桂林桂树成林,满城飘香;另一件是修浚城北朝宗渠,使渠水绕城环流,水脉畅通。清人陆增祥曾这样评价《鹿鸣燕诗》:“是石湖非仅风雅好事以诗雄于世也,即此一诗,亦具见培植人才之意也。”马衡录此诗以赠,亦有表彰主事者造福乡梓,弘扬中华学术之旨意。
马衡不仅是金石学家,也是声名远播的书法家。其作品具有商、周金文余韵,书法古雅,自然天成,将笔墨和篆刻相结合,深得碑刻之法度,形成了个人书法之独特风格。马衡能书,但不多作,故而其书法作品相当稀少。遗憾的是因书幅较大,又受条件限制,无法制作锌版,不然在《特刊》上我们就可一睹大师的书法风采了。
据资料记载,1947年,林半觉编有《广西石刻志》。我多方寻觅未果,最后在桂林市图书馆查询到,这只是林半觉先生的手稿,严格地说应称作《广西石刻志稿》,一函九册,并未正式出版。马衡不仅因“典守有责,终未能一揽桂林山水之胜,每以为憾!”就连“他日手此一编,以当卧游,岂不快哉”的期盼也最终没能实现。八年后,在一些人的指责和怀疑声中,七十四岁的马衡撒手人寰,临终遗言将自己所有私藏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
时间过去了六十多年,在中国文物考古史和文物文献展览史上,广西石刻展览都可谓留下了重重一笔。当年参与展览的大师、学者们均已远去,但他们对祖国文物、祖国文化的热爱之情却永远留在天地之间,虽不轰轰烈烈,却余韵深长,让人感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