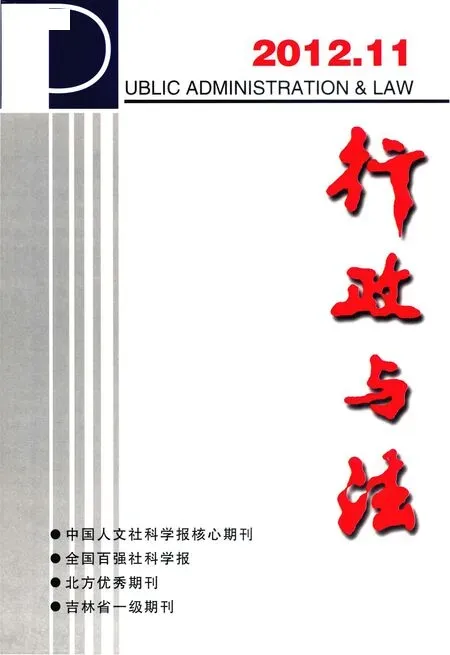农村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机制研究
——从过程与角色相结合角度的分析
2012-12-23祝天智
□ 祝天智
(复旦大学,上海 220008)
农村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机制研究
——从过程与角色相结合角度的分析
□ 祝天智
(复旦大学,上海 220008)
从过程的角度看,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酝酿与动员、爆发与高潮、回落与恢复三个阶段;从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看,所有成员可以分为组织领导者、核心骨干成员和外围普通参与者。本文以过程为纵轴,以角色为横轴,分析了在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中不同的角色在不同阶段的心理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加强社会心理调适的角度探讨了治理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应采取的对策。
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过程;角色;心理机制
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多因补偿过低、补偿款被挪用、安置不到位、征地程序不合法、面积丈量争议或用地单位强行施工等原因而起。近年来,此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乡村稳定和困扰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难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在36%的被调查村庄中发生过与征地相关的暴力事件”。[1](p25)学界对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和法律根源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其心理根源和心理机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制度及法律层面的原因相比,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原因更加隐秘而复杂:不仅在群体性事件中因角色的不同而有差异,而且同一角色在事件的不同阶段其心理也有所变化。本文尝试从角色细分和动态发展相结合的视角,剖析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人员的复杂心理,深化对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以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从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分析,每起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基本都会经历酝酿与动员、发展与高潮、回落与恢复等三个阶段。同时,根据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角色的不同,每起事件的参与者又可以分为三类:组织领导者,即“把个人怨忿塑造成群体诉求”、“招募积极分子”和“筹划集体行动”[2](p128-129)的人;核心骨干,即主动参与并起中坚作用者;外围普通参与者,即除上述两部分人之外,只是被动员或随大流而参与的人。本文的分析将以过程为纵轴,以角色为横轴,沿纵横两个方向展开,揭示各个阶段不同角色的心理特征及其相互作用。
一、酝酿与动员阶段
在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爆发前,一般都会有一定时间的酝酿与动员过程。在此阶段,群体性事件的形态一般是在经过合法渠道无法争取到预期的利益后,组织领导者被迫进行联络并发动核心骨干,阐述问题的严重性,说明发动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并制定计划。
(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心理
最先将征地矛盾问题化的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促使组织者和领导者挺身而出的心理动因主要有:
一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使。多数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由村干部、老革命、老党员、退伍军人、退休干部、各种经济和社会能人等来担当的。一方面,这种特殊的身份能够使其在村内有较大或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这种身份也是一种政治资本,使得他们在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有不同于普通农民的优势。虽然征地一般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甚至与他们的利益不一定直接相关,但由于这部分人大多具有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敢于挺身而出的担当意识,因此,当征地损害到村民利益,严重挑战这些人的公平正义观念时,虽然可能并不关乎他们的切实利益,而且要冒巨大的风险,但他们仍会放弃利己的打算,充任领导者和发起人的角色。
二是生存伦理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强烈危机意识的驱使。这一类类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因为征地导致生活困窘,或主要依靠土地生活,征地可能给其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虽不至于像斯科特所描述的,“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3](p1)但对于那些长期从事农耕、年龄较大而且不具有非农就业技能的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和安身立命的依靠,而且还是未来生活的保障和生命最终的归属。由于剧烈的生活变故和强烈的心理落差,或者由于对未来的担忧,驱使他们甘冒风险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发起人。
三是“不闹不解决”和“闹了就解决”心理的驱使。当前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由于对社会矛盾反应的体制性迟钝,总是等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才启动应对措施,即不闹就不解决;另一方面,在“维稳”高压线的作用下,基层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往往采取 “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即“闹了就解决”。甚至有些无理取闹者也能通过闹事获取利益。这种治理逻辑告诉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闹”是无奈但明智的维权办法。
(二)核心和骨干分子的心理
一是基于对征地事件的强烈不满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心理。征地虽不至于影响骨干分子的生存伦理,但也往往会直接损害或影响其利益,而且土地补偿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因此,出于对地方政府、村干部或用地单位的强烈不满,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他们会积极响应并参与群体性事件领导者的动员活动。
二是出于对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信任和追随心理。在处于熟人社会的村庄范围内,领导者的角色往往是在长期的集体行动中自然生成的,他们由于特殊的品格、出众的能力或者独有的资源而受到拥戴和信任。因此,在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酝酿阶段,骨干分子往往会基于以往形成的与领导者之间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带领与追随、领导与服从关系而积极响应,甚至参与策划、动员工作。
(三)外围普通参与者的心理
在酝酿发动阶段,普通参与者往往并没有直接行动,而是作为潜在的参与者处于被动员状态。他们的主要心理特征包括:
一是怨恨心理的驱使。普通参与者的怨恨心理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弥散型的,没有具体的怨恨对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近年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定化和纵向流动机会的减少,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增强,形成了以“仇官”和“仇富”为标志的社会怨恨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权益被侵害但又无力改变形成的。正如舍勒所描述,这种报复的冲动处于“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4](p10)状态。于建嵘称之为“抽象愤怒”。[5]第二个层次是因为土地权益受侵害但又无力反抗形成的,具有具体的怨恨对象。他们往往会经历征地过程中的不公境遇而又反抗无效或无力反抗甚至不敢反抗的过程。因此,当组织者和核心骨干的动员活动使他们看到了发泄积怨、获取心理满足的机会时,他们会在心理上接受并乐于看到群体性事件的出现。
二是对土地特殊眷恋心理的驱使。据钱忠好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在现行条件下绝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6](p152)土地之于中国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仅生于斯长于斯,而且要老于斯终于斯;土地不仅是谋生的工具和生存的依赖,而且是心灵的家园和灵魂的归属。因此,尽管有时土地补偿并不低,尽管有些农民的土地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很低,甚至征地与其利益并无直接关联,但多数农民并不希望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参与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不仅是出于理性的计算,而且有重要的情感驱动因素。
三是搭便车心理的驱使。由于靠自身的力量无法维护土地权益,或者在其他问题上有维权不成甚至无力维权的经历,因此,无论征地是否直接关系他们的利益,群体性事件的即将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借助群体力量,使基层政府陷于被动境地并借机向其主张自身其他方面权益的机会,因而搭便车心理成了他们接受动员的原因。
二、爆发和高潮阶段
一旦前期组织发动成功,出现大批民众阻塞交通、阻止施工、围攻政府甚至发生损毁公共财物、与警察和用地单位发生肢体冲突等状况,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随之就会进入爆发和高潮阶段。在此阶段,由于局面充满冲突而且瞬息万变,各角色的心理活动也更加复杂且充满矛盾。
(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心理
一是既希望把事情闹大以解决问题,又希望将事态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以防祸及自身的矛盾心理。作为具有村干部、老党员、退伍军人等身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和理性精神,其发动群体行动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向政府施压以维护权益。因此,一方面,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更多的媒体报道,最好能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唯此才可以给基层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进而达到维权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由于这部分人一般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和理性精神,其发动群体行动的目的并不在于发泄不满或者进行破坏,更重要的是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又极力希望将群体性事件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是孤注一掷心理的驱使。对于这一类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言,由于是在其他途径都无法维护利益的背景下被迫发起群体行动,而且一旦发起群体行动,他们与基层政府及用地单位之间极易形成零和博弈局面,即要么通过群体性事件最终维护自身利益,要么被迫接受现实而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同时,“如果他停止了维权抗争,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里,也就失去了人们的起码尊重,会被人称之为软蛋”。[7]因此,这类组织者和领导者出于对生存伦理的守护需要,或者出于 “争气”,即“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来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8]的需要,在群体性事件的高潮阶段往往会变得很极端。同样,在心理层面,这类组织者和领导者往往没有第一类领导者的理性和克制,孤注一掷的心理往往是其主观方面的重要特征。群体性事件中的过激行为,如攻击性行为或者自杀、自残行为也往往由这些人做出。
(二)核心和骨干分子的心理
在此阶段,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骨干分子,他们的心理特征有:
一是乐于表现的英雄主义心理。在酝酿与动员阶段,如果说组织者和领导者起主要作用的话,那么在爆发和高潮阶段的主要角色就变成了核心和骨干分子。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往往会形成一个特殊的“气场”,即“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9]在此“气场”之中,由于有众多的追随者,使其摆脱了平时令其不快的无能感,暂时忘记了可能的危险,而追随者的围观和喝彩更是增强了社会促进效应,即由于他人在场的刺激而使其更加兴奋。在此阶段,即使组织者和领导者极力控制,也很难避免出现过激行为。因此,组织者和领导者往往为了免责而退居幕后甚至远避外地,而核心和骨干分子的行为将决定着群体性事件的形态和破坏性。
二是法不责众心理。骨干分子之所以敢于带头,是由于当人们处于一个群体之中时,会出现“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情感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10](p51)即由于明显的匿名性,骨干分子会产生去责任感;同时,由于人群数量的增加,又增强了骨干分子的力量感。因此,在上述两种心理因素的作用之下,畏惧法律制裁的意识被暂时蒙蔽,法不责众心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正是在这种心理意识主导下,骨干分子往往会成为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带头人。
(三)外围普通参与者的心理
一是借机发泄心理。如果说多数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动因是由于社会怨恨心理的话,那么他们在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和高潮阶段则明显受发泄心理的驱动。在与政府官员等强势群体的交往中,由于各种原因而积累起来的报复欲,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始终“不能”或“不敢”付诸行动,或者最多只能使用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式的偷偷摸摸地反抗,现在终于有了发泄而且很可能不受追究的机会。因此,一旦有骨干分子带头进行破坏或进行人身攻击行为,往往会有大批的普通参与者群起响应,进而出现局势失控的局面。
二是从众心理。即参与者在“不知不觉受到群体压力,从而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11](p251)正如于建嵘的研究显示,“与税费争议时主要以抗争精英为主情况有明显的不同”,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往往出现“男女老少村民齐上阵的情况”。[12]对于大多数参与者而言,他们并不知道行动的计划和事态发展的后果,而只是盲目追随。尤其是那些文化素质不高或法治观念不强的老人、妇女和年轻人,他们行动的理由仅仅是看到骨干分子或者家里的其他人有了类似的行为。
三是被迫心理。在某些情况下,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会提出某些惩戒性的措施,既包括现实利益方面,例如不参加者将不得参与集体行动所争取到的利益的分配,甚至不得享有在承包地调整和宅基地、村基础设施使用等方面的权益;也包括非现实利益方面的,如人际关系方面的孤立、道德和舆论谴责等社会资本的损失。因此,有些村民尽管并不赞同发起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带有破坏性的违法活动,但迫于多种压力的作用,也会参与其中。
三、回落与恢复阶段
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一般因两种原因会趋于回落,一种是利益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如补偿标准提高,被拖欠的补偿款落实到位,不合法的征地被阻止等等;另一种是出现明显违法犯罪行为,地方政府进行依法处置。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最后都会走向回落和恢复阶段,群体行动消散,社会秩序恢复。
(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心理
一是成就感和满足心理。如果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取得成功或者部分成功,则其中的第一类组织者和领导者维护群众利益的愿望就得以达成,其形象和威望就会得到提升,在社区中的权威和地位就会得到进一步巩固;而第二类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核心利益至少会得到部分满足,威胁其生存伦理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因此,在这一阶段,组织者和领导者无疑会产生成就感和满足心理。
二是失落和理性免责心理。如果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失败,对于第一类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言,其直接的心理感受无疑是失落。因为不仅其理想和信念会受到打击,其形象和威望会受到影响,甚至会面临村民的抱怨和责难。更重要的,他们应考虑如何理性免责。一方面,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惯例,他们是基层政府问责的重点。他们要么证明破坏行为发生时不在场,或者与事件中参加违法犯罪的人员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就事件的结果给村民一个合理的解释和交代,对此,他们一般会归责于政府的强横,事件中某些人没有听从指挥而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等。
三是绝望心理。对于这一类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言,事件失败带来的心理影响可能会更严重。对他们而言,通过群体性事件来维护土地权益本身就是在其他合法途径都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事件的失败无疑会使他们产生绝望、无助与强烈的怨愤心理,而这些心理的出现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二)核心和骨干分子的心理
一是自豪感。如果群体性事件取得成功,骨干分子会获得心理上的自豪感。与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同,骨干分子平时在村中并没用前者所拥有的地位和威望,甚至没有太多出头露面的机会。而在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和高潮阶段,骨干分子在事件成功之后往往会因此得到村民的肯定和赞扬。因此,自身效能感和他人的赞誉都能够极大地提升骨干分子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是失望和悔恨心理。既包括对基层政府的失望,也包括对组织者、领导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失望。对前者的失望是因为利益没有得到合理满足,或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粗暴和蛮横;对后者的失望是因为组织者中途妥协、退出,甚至为自己免责而出卖骨干分子,或者因为其他普通参与者没有像他们那样坚持。悔恨则是因为骨干分子往往是群体性事件高潮阶段破坏行为的带头人,因而也是基层政府惩处的重点。他们往往要为群体性事件中自身的非理性行为付出代价。由于代价沉重而毫无所得,悔恨成为许多骨干分子的心理特征。
(三)外围普通参与者的心理
一是因发泄而得到的满足心理。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只要没有明显的犯罪行为,普通参与者都将被称为“不明真相的大多数群众”而不会被追究责任。因此,无论群体性事件是否取得成功,至少他们在群体性事件中通过呼喊口号、围观等行为,看到他们怨恨的对象陷入被围攻甚至殴打的被动境地,可以使其久积的怨恨得到暂时的宣泄,从而获得短暂的心理满足。当然,如果群体行动取得成功,通过分享集体行动获取利益,他们同样可以获得心理的满足感。
二是因群体性事件失败而导致怨恨的进一步积累。无论农民的诉求是否合理,但由于普通农民多缺乏正确归因的能力,只要群体行动被压制或者无果而终,他们就会将结果归因于政府和用地单位。在他们心中,此次行动的失败再一次验证了他们关于基层政府和用地单位等强势群体的“恶”的形象。对上述对象的怨恨虽得到了暂时的发泄,但由于失败,其怨恨心理会进一步强化。
四、加强社会心理调适,科学处理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
处理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以及提高补偿标准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从加强社会心理调适等多个视角入手。
(一)怨恨的消解与和谐政治参与文化的建构
“怨恨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最为主要的社会情绪之一”,[13]而这种情绪在失地农民中尤其突出。从微观层面看,近年来,征地导致农民的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据党国英的研究显示,“2002年农民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相当于被无偿剥夺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14]更重要的,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缺少知情权、参与权和谈判权,导致农民利益受损的同时又无力表达和倾述,成为农民产生怨恨心理的最重要根源之一。从宏观层面看,随着近年来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显性化,尤其是少数暴富阶层的为富不仁与农民辛劳而清贫的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导致了部分农民的“仇富”心理;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部分贪官的贪腐细节被曝光,尤其是少数官员的奢侈和擅权与农民的弱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致使农民对贪官持仇视态度;随着社会结构的固化和纵向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农民向上流动日益困难;对农民本身而言,勤劳已难以致富;对农民子女而言,知识已无法改变命运。尤其是少数所谓“官二代”、“富二代”与“农二代”的不公平竞争,使农民形成了对强势群体的怨恨。而由于政府和社会忽视并疏于对农民怨恨心理的调适、咨询和纾解,使怨恨心理积郁、传染进而弥散化。
怨恨心理的弥散不仅导致了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高发,而且使群体性事件更容易走向情绪化、无序化和暴力化。因此,要治理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必须先消除农民的怨恨心理。一方面,要尽快解决当前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各种现实问题尤其是征地和拆迁等问题,构建农村利益均衡机制和农民诉求表达机制,保障和维护农民权益;另一方面,要从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改善民生入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拓宽农民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消除农民产生怨恨的宏观社会环境。同时,还要进一步引导农民树立法治观念,培养其有序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其通过合法渠道理性地维护自身的土地权益。
(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有针对性地疏导和纾解农民因征地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
当前,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缺少对于农民心理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更缺少对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各环节和各角色心理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导致其预防和应对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举措缺少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建立心理调适机制,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就成了有效预防和治理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的必要途径。
一是重在事前调查和预防。在征地之前,有必要通过座谈、访谈和问卷等形式了解农民对征地的心理接受状况,尤其是村中意见领袖和权威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在征地过程中,密切注意农民对土地面积丈量、补偿标准、补偿分配办法、就业安置、社会保障补偿等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在征地之后,注意调查农民对征地后生产和生活的满意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详尽的信息公开和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对农民的各种疑问予以解答,消除各种谣言和猜忌,及时发现和解决农民的各种心理问题,预防农民不满情绪的产生和积累。
二是在征地诱发型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针对不同阶段各个角色的心理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于组织者和领导者,重在通过理性沟通和解释,消除各种误解,或者在爆发和高潮阶段能够有效约束参与者,避免暴力行为,并在回落和恢复阶段配合政府对事件进行善后处理;对于核心和骨干分子,则重在晓之以理,避免其带头做出违法和犯罪行为;对于外围普通参与者,则应消除其借机发泄和法不责众的机会主义心理,劝其拒绝参与,或者至少不会参与违法犯罪行为。
[1]韩俊.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调查[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2]李连江,欧博文.农村的抗议带头人研究[A].载肖唐镖.群体性事件研究[C].学林出版社,2011.
[3](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版,2001.
[4]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曹卫东译.三联书店,1997.
[5]于建嵘.有一种“抽象愤怒”[J].南风窗,2009,(18).
[6]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Ⅲ)[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7]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J].学海,2006,(02).
[8]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J].开放时代,2007,(06).
[9]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9,(06).
[10](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于建嵘.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查[J].调研世界,2005,(03).
[13]郝宇青,车跃.怨恨情绪及其化解: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J].探索,2011,(04).
[14]党国英.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剥夺[J].中国改革,2005,(07).
(责任编辑:高 静)
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ass Incidents Induced by Rural Land Requisition——Analysis on the Point of the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Role
Zhu Tianzhi
S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cess of land acquisition induced mass incid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brewing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outbreak,with the climax,fall and recovery of three stages;From the role in the event,all members can be divided into organizational leader,core backbone members and the periphery ordinary participants.In this paper,the process as the longitudinal axis,taking the role as the horizontal axis,analyses in land requisition of inducible group events in different rol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their interactions.On this basis,from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land management inducible group events should adopt countermeasure.
land-induced type;mass incidents;process;role;psychological mechanism
C912.6
A
1007-8207(2012)11-0061-05
2012-09-07
祝天智 (1975—),男,山东定陶人,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基层治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 “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村征地冲突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CGL097);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管理创新与征地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YJC63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