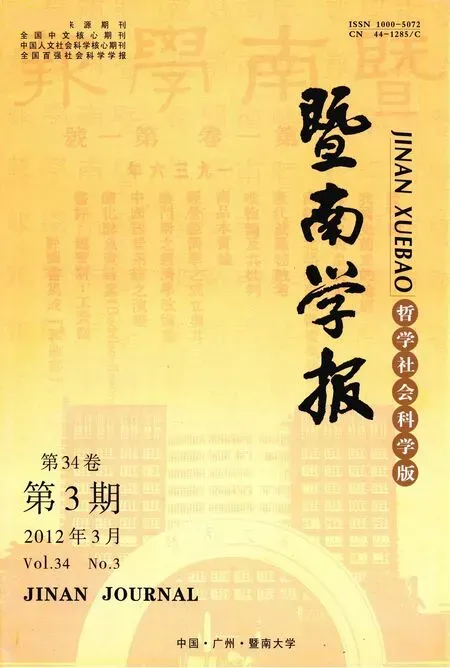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2012-12-18袁济喜
袁济喜,王 猛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袁济喜,王 猛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曹魏文人集团;都城;制度;中心秩序;仿拟
《文心雕龙·明诗》中评论:“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1]66过去学者研究汉末建安文学,多引用刘勰的这段话,强调其对汉代文学,如乐府诗等的改造,对汉赋的改变等。一旦涉及与政治体制和皇权秩序相关的东西,往往将建安文学视为对汉代文学的反叛。但在所谓的“文学自觉”思潮中,有哪些层面仍是对汉代文学乃至政治结构的承袭却少有研究者加以重视。因此,本文想通过对汉末曹魏集团文学实践与文本之辨析,来探讨汉代颂声对中心王权“敷陈其事”与“体国经野”之模式如何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呈现,进而辨析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
一、曹魏营建都城的象征意义
我们通常以“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来评述魏国初建两位君主的治国特色,若联系汉代政治模式的变化观察,则能更进一步理解曹氏营建魏国一脉相承之苦心。曹氏之营建魏国邺都,既在被动的意味上受前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又在主动实践上对前代进行改良。邺下风流不仅是曹魏集团与文士的吟风弄月,也是政治理想的实践活动。
都城在帝国天下秩序中居于重要位置。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就曾说“都邑,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2]465都城之确立,与以都城为中心的“四方”、“八极”之确立,是帝国天下秩序的基本要素。在地理学思想意味上,“文明具备了明确的空间属性,具备了独特的空间价值这些地理观念形成了每个成员的自觉的、成熟的空间常规意识,亦可转化为社会整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方略、开启后世大地域集权帝国的先河。”[3]23汉代的四方,也的确是与当时经过数次讨论而形成的天下秩序观念相匹配的。此观念体系首先是对“三代”古典国制的追溯。《史记·周本纪》载“(周公)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4]143董仲舒《春秋繁录·三代改制质文》曰:“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5]196这个中心也是联系帝国行政祭祀秩序并与天道相配枢纽,因而在《郊义》中强调“宗庙因于四时之易”[5]402在《四时之副》中又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5]353《周礼·春官·大宗伯》说“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6]1296都具有这种以帝王和都城为中心而展开国家典礼祭祀的观念意味。因为这是“圣人有以起之”的“天之经,地之义”。不惟如此,汉人的讨论还进入到非常具体的层面,散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周礼·职方氏》、《盐铁论·地广》、《白虎通义》,以及纬书《河图括地象》等。①此观念与讨论的具体的演变过程,可参见日人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及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其目的显然是欲将不断扩大的汉帝国现实版图与理想典籍中的世界秩序对应起来,以确立权威的天下秩序体系。据徐复观先生考察,汉代的文学创作已经影响着这些政治思想文本的写作,那么反过来当这些文本中的观念成为帝国认定的权威秩序后,也必会影响文人的思想、行动与文学创作,否则就不能承担“体国经野”之重任。张衡《东京赋》就沿着这样的逻辑强调“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7]545可见在这样一个将宇宙、社会与王权法则相互对应庞大体系中,“辨方位而正则”,就意味着可以建立起一系列富有权威性的国家礼制秩序。
简而言之,居天下之中而实现对四方之音乐、文化、物产的控御与汇聚,是汉代政治秩序之核心原则体现。在这种观念体系内,关于都城的建设,礼制规范和文学表现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即土之中”就意味着“京邑翼翼,四方所视”。雄才大略的曹操当然深谙此道,故其迁汉献帝于许都和对邺都的营建也同样富有深意。彼时曹氏集团尚处于觊觎汉室而作各方面准备工作的时期,将汉献帝迁都许昌兼具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一方面便于自己的控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也使得皇帝与传统意义上的帝都分离,从而破坏了洛阳在天下秩序中作为帝都的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再营建邺城,固然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说有以人口,物产,矿藏为向度的物质基础方面之原因[8]207-208。然而在此历史情境中,对于曹操这样具有远图的政治家而言,对邺都在吸纳文学,方术,音乐等人才方面的努力就不仅仅是促成“文人集团”或“贵游集团”这样简单了,而是力图按照汉代洛都为天下中心的政治结构图示,塑造一个新的既有武力法度,又有典章文学而能够实现“体国经野”并光大其事的中心政治秩序,实现他早期的政治理想,我们也可以说,他在邺城的营造,与其说是创新,勿宁说是复古汇聚网络天下人物,首先让邺城与文化制度上的中心符合,继而就能在天下各种势力角逐时显现出自己无可比拟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二、文学中的都城观念及其功能性
两汉时期的都城,是各地文化、音乐、人才物产的汇聚之地。以音乐为例,张衡《东京赋》中曾描写洛阳、长安的音乐之盛,这个盛就意味着要汇聚“四方之乐”,涵括“荆吴郑卫之声。”在汉末人的观念里,“京、洛出名讴”是中心都城所有的文化水准之一②曹植《野田黄雀行》、《置酒》诗皆述此事。。置换到魏国邺都,自然也应具有这种特征。曹植《侍太子坐诗》就以动人的笔调描述了这种场景“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9]450。诗中之“白日”可以喻示君主,“时雨”在东汉时可以传达“夫人道得于下,则阴阳合于上,然后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则夷狄慕德重泽而至矣。(后汉纪.章帝纪)”的意味。由此本诗就体现出“公子”居于高贵奢华的场景之中心,实现对齐、秦音乐家和歌唱家所象征之“四方”的汇聚。
与音乐相类的是物产,曹植、王粲、陈琳、刘桢等诸人多次针对某一物品为同题之作,如《迷迭赋》、《马勒脑赋》、《车渠碗赋》等。邺下文人集体性吟咏奇珍物品,仅仅归为咏物赋来看待是不够的,而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中的个人抒发与并归因于魏晋文学与政治功能的远离就更不确切。无论是王粲的《迷迭赋》的“扬丰馨于西裔兮,布和种于中州。去原野之侧陋兮,植高宇之外庭,”[7]912(王粲《迷迭赋》)还是“尔乃他山为错,荆和为理,制为宝勒,以御君子。”[7]926都在强调这些物品的珍贵以及产地之遥远,然而在曹氏魏国“广被仁声”后,四方之“夷慕义而重使,献兹宝于斯庭”[7]137。这种类似于应制诗一般集体对各方珍稀物品的吟咏,显然也是一种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对邺都象征性中心地位“义尚光大”之努力。
曹魏集团的努力实际上系统涵盖着能够体现帝国中心制度的各个方面,如音乐的搜寻与重建,据《晋书·乐志》载: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10]679
再如对待方士,曹植《辩道论》记载:“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7]181。又如典章的重建,当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2]598以及对宗教神祗的赞颂等①据《宋书·乐志》记载,王粲曾专作专以登歌安世诗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关于汉代宗教祀典研究请参见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文学活动成为当时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与杨德祖书》,曹植先描述一番汉末文士散于各地,赞颂“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7]159这些例子都反映出,即使是在天下秩序崩溃的汉末,汉代秉行的以都城皇权为中心而建构天下秩序的原则,仍然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直到西晋,这种观念作为皇权制度的原则仍被重视,《晋书·乐志》记载“武皇帝采汉魏之遗范,览景文之垂则,鼎鼐唯新,前音不改。”[10]676明晰这一线条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为何西晋时皇甫谧作在《三都赋》序中谓左思之作“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如果单从文学辞藻观念去理解他的文章就不免失之偏狭。若从都城与皇权和天下秩序关系的角度,则能更深入的理解其中与班固“博我以皇都,弘我以汉京”相似的观念形态。这既是贯穿汉代政治制度建设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成为汉末人们思维框架中或显或隐或自觉或非自觉的行动模式和创作背景。
由上论可知,尽管此时之邺都未能成为天下之中,但在文化意义上成为正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现实政治局势与汉代秩序观念一起影响着汉末文人将对往日的追怀寓于对新秩序的想象之中。曹魏文人集团,从文学史看来似乎代表着开启“文学自觉”的趋势,然而在曹操所力图建立的新政治图景中他们所对应的恰恰正是汉代“光大”都城和帝王秩序的功能。换句话说,邺下文学集团的创作活动和成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是其形成的直接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形成中的新政权对文本的各种功能性需要。在一个既有各方敌对势力又有维护汉代势力的环境中,以文本形式宣扬曹魏政权并非仅有军事之势,而是具备与之前的神圣帝国同样的可资光大和具有中心吸引力的都城配置与上层文化制度②对汉魏文人景观、空间、政治等象征意义研究较多的是台湾学人,参见郑毓瑜《试论公宴诗之于邺下文人集团的象征意义》,《六朝情境美学综论》第172-210页,(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在获取“禅让”所赋予的合法性之前,曹氏集团主要通过对汉代都城和帝王中心秩序或隐或显的营构来彰显自己在天下群雄中的权威与正统,即营造出曹氏集团处于中心秩序下,对四方文化、物产、人物的汇集从而宣扬曹氏魏国在文化、礼仪、典章等诸方面的中心地位。所以《典论·论文》对文学“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弘扬,固然已经有新的时代环境,创作风气中的新内涵,但是我们却总能在其中听到汉帝国功能性文学建制的回声。
三、文学中王权模型的表现方式与功能
在曹魏文人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对汉代模型较为直接的仿拟,即对中心秩序下对四方的汇集与控御之描写;另一种则是较为深层,是在场景的结构设置上隐现出一个以主人为中心的宴会秩序(这个体系结构本身显然是对汉天子与周围的文学侍弄之臣的模仿),围绕着一批文人相互唱和,歌颂其人格与可能取得的功德,并着力赞颂君臣之和谐。前者多用于都城,后者多用于主公,因为能够与汇聚四方珍奇的壮观都城匹配的正是中心王权。早在帝国秩序尚未完全肇成的西汉,司马相如就说“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4]3068到了东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帝国秩序逐渐完善,班固在《两都赋·序》就说:“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强调文人“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并界定赋作“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7]235西汉“劝百讽一”的标准逐渐被淡化,而代之以强烈的国家意识。对国家来说,需“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对文人来说则说“臣子当颂”,并且强调“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11]847-854。由此,帝国政权合法性与神圣性的确立就包含了物质现实的营造与文本创制两个方面。一个同时具有“怀柔远人”的“德化”能力与军事征服能力的帝国政权,需要文章来记载,传播自己的功绩和形象。进而言之,一个和谐完整的天下本身,就应当包括事功和与之相对应的典诰礼制文本。
曹魏集团文学创作中更多的对应比拟来自围绕汉天子所建构的正统皇家典礼秩序。东汉春天有朝会礼,帝王会见群臣及天下诸侯方国使者,其以帝王和京城为中心,宣示天下秩序之和谐的象征意味极浓。东汉班固《东都赋》曾记载其场景:“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2]240张衡《东京赋》也记述“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聊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7]544语句或有夸张,但其向我们展示的天子居于帝国中心实现对四方控御教化的东汉帝国秩序观念中仍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基础上,往往还要进一步突出宴饮场面之盛大器物之尊贵,君臣之和谐,以彰显帝王之威仪与天下之和谐。汉代以皇帝为中心的盛大场景如“庭实前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7]36,都以描写盛大的场面和尊贵的器物来显示天子之庭的气度,继而突出“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4]37或是“君臣欢康,具醉熏熏。……上下通情,式宴且盘”[7]110,以强调天子之礼乐以及君臣和睦,上情下达的和谐。唯此方能显出人间仪礼合于天道从而颂扬帝国所控御的天下秩序之和谐。
魏国彼时尚未具有天下,也并无天子的法度。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文人创作仍然表现出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凸显魏国君主位居中心位置,与群臣欢宴并上下通情的和谐形象如阮瑀《公讌》诗,先言“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在时间上就暗合于东汉帝王之春日朝会,之后又以“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9]380,描绘出一场围绕中心秩序,汇聚中外物产而展开的欢宴。又如王粲《公宴诗》“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以昊天与百卉喻君臣关系,继而突出“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最终渲染君主众人气氛和畅以至于“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直到诗尾才稍显露骨的赞颂“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9]360前文已论述过东汉之帝国政治观念将四时、四祭、四政、四方沟通起来,形成一个天人合一,宇宙与社会同步运转的认识论体系。因而其文学往往先言时令之后才描写帝王的相应的活动。汉末文人也很注意这一点,徐干就曾在《中论》里强调“信无过于四时”。上引阮瑀和王粲的创作是都先叙说时节天气之佳,继而写人事以呈现出这种人间秩序与天地秩序合一的和谐。曹丕《夏日诗》以主人的视角叙述“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亦是如此[9]404。徐公持先生曾注意到曹植《当车以驾行》、《元会诗》与曹操《气出唱》在描写欢宴场面,饮酒作乐以及歌舞助兴等方面的相似性[12]44-45。结合本文的考察,我们认为这实际上说明曹魏文人据以观察世界的角度以及背景之相似性。通过对汉代描述帝王之事的文本与观念进行模仿改造,曹魏文人以相似的结构来展现光大曹魏势力。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之一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高雅有序的君臣共乐的场景:“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大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9]369而曹植《公讌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昌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技。神飚接丹毂,轻荤随风移。”与刘桢同题诗“芙蓉散其华,菡萏溢出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的描画更将宾主和谐推至与周围环境、自然景观、植物鸟兽相互感应的层面。综而论之,曹魏文人以金罍与甘醴,嘉肴与珍果,以及“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9]369的器物与场面来显示宴饮场合之高贵,同时以宾客环侍显示出“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之威仪[9]383。最终,所有的这些描写最终都指向刻画出一个兼具仁德法度的君主以及环绕其周围的和谐的天人、君臣、甚至自然秩序。虽然没有如汉代君臣“具醉熏熏”,但也是在一个具有相当品级气度的场景中实现了“穆穆众君子,好合同安康。”或是“四坐同休赞,宾主悦欢欣。”[9]384
我们不难发现,上引诗作对围绕主人的中心秩序的描绘,对人才汇聚的强调,对周公的比拟,对奢华景象的强调,以及对天人君臣和谐景象的呈现都在某种程度上模仿着汉赋所记录的天子祀典之场景结构,构建出一个小型的围绕中心旋转的和谐景象。其中对景物和事件的叙述顺序与叙述结构,也往往与汉赋对帝王活动的描写相类,只不过由于现实环境的局限和舆论环境的局限,尚不能采取汉赋那样的夸张与铺排。但是,配合曹魏集团的军事活动和制度建设等其他方面的努力,此类文学创作已经足以烘托出一个与当时其他割据势力相比,具备初步礼仪规模和文化品位的中心政权形象。因此,曹植在《王仲宣诔》中才说:“我王建国,百司俊乂。君以显举,秉机省闼。戴蝉珥貂,朱衣皓带。入侍帷幄,出拥华盖。荣曜当世,芳风晻蔼。嗟彼东夷,凭江阻湖。”[7]186在赞颂王粲之余,对魏国礼仪典章完备的自得和对凭天险偏据一方的东吴之鄙夷溢于言表。毕竟曹氏集团所追求的是“将参迹于三皇,岂徒论功于大汉。”[7]174在汉代观念的影响下与当时的现实情境中,唯有具备“天下之中”的礼乐形态,才能宣扬四海臣服的正统象征意义,这应是曹魏三祖在好文辞的个人兴趣之外,努力营建文学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曹氏集团的文人作有一系列都城赋,如徐干《齐都赋》,刘桢《鲁都赋》,杨修《许都赋》,吴质《魏都赋》,曹植《洛阳赋》等。可惜现在仅有残文而无法览其全貌但是由上文所分析之背景,我们不难猜想此类赋作与东汉都城典章秩序以及曹氏集团营建魏国现实努力之间的关系。
在德化的王权之外,与王权威仪相配的军事实力一面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彰显。萧统《昭明文选》赋类自京都赋之后,接以校猎,想必正是从这一思维模式出发。汉末曹氏文人集团也近乎如此,在对现实政治秩序的文本建构中,这样的观念模式既是政治所必要,也为思维所本能。汉末文人创作中之被动:一是因为曹魏集团(或当时的其他势力)在汉代政治观念影响下欲使用这些文人润笔“鸿业”;二是因为文人群体必须运用历史经验性的概念与文辞对新的现实环境进行“再生产”性质的分类与表达。除上引诗歌赋作外,这种表现最直接就可见于征讨校猎赋,为方便对比,先以两汉大一统秩序背景下献于皇帝的相同或相似题材之赋为例:
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扡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後道游,孙叔奉辔,卫公骖乘,江河为阹,太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生貔豹,抟豺狼,手熊罴,足野羊,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4]370
——(司马相如《上林赋》)
——(杨雄《羽猎赋》)
这些大赋为虽异时异人而作,但是在内容的描摹,气势的渲染以及叙述的结构方面都差不多,这说明其背后实为表现帝制之正统观念体系,不可因人才情而随意更改,自然也不能随意僭越。再举汉末为曹氏集团而写的作品:
相公乃乘轻轩,驾四辂,驸流星,属繁弱,选徒命士,咸与竭作,旌旗云挠,锋刃林错。扬晖吐火,曜野蔽泽。山川於是摇荡,草木为之摧拨。禽兽振骇,魂亡气夺,兴头触系,摇足遇挞,陷心裂胃,溃脑破颊,鹰犬竞逐,弈弈霏霏,下韝穷绁,抟搏噬肌,坠者若雨,僵者若抵,清野涤原,莫不歼夷。[7]910
——(王粲《羽猎赋》)
长铩纠霓,飞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连。跱如丛林,动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厉障澨之双川。列翠星陈,戎车方毂。风回云转,埃连飚属。雷响震天地,譟声荡川岳。遂躏封豨,籍麈鹿,捎飞鸢,接鸑鷟。聚者成丘陵,散者阗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纷其翳日。[7]39
——(曹丕《校猎赋》)
通过对比可见,两汉赋作中对帝王出猎场面描写所具有的诸种元素,如舆服旗帜,山川态势,鸟兽惊惧之状,军队披靡之势等都在汉魏之际的赋作中直接表现出来。建安时代,东汉天子已经没有现实的权力,而曹操所具有之魏国势力又不具有理想之名位。此类文章恰恰通过对传统帝王才能拥有的宏大的校猎“图景”结构之仿拟,将现实的势力与理想的名位结合起来,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情境中实现了“光大”曹氏之权势与合法性的政治目的。另外,由于天子对天下四方的控御不仅有征伐和炫耀,还通过巡视祭祀等“法古”的礼制手段。汉末诸多以征讨校猎为题材的赋中也在新的语境中仿拟了这种巡视的形式。如徐干《序征赋》慨叹:
余因兹以从迈兮,聊畅目乎所经。观庶土之缪殊,察风流之浊清。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从青冥以极望,上连薄乎天维。刊梗林以广涂,慎沮洳以高蹊揽循环其万般,亘千里之长湄。[7]939
又如阮瑀《纪征赋》写道: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轨。希笃圣之崇纲兮,惟弘哲而为纪。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贤智其能使。五材陈而并序,静乱由乎干戈。惟荆蛮之作仇,符治兵而济河。遂临河而就济,瞻禹绩之茫茫。距疆泽以潜流,经昆仑之高冈。目幽蒙以广衍遂沾濡而难量。[7]934
这两段文字中都涉及对军队经行之地的描写,体现出一种对四方河山的巡视意味。与杨雄《河东赋》“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从而“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宗”[7]522的描述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思维联系,尤其是阮瑀之作更是如此。如果说前面校猎赋中体现的是王权对天下四方的武功之炫耀和征伐的宣扬,那么这种描写就是天子对天下四方带有“礼”之意味的巡视在战乱时代一种被动的变体。中国古有望秩之礼,《尚书·尧典下》载舜即位之后,“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13]39在董仲舒阐发的帝国秩序中帝王之望秩既也为“奉天”而又“法古”的表现汉末文人虽迫于战乱而仅能描写军事活动,然而通过汉代文学和制度传承下来的这种对天下各地带有巡视意味的思维模式却延续了下来,并表现于文学作品。事实上,这种观念痕迹也不仅只限于魏国,如陈琳就曾为为袁绍讨伐公孙瓒作《武军赋》。这种对军阵景观,狩猎场面的描画并不止于校猎文章,它也作为叙述模式渗入了建安文人创作的其他作品中,如王仲宣之《弹棋赋》与应玚《弈势》就都是写以军事喻写棋势等等。
四、结 论
综上所论,建安时代曹氏集团试图在汉代帝王—都城中心观念体系下构建新的社会共识之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汉末名士对曹操的期待也折射出一种期待强权人物恢复纲纪的心态。如汉末太尉桥玄为曾对曹操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汝南月旦评主持者许劭称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颍川名士李膺之子李瓒认为:“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并临终命子舍张邈、袁绍而归曹。不烦赘举,皆可说明建立与恢复如汉代一般的国家秩序是曹操与汉末士人始终无法超越的政治理想模式。曹魏集团与文士固然有许多感时伤乱的诗文,但也无法超越历史思维对自身的束缚。尽管《隋书》批评“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14]1544。而今人多言汉魏时文学之自觉,脱离政治经学之束缚。但由以上角度观之,文学在建安时代仍然非常强调其功能性,大批文学之士也是由于功能性的需求而被任用。而这种功能性的强调,又是与汉末文人自己的传统——以帝王和都城的威仪法度为中心继而去“体国经野”,褒颂光大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据现代之文学概念而去规矩古人,反而会陷入文学与政治相离则立,相合则僵的简单范畴,忽略文学本身具有的功能性,以及文人的文学才能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劭在《汉官仪》提出:“国之大事,莫尚载籍”,邯郸淳《上受命述表》称:“《雅》《颂》之作于盛德,典谟兴于茂功德盛功茂,传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载之,金石以声之,垂诸来世,万载弥光。”[7]258直到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仍强调:“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7]819这些都说明曹魏文人集团的创作,在其纯文学的特征之外,既体现着曹魏集团在汉代政治经验影响下建设新的中心秩序的努力,也体现着文人以历史的经验重新描画现实的努力。曾经的典章制度与观念并不会凭空消失,其深层结构的变化,也远比我们想象的缓慢。因此,从都邑与王权相结合的角度去重视观察与讨论曹魏集团的诗文创作,再来看他们的感时伤乱,将是一个更全面的视域。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一册)[M]∥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严可均.全后汉文[M].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M].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9]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中华书局,1983.
[10]房玄龄,等.乐志[M].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东汉.王充.须颂[M].论衡.北京:中华书局.
[12]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Literary Activities of Caowei Bloc in terms of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combined with Capital and Royalty
YUAN Ji-xi,WANG Me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In addition to features of self-awareness and lyric,the Works of Caowei literary group still had strong connection with Politic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The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 conceptions circling around capital and royalty did not wither keep with power of Han dynasty,but rather still keep the way which scholars used to express the new reality.At the same time,driven by political reasons,scholars of Caowei force continuously simulating the Orthodox patterns reflected from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 of Han dynasty.Thus their creative writing still had strong political function.Voluntarily or compulsorily,catering to the conception and institution which was already stereotyped in the history.
Caowei literary group;capital;institution;central order;simulation
I206.2
A
1000-5072(2012)03-0091-07
2011-03-18
袁济喜(1956—),男,上海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论研究;王 猛(1983—),男,河南洛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