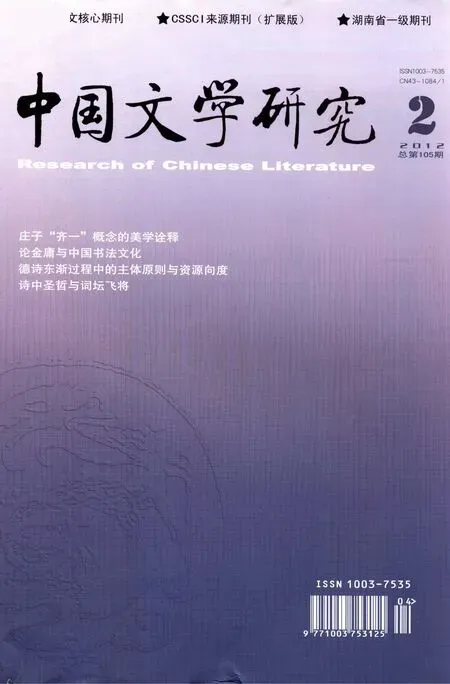德诗东渐过程中的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
2012-12-17叶隽
叶 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诗人巨像”与“文学镜像”的二元互补
选择德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如歌德及其《浮士德》、席勒及其《退尔》,还有尼采和他的《苏鲁支》来考察德诗东渐过程,无疑让人饶有兴味。就现代中国的德国文学接受而言,其他的人物也并非就不重要,即便将相对较近的人物如曼氏兄弟、霍普特曼、苏德曼等人排除在外,那么至少还有像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蒂克、施莱格尔兄弟等煌煌巨星,如何可以忽略?可如果我们回归到现代中国的接受史语境,就会发现,原来其中自有奥妙。仅以其时产生相当影响的若干“排行榜”而言,就各有其标准不同。如谓不信,我们不妨略举二例以做考察。
1902或1903年,诸如赵必振依据日人编本所作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其中就提到歌德、席勒等人(“可特传”、“希陆传”)①,其中涉猎的主要是重要的大家人物;1914年,应时出版《德诗汉译》(1914年1月由浙江印刷公司出版),这是第一部译自德语的著作〔1〕。此书选诗人十位,诗作十一首,除歌德、席勒、海涅等大家外,另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乌兰德(Ludwig Uhland,1787-1862)、毕尔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施瓦布(Gustav Schwab,1792-1850)等名家,但至于象赖尼克(Robert Reinick,1805-1852)、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纪善勃赉希(H.Ludwig Griesebrecht)等人②,虽不能尽现德国诗史,但颇有独到的文学史眼光;而郁达夫在1931年撰《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提到的则超过此数,共有十五位作家(在出版社意见上另增加四人),包括歌德、席勒、海涅、克莱斯特(Kleist,Heinrich von,1777-1811)、尼采、豪普特曼(Hauptmann,Gerhart,1862-1946)、苏德曼(Sudermann,Hermann,1857-1928)、凯泽(Kaiser,Georg,1878-1945)、托勒尔(Toller,Ernst,1893-1939)、魏特金德(Wedekind,Franz,1864-1918)、施尼茨勒 (Schnitzler,Arthur,1862-1931)③,郁 达 夫 另 加 四 人 是 黑 贝 尔 (Hebbel,Christian Friedrich,1813-1863)、凯勒(Keller,Gottfried,1819-1890)、托马斯·曼(Mann,Thomas,1875-1955)、瓦塞曼(Wassermann,Jacob,1873-1934);此外,他还列了个补充名单,包括: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Franz Seraphicus,1791-1872)、弗莱塔克(Freytag,Gustav,1816-1895)、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Hugo von,1874-1929)、德布林(Döblin,Alfred,1878-1957)、亨利希·曼(Mann,Heinrich,1871-1950)、布罗德(Brod,Max,1884-1968)等。这个名单虽是在中华书局编辑草拟基础上增补,但确实仍有一定之代表性。在歌德、席勒、海涅等传统名家之外,已注意到将克莱斯特、黑贝尔、格里尔帕策、凯勒等纳入视域,甚至作为哲学诗人的尼采也没有错过,而当代作家中则所举更是不少。不过,擦肩而过者也并不算少,譬如作为浪漫派集大成者的诗人代表蒂克(Tieck,Ludwig,1772-1853),还有如荷尔德林,当其时代者如黑塞、卡夫卡等,仍不可不说有重要遗漏。不过当然谁也不是全知全能,而且品藻选择标准亦各有自,不必太过苛求。
从另一个角度,就推荐作品而言,则也确实颇有见地。如论歌德,择其《浮士德》、《麦斯特》,一下子就把握住了他的最关键性的两部作品;特别推崇黑贝尔、乃是歌德、席勒之后的“一大悲剧作家,系界在德国新旧戏剧之间的一条桥梁,世界文学名著的译丛里,这却是不可少的人物”,举其代表作分别代表初期、成熟期、后期,即《犹滴》(Judith,1840)、《玛利亚·玛格达莱娜》(Malia Mageddalene,1844)、《阿 格 妮 丝 · 贝 尔 瑙 厄》(Agnes Bernauer,1851)〔2〕(P93)。
这份德国文学书目的名单是由林语堂、郁达夫共同选编的,这两位与德国当然有一定渊源,但却未必是最佳人选。林语堂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研究的却是《古代中国语音学》(Altchinesische Lautlehre),而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接受英美文化影响更多;而郁达夫则虽对德国文学饶有兴趣,但终究是由日本旁涉而来。所以其整体修养,倒还未必如他的弟子、日后留日的刘大杰,后者师从日本之欧洲文学史家小铃寅二,从而不仅培养了自家的世界文学阅读兴趣,更学会了如何以学术方法来处理世界文学对象。当初严复就强烈批判那种转译的风气,认为:“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誖常如此矣!”〔3〕(P567)这话虽然只是翻译,但若论及整体性的文化转移,也一样适用。当然严复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走向极端的片面之危害,却不容陈寅恪之通达认知,陈氏曾谈论过文化传播的渠道之别:“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辗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4〕(P83)应该说,针对中国语境的间接传播之弊端,严、陈二氏所见略同;但陈氏的这段之所以很有见地,在能够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就是文化传播之“直接法”、“间接法”各有所长,并不能因中国一地间接传播之失而就完全否定一种方法本身。
虽然这样一份名单,或许仅仅表现出一种意见,但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出他们作为诗人的见地,尤其又是与德国文化相关联者,对当时的中国语境的德国文学认知而言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至于说到各类德国文学史著述,如《德国文学史大纲》、《德国文学概论》、《德意志文学》等④,也都有一定之影响,此处不赘。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接受史的阐释过程中,除了应当充分重视由本土媒介树立的诗人巨像之外,我们也仍能回应接受对象本身的文学史、思想史价值意义的问题。相比较尼采的苏鲁支、歌德的浮士德,退尔形象的中国阐释声调相对单一,至少远不如前者那么众声纷纭、喧哗噪杂,无论是辛亥革命之前欲借之以唤醒国魂的马君武,还是抗战之际的宋之的、陈白尘,乃至建国之后的张威廉、冯至,都不约而同地称道其人民性,可以见出某种程度的“同质性”来,这恐怕不能归责于学者或作家的“浅见”,而应主要反映出《退尔》创作本身的“目标明确”。确实,席勒的戏剧创作,在成就了自家“史诗气象”的辉煌的同时,确实也有其不容规避的弱点,马克思所批评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5〕(P340)或许过于苛厉,但其作品多元阐释度的欠缺则是事实。故此,退尔的意义单一,不能仅看作一种偶然现象。当然,异族形象变换与阐释的单一化倾向,并不是一件值得特别大惊小怪的事情,但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情况究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或“远近高低各不同”。至少从这几个主要个案文学镜像的比较来说,应属后者。因为在苏鲁支、浮士德这两个形象上,其接受情况恰恰相反。虽然在众多阐释中也不乏简单化倾向,但显然更能显示出一种“众说纷纭”乃至“激烈辩论”的气象。而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证出,尼采、歌德的思想覆盖力度是极其强大的,一种伟大思想的标志本身就应该是其“可阐释空间的丰富多元”。相比较本就多少沾染哲学思维表述的苏鲁支(其本质还是哲人的诗性言说),浮士德基本上是个纯粹的文学人物,可在这样一个文学镜像的塑造上,歌德恰恰十分成功地赋予了其独特的思想与哲学品格,而这样一种“运思于诗”的高明,真是舍歌德其难为。问题讨论到这里,已经逼近了下一个问题,即“授者”对“受者”的规定性问题,暂且收住。
总体来说,“诗人巨像”与“文学镜像”之间应该是一种互补、互动、互释的关系,仅仅从某一个单向度去理解,都难免其局限性。不过,过分强调一体感也有问题,譬如维特、浮士德都被打上浓烈的歌德标签,郭沫若说:“我们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迈斯达’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尔夫冈他自己。”〔6〕(P97)商承祖也说:“我们把《少年维特的烦恼》未尝不可以改称《少年歌德的烦恼》。”〔7〕诚然,这些著作中难免有诗人的影子和事迹在,但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自叙传,它是经过升华加工后的艺术创造,这是基本分野所在,不可不别;但诗人原相与文学镜像毕竟千差万别,岂可任意等同?郭、商二氏可谓乃现代中国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为诗人,一为学者,他们如此直截了当地做相近判断,可见其时的风气所向。故此,我们提出“诗人巨像”与“文学镜像”的区分维度,也就是揭示出德国文学东渐过程中的二元问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必须充分呈现此二元,才可能追索在这二元现象之后的那个统一之“道”所在。也就是说,在这二元表象之后的那个“精神”(Geist)在哪里?
二、接受维度的变形:德诗东渐对受者主体的规定性
除了以这样一种接受史史实区分以反证来源国文学史、思想史以外,我以为这样一种比较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如何进一步在细密的维度上区分接受维度的变形问题。这是一个枢纽性环节,对我们深入进行此类研究有重要意义。在本文研究中,我特别选择了不同的点铺展接受研究,即就诗人巨像而言,是国别留学群比较、单个国别(留德)学人群、作为日耳曼学家冯至的个案;在文学镜像而言,则也紧扣某个文学形象本身,展开在现代中国语境内的问题史。
一般而言,接受美学倾向于体现主体性的功用,如姚斯就指出:“接受过程是有所选择的。接受过程具有删节、价值变换的过程,简单化,同时也再次复杂化。因为接受毕竟是独立的,具有新创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对传统进行依赖性模仿。”而更重要的是:“接受中所提出的疑问揭示了选择的意义”〔8〕(P146)。有论者在论及文学影响的关键因素时就强调:“授者提供选择,受者自身才决定取舍。”〔9〕(P1)特别凸显了受者的作用,诚然,受者作为接受主体,起到了决定性的枢纽作用,殆无疑议。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授者”,那么受者又何从受起?必须有给予,才能有取舍。这也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再进一步,如果我们将授者看作是原作者的话,那么即便摒除掉中介过程的各种因子之外(如翻译、媒介、评家、教师等),授者的意义依然重大。或谓各种文学镜像其实所反映者则一,故此有所谓德语文学符码之说,譬如将某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人如歌德看作一个文化符码〔10〕(P17)。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仅做此看,也就过分简化了“授者”的能动意义和规制功用。
作为一代诗哲,歌德不仅成就了文学世界里的君王事业,而且是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不可规避的“诗人巨像”。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歌德之影响乃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命题。在宗白华的视域里:“诗中的境/仿佛似镜中的花,/镜花被戴了玻璃的清影,/诗镜涵映了诗人的灵心。”〔11〕(P357-358)而在冯至那里:“你生长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你为过许多平凡的事物感叹,/你却写出许多不平凡的诗篇;/你八十年的岁月是那样平静,好像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12〕(P228)在冰心的心目中,歌德则极为宽广博大:
万有都蕴藏着上帝,
万有都表现着上帝;
你的浓红的信仰之华,
可能容她采撷么?
严肃!
温柔!
自然海中的遨游,
诗人的生活,
不应当这样么?
在“真理”和“自然”里,
挽着“艺术”的婴儿,
活泼自由的走光明的道路。
听——听
天使的进行歌声起了!
先驱者!
可能慢些走——?
时代之栏的内外,
都是“自然”的宠儿呵!
在母亲的爱里,
互相祝福罢!〔13〕(P1-2)
可郭沫若回忆歌德对他的影响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也很有趣的例子。与多数人的美好回忆不同,郭沫若的歌德追述常带贬义:
我最初从事于戏剧的创作是在民国九年的九月。我那时候刚好把《浮士德》悲剧的第一部译完,不消说我是受了歌德的影响的。歌德的影响对于我始终不是甚么好的影响。我在未译《浮士德》之前,在民国八九年之间最是我的诗兴喷涌的时代,《女神》中的诗除掉《归国吟》(民国十年作)以外,大多是作于这个时期。第三辑中的短诗一多半是前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海涅与太戈尔的影响写出的。第二辑的比较粗暴的长诗是后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惠迭曼(Whitman)的影响写出的。……我那时候要算是感受过些“茵士批里纯”的了。但是自从我把《浮士德》第一部译了之后,这种状态我是绝少感受着的了。内在的感激消(×水固)了。形式的技巧把握束缚起来,以后的诗便多是些没有力气的诗,有的也只是一些空嚷。……我自从译完《浮士德》第一部之后我便开始做起戏剧来了。第一篇的诗作就是《棠棣之华》……全幕的表现完全是受着歌德的影响,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毫没有剧情的统一。⑤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体社会场域的重要人物,郭沫若的自传当然会有相当的场域因素制约,故此“不能尽信”;但另一方面,诗人之追溯“逝水年华”,也有其艺术上“向真”的一面。故此,我们应从“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的双重角度去把握之。我想这其中有几个因素值得关注:一是郭氏自述的时代背景。当他如此对歌德显得“不恭”,甚至称呼其为“西洋贾宝玉”(这可是一个颇有贬义的绰号了)时〔6〕(P97),正是大革命之后,郭沫若东渡十年的时代。他不仅抛弃歌德,也拒绝尼采,从这个意义上,恐怕时代需求和自我左转的功利抉择成分更强些。所以,对郭氏自述“以今日之我讨昨日之我”不可尽信。二是译介工作本身对创造主体的深度影响。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外来影响的力度,但译介工作之重要,尤其是对一个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同时进行的重要翻译作品的潜在规定性,恐怕是超出一般想象的。而郭沫若的青年时代创作,恰与其翻译过程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讶异于其创造文学产品数量之丰富(在创作、翻译方面几乎是并驾齐驱),必须从资源采择与活力激发两个方面有机互动地去找原因;三是创造主体在资源向度上不可避免地面临“多重博弈”的困境,仅就郭氏自述来看,至少在德国资源的歌德、海涅之外,还有美国之惠特曼、印度之泰戈尔。这些资源本身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而是构成了一种相当复杂的博弈张力,如何融汇化生,对主体本身既是一种大机遇,也是一重大挑战;四是授者之于受者的规定性制约。虽然我们这里强调了受者的主体性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授者的原型力量。这里郭氏给了最好的实证之例。也就是《棠棣之华》与《浮士德》的关系,而作为其特点的“诗意盘旋”与“剧情不协”正也是歌德戏剧创作中的大病。有论者曾深刻指出:“歌德一辈子热心地经营剧院,可是他创作的重点并不在戏剧方面。虽说他的旷世巨著是用戏剧的形式铸就的,可是它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一个剧本:非要把它搬上舞台演出,它花蕊里所有的蓓蕾才绽开怒放。正好相反!谁要是看过《浮士德》的演出,不论这次演出是何等的完美精采,都难免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深深感到这部不朽的诗篇有多少精美绝伦纤巧细腻的思想光辉因此遭到破坏。”〔14〕(P65)这段话道出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作为表演性的戏剧而言,歌德并不能算成功。歌德一方面指导剧院的实际演出活动,另一方面在自己创作时却偏偏“思想高于实践”,他在文本中并不太注意戏剧演出的实际效果。所以,难怪斯太尔夫人不客气地批评歌德“不屑于费心处理戏剧高潮,使之产生戏剧性”〔15〕(P179)。但歌德并非是真地“知错犯错”,这样的选择有着他深刻的思想基础,在他看来:“不取悦于人的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新兴艺术之所以败坏,就在于它想要取悦于人。”〔16〕(P285)歌德立定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伦理”原则,即绝不“媚时媚世”。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的则是,作为艺术品,歌德作品确实有其局限,譬如重现在郭沫若剧作中的“剧情不协”。应该承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里最具创造性力量的诗人郭沫若,应该是具有相当明确的主体性自觉意识者。可即便是这样一个大诗人,他在面对强大的授者主体(虽然这个授者本身并没有直接对郭这个受者进行教育或对话)时,仍然表现出自然的规制作用。但随着郭氏创造性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其知力学养的不断拓展和提升,这种情况要不断好转起来。或者,用“创造性对抗”(creative confrontation)的概念更容易解释这种现象〔17〕,但这种“对抗”不能涵盖全部过程,也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属于“创造性”的对抗。
浮士德是德国学者、苏鲁支是波斯圣哲,而退尔则为瑞士英雄,这样三个不同国别的人物,出自德国诗人之手,却又别加改造,乃成就世界文学凌烟阁的“重要人物”。浮士德要放眼望洋,苏鲁支要下山救世,而退尔则要利箭出弦。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人物皆有其表现自我的象征行为,而诗人则隐于形象之后,相比较席勒的民族激情⑥,歌德以毕生之精力倾注于《浮士德》,其目的仍当在超越小我,走向世界,在他的心目中:“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⑦而尼采日后虽“走向疯癫”,但却非常深刻地理解歌德的精神史意义:“歌德的文学属于比‘民族文学’更高的那一类文学。因此,歌德同他的民族的关系既不是生活上的关系,也不是一种新的关系或一种陈旧的关系。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仅仅为少数人而活着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的喇叭,一代又一代的人拿起这喇叭向德意志以外的地方吹去。歌德不仅是一个善良的人和伟大的人,而且他就是一种文化。歌德是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现象。”⑧所以当尼采在盛年之际完成的《苏鲁支语录》,未尝不是一种以浪漫的态度书写歌德的理想。只不过他走的更远,更激烈,更极端!总体而言,在德国思想史上,歌德、席勒、尼采都大约可归纳到试图走中间道路的古典思脉中人物,但席勒略为偏左,即接近启蒙思脉;而尼采更为偏右,接近浪漫思脉。三者基本形成了一个左-中-右的格局。
这样一种内在的德诗本身的思想史位置,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规定了其在现代中国语境里的接受状况。尼采(Nietzschen,Friedrich,1844-1900)作为后世之人,反而最受到追捧,成为清民之际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而作为前代大贤的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席勒(Schiller,Friedrich,1759-1805)其实和他相差近一个世纪。可在现代中国语境里,这样一种时间的历史感仿佛就被自然消解了。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在以不同的德国诗人、镜像规划线索的研究过程中,本为现代中国接受创化主体的知识精英个体可能会不断地出现在尼采、歌德、席勒,以及苏鲁支、浮士德、退尔,甚至也包括麦斯特、维特等人的中国之旅过程里,尤其是几个关键性人物,如郭沫若、冯至等。这样一种现象,体现出某种规定性色彩,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以受者为中心的接受史进程里,我们有时也不可能完全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挥洒自如”,而是必须接受授者原型的基本元素制约,也就是必须在“原相变形”的基础上展开接受史研究。
就此而言,即便是一个区区德风东渐,这里甚至仅仅能说是“德诗东渐”,其转换化生的景象也是非常多元而复杂。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众声喧哗”之中“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如何不被湮没在数量众多、人物浩瀚的文学海洋中,才是至关重要的。总体来说,在接受史的细节层面,可以考察者众多。从群体的层级区分,到某个群体的分层研究,再到个体的聚焦,这样一种考察显然需要多维度的互释与渗透。而就诗人接受与形象接受而言,也很有不同之处。但无论如何其表象如何纷纭,我们应把握的核心本质则一,那就是要明确“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的关系。
三、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
无论如何强调接受维度的路径区分,不可否认的事实仍然是,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主体原则。也就是接受主体是否具有强势的知识拓新和学养奠基,这非常重要。
有论者指出中国百年以降尼采接受史之缺憾:“尼采作为一个现代性思想家的形象未被中国知识界认真而充分地刻划出来。”具体言之则为:“‘新民’或‘立人’与‘立国’的思想更多地为‘救亡’所导向,而作为其深层支持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未及从学理上建树性地开拓过,即我们没有接着尼采这一契机而构造出自己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思想体系。”〔18〕(P19)现代性问题乃是20世纪以来的显学,但实际上早在18世纪后期,席勒等人即已非常敏锐地感受到启蒙可能带来的恶果,意识到现代性给人性所带来的断裂,强调说:“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⑨到了19世纪,则片面的启蒙造成的欧西强势则体现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潮流中;20世纪,这种启蒙的极端性发展又导致其内部分裂,英、法竞势于前,德、日突起于后,而美、俄继之。思想的潘朵拉盒子就这样最终以大国纷争的戏剧登场,而受苦者是民众。黑格尔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虽然“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19〕(P51),但终究明确地指出了主体性解救自己的方法,“必须与哲学对抗”〔20〕。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过犹不及”,在他那里,“理性既是思想,又是事物的本质、存在的真理,同时又是真理的实现”,理性就是一切,成为了神话〔21〕(P129)。然而,对于所有这些深层的问题,五四诸贤又何尝能静心细思推究?总体来说,他们仍不能摆脱“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而就“启蒙”而言又远非是能与西方主流概念对话者。有论者如此描述:
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是本源感性与外来意识形态争战协商下极其复杂的共生,借生物学的一个名词,可以称之为Antagonistic Symbiosis(异质分子处于斗争状态下的共生),指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霸权利用船坚炮利、企图把中国殖民化所引起的异质文化与本源文化的争战。〔22〕(P259)
这样一种概括其实并不全面,因为如此“自我-他者”的二元概括,其实并不能穷尽中国文化面对外来者的全景。可毕竟,这比较简单的外力迫来之“冲击-反应”说要略进一层。而就文化思想层面的侨易与交流而言,则远要比这样一种“社会进化论”的思维要更非功利一些,虽然它表现出来往往仍是以功利取向为原则的。
或许,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陈寅恪先生讲的那段话上面,也就是所谓如何才“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问题〔23〕(P17)。因为这不但是陈氏个体所追求的终极理想,而且也是中国学术界与知识人理当追求的方向和设立的目标,它具有超越个体与时代的核心命题。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一一种主体原则和资源向度的关系。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自然是毫无疑问,具体地说,那就是确立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绝对位置。可如何不忘,如何确立,却是陈氏语焉未详的。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同样有这个问题,输入不等同于吸收,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而“道教之真精神”何指?“新儒家之旧途径”又何指?最后的标的则应是“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成系统固然已难,有创获则更难,两者兼具,乃是当求理论上的整体建构与细节处的实质推进并行。“鱼与熊掌”,欲兼得之者。其实,说到底,“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最后的指向都应是“归一”,即以学术创获为厚重积淀与坚实支撑的“成系统之思想”,由学而致思。
中国传统的二元思想结构中,道家日后发展为道教,虽然未免偏于幽远玄虚之讥,但其大道仍是明确的,而且由此可以观测作为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民间宗教方面;而儒家之变则更为清楚,当经历佛学之冲击后,儒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支柱与社会主流,强烈意识到“不变不足以应大变”,乃开辟新儒家之源流,理学的诞生是最好的证明。儒、道二家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即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主要象征,他们的历史就是中国思想与中国社会的进程。但陈氏此处暗示者,乃另一非常重要的思潮,但此乃外来和尚。所谓的“道教之真精神”与“新儒家之旧途径”舍却佛教的传入与冲击都无可言,正是通过对佛家思想的全面辨识、改造与汲取,才有道家之新发、新儒家之崛起,并最终没有被外来强势文化所化,反而将其为我所化。蒋梦麟将中国接受外来文化分为两个大阶段,前者由新疆输入,“千余年来只点点滴滴地传入了少许外国东西。因此她是逐步接受这些东西的,有时间慢慢加以消化”〔24〕(P339-340),所言正是佛教东来这一段历史。反之,佛教虽诞之于印度,但发扬光大并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可谓在中国,这是经过中国化后的佛教才灼射出其灿烂光辉。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到:“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25〕(P380)此理同样适用于对西方诗人的深层探究,如歌德这样的大诗人,其所蕴含之丰富,远非仅从文学文本角度就可以解释清楚;如果只将其视作一种小说、戏剧之类的消遣娱乐之作,不但大大低估了其文化史的价值,而且也将“入宝山而空归”。甚至更深一层,就是适得其反而取其糟粕。事实上,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由华东沿海输入中国,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如潮涌至”,而“西方文化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正是盛极一时,要想吸收这种文化,真像一顿要吃下好几天的食物”,其结果是“反感”。而1902年后,“胃口最佳的学生已为时代精神所感染,革命成为新生的一代的口头禅”〔24〕(P339-340)。这段描述虽然很是简短,但却触及了中国精神史上的核心环节所在,也就是中国文化三变的后二者,佛学东来与西学东渐。而其相异处恰恰在于,对于前者,经历漫长时间的遭逢、冲撞、融合之后终于变“佛教征服中国”为“中国融涵佛教”〔26〕;而对于西学,则还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容消化之⑩,仓促之间所获,未必就是精华。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表现在政治、社会层面,更表现在精英层次的思想、文化层面。五四一代人应对之仓促,实在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虽然功绩显赫,但其责任也不容推卸。相比之下,由曾国藩-张之洞等演变之路径,似乎更加值得推敲。世无完人,然而后世衡史,毕竟是为了资鉴以往、有益当下,故此总结前贤之功过,非仅有“月旦人物”雅好,主要仍在于“面向未来”。
主体原则仍不是毫无疑议的“以我为主”,而是应当“求真、求善、求美”。所有这一切,当以求真为最基础之原则,这才是最为根本也能行之久远的“元规则”(11)。或许,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的判语要略作修正,首当不忘者,乃严守学人求真之本位,而非仅本来民族之地位。无论何时,当以求真为第一原则之“元规则”。而本来民族地位之彰显,主要表现在受者主体乃是具有独立精神和品格之人,他既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大丈夫”,也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即代表此民族文化之人。或许用费希特所明确界定的人类各群体中“学者的使命”(Einige Vorlesungen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来形容也可略作注脚:“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27〕(P43),不但要“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der in allen Stücken der Cultur denübrigen Ständen zuvor seyn soll),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die höchste Stufe der bis auf ihn möglichen sittlichen Ausbildung in sich darstellen)〔27〕(P44),学者应当树立起与普通人一样的最终目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许地山曾非常精辟地总结出两类民族的概念,或许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本来民族地位”之确立而提供另一视角:
民族,可以分为两种,就是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自然民族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底。这种民族像蕴藏在矿床里底自然铁,无所谓成钢,也无所谓生锈。若不与外界接触,也许可以永远保存着原形。文化民族是离开矿床底铁,和族外有不断的交通。在这种情形底下,可以走向两条极端的道路。若是能够依民族自己的生活的理想与经验来保持他底生命,又能采取他民族底长处来改进他底生活,那就是有作为,能向上的。这样的民族底特点是自觉的,自给的,自卫的。若不这样,一与他民族接触,便把自己的一切毁灭掉,忘掉自己,轻侮自己,结果便会走到灭亡底命运。〔28〕(P280)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其划分标准正是“文化交流”。而世界历史中不断得以发展并成为强势国家的,当然都是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文化交流而获取新鲜血液和文化资源的文化民族。而中华民族恰是在这个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个民族,关于中国文化大度能包的事实,翁文灏这样说道:“我们推想中国以前的历史,似乎感觉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就是同化他民族或他文化的力量,常常在那儿活着,把各种个不同的民族或文化都慢慢的调和了,溶解了。这种调和民族及文化的溶解剂,大约就是我们汉族。他们的精神是大度包容,兼收并蓄,但仍能始终不失他的本来面目。好像苍海汪洋,黄砂黑土一律兼收,但终竟不失他的本色。”〔29〕(P74)此语极形象,汉族大度能包,中华民族大度能包,表现在现代中国,其巅峰之作就当为蔡元培改革北大时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惜并未确立为长久之计。蒋梦麟、胡适等翻然变计,固然有其客观场域因素,但不以求真为主体原则(元规则)、功利致用当为要旨,也反映出现代中国的主导型精英分子的远未臻成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是中国之传统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如此就要求我们能“握其大者”。我们现在谈中国传统,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了佛学东渐的背景来谈的,离开了经过中国化之后的佛学知识体系,无论是新道家还是新儒家都无法成立。而五四“打到孔家店”的口号,虽有其不破不立的不得已因素,但也同样见出其器局和气度。也就是由蔡元培-陈寅恪(部分包括吴宓等学衡派)的路径,使我们略微感受到中国之传统大气尚未完全消失。这一点表现在文学接受史领域也很明显,除了鲁迅等极少数精英(当然也免不了向左转)的知识学和思想史意识外,更多人包括如郭沫若、林同济等,基本上都是在一种功利维度考虑问题的。主体虽呈现的很明显,但却并不能把握作为元规则的主体规则,即“求真”。
资源向度则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也就是说,当主体原则明确之后,并非单一的国别资源就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更不仅是“吸收输入外来之思想”之笼统概况就可了事。因为当主体面对他者之际,这个他者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故此资源采择是多维度的,其间既有互补、互释,也有冲突、对抗,如何使之形成一种有序之博弈格局,并进而最终达成有效之融化、创生,乃是一个必须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进行探讨的问题。这其中我们既要注意到主体的能动性,也决不可忽视授者的客观规定性,这也是一种规训与规制,所谓“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说也就是这个道理吧!我们只有客观地认识到这一点,承认这样的基本事实,才有可能真地冲破樊笼而进入一个“带着镣铐起舞”的自由境界。在个体是如此,在群体(或曰共同体)亦然,推而广之,就民族文化层面亦然。
所以,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甚至所谓“中体中用”、“西体西用”,都有其立论成说的内在逻辑。但不可忽略的根本原则是“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的互动,即一方面必须意识到这样一种在“求真”基础之上的元规则与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充分意识到面对外来异者是在内在规定性基础上提供文化资源的,这样一种“资源向度”乃是意味着一种面对外部事物的客观理性态度。在德国三座诗人巨像进入现代中国语境的过程里,我们看到了逐一登场的各家知识精英,他们出于各种立场而借助诗人巨像及其文学镜像而“翩翩起舞”于知识场域,然而能借助这种资源而成就自家“诗与思”之事业者,则凤毛麟角。即便其中突出者如郭沫若,其所提供的经验维度也是很不寻常的。这与德国古典时代知识精英如歌德等人凭借外来资源,区分“资源向度”而成就“诗与思”之人类文明史巅峰,恰成一比。其中可追究的原因固然多哉,然而在“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方面,或许仍蕴藏有最基本的因子可以探寻!
〔注释〕
①赵乾龙《席勒和中国文学》,载于杨武能选编《席勒与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不过阿英说是1902或1903年,赵必振依据日人编本所作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可特传”(歌德传)。阿英在《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第7版上发表《关于歌德作品的初期中译》,不久又在《教育世界》第70号(1904年3月)上发表了《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另见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尤其是纪善勃赉希,查辞书与文学史索引均无此人。参阅张威廉主编《德语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Salzer, Anselm & Tunk, Eduard von(Hrsg.):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插图本德语文学史).Band 6.Köln:Naumann&Göbel,无出版年份。或疑德文拼写有误。
③1931年,中华书局拟组织中国翻译界先翻译19世纪后的百种世界文学名著,国别分配如下:英、法、俄各20种,南欧、北欧各10种,德15种,日5种。参阅《郁达夫文集》(第6卷)的《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
④现代中国(1949年前)进行较为系统的“德国文学史撰著”的主要人物及其著作是张传普(张威廉)《德国文学史大纲》(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刘大杰《德国文学大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李金发《德国文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余祥森编《现代德国文学思潮》(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余祥森《德意志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余祥森编《德意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比较详细的论述,参见拙著《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⑤转引自《郭沫若全集》(第16卷)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实际上,这一点,也为后世论者所指出,如叶维廉就批评郭沫若只学到了歌德的情感而没有其恣肆的想象力。可参阅〔美〕叶维廉的《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而范劲则进一步认为,“实质是这一情感性自我在内容上的空洞。这种空洞自我及其镜像歌德注定要成为现代性追寻者克服的对象,这当然不是歌德的过错,只是表明,‘五四’人对他者的叙述方式将歌德符号化约成了单义的情感象征。”可参阅范劲的《德语文学符码与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里似乎过于凸显了符号化的意义,而忽略了歌德作为诗人巨像本身对受者的规定性功用。
⑥陈铨这样比较歌德与席勒:“歌德是‘世界诗人’,他的眼光常常都注意全人类的发展,他问题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人生。”相比之下:“席勒是‘民族诗人’,他的作品,比较多含地方性,他充分发挥德国民族精神,他有德国民族性格一切伟大的特点。”可参阅陈铨的《狂飙时代的席勒》,《战国策》1940年第14期。
⑦德文原文为:“Nationalliteratur will jetzt nicht viel sagen,die Epoche der Weltliteratur ist an der Zeit,und jedermuβjetzt dazu wirken,diese Epoche zu beschleunigen.”Mittwoch,den 31.Januar 1827.in Johann Peter Eckermann:GesprächemitGoethe-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Berlin und Weimar:Aufbau-Verlag,1982.S.198.中译文见〔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当然,我们注意到歌德说这番话的时候并非没有自家的民族指向,此处不赘。
⑧德文为:Goethe gehört in eine höhere Gattung von Literaturen,als“Nationalliteraturen”sind:deshalb steht er auch zu seiner Nation weder im Verhältnis des Lebens,noch des Neuseins,noch des Verhaltens.Nur fürwenige hat er gelebt und lebt er noch:für die meisten ist er nichts als eine Fanfare der Eitelkeit,welche man von Zeit zu Zeitüber die deutsche Grenze hinüberbläst.Goethe,nicht nur ein guter und groβer Mensch,sondern eine Kultur-Goethe ist in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 Zwischenfall ohne Folgern.Friedrich Nietsche尼采: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人性的,太人性的),1886年。转引自Boerner,Peter:Johann von Wolfgang von Goethe1832/1982-Ein biographischer Essay(歌德传).Bonn:Inter Nationes,1983.S.188.中文本参见〔德〕彼德·贝尔纳《歌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⑨参阅〔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载于冯至《冯至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里的近代,亦可理解为现代。德文为:“Die Kultur selbst war es,welche der neuern Menschheit diese Wunde schlug.Sobald auf der einen Seite die erweiterte Erfahrung und das bestimmtere Denken eine schärfere Scheidung der Wissenschaften,auf der andern das verwickeltere Uhrwerk der Staaten eine strengere Absonderung der Stände und Geschäfte notwendigmachte,so zerriβauch der innere Bund der menschlichen Natur,und ein verderblicher Streit entzweite ihre harmonischen Kräfte.”〔Schiller:über die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Schiller:Werke,S.4012(vgl.Schiller-SW Bd.5,S.583)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103.htm〕际即开端,但大规模的西学涌来仍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参阅〔法〕谢和耐(Gernet,Jacques)《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A Conflict of Cultures),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⑩当然中国与西学接触早在明清之际即开端,但大规模的西学涌来仍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参阅〔法〕谢和耐(Gernet,Jacques):《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A Conflict of Cultures),于硕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11)“元规则”(meta-rules)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学者。Brennan,Geoffrey&Buchanan,James M.:The Reason of Rules: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应时.德诗汉译〔M〕.上海:世界书局,1939.
〔2〕郁达夫.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A〕.郁达夫文集(第6卷)〔C〕.广州/香港: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
〔3〕严复.与曹典球书〔A〕.严复集(第3册)〔C〕.
〔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致斐·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郭沫若.创造十年〔M〕.上海:现代书局,1932.
〔7〕商章孙.少年维特之烦恼考〔J〕.时与潮文艺,1943(创刊号).
〔8〕〔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9〕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10〕范劲.德语文学符码与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1〕宗白华.题歌德像〔A〕.宗白华全集(第 1卷)〔C〕.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2〕歌德.十四行二十七首〔A〕.冯至全集(第1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3〕冰心.向往——为德诗人歌德九十年纪念作〔A〕.周冰若,宗白华.歌德之认识〔C〕.南京:钟山书局,1933.
〔14〕〔德〕梅林(Mehring,Franz).论文学(Aufsätze zur deutschen und ausländischen Literatur)〔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5〕〔德〕斯太尔夫人(Mme De Stal).德国的文学与艺术(De L’allemagne Seconde Partie La Littérature et Les Arts)〔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转引自〔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7〕〔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8〕金惠敏,薛晓源.评说“超人”——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9〕〔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0〕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Werke(全集).Band 2.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0,S.175.
〔21〕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2〕〔美〕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3〕刘桂生,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4〕明立志等.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2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A〕.孙尚扬.汤用彤选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6〕参阅〔荷〕许理和(Zürcher,Erich).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7〕德文为:In dieser Rücksicht ist der Gelehrte der Erzieher der Menschheit.〔Fichte: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Quellen Philosophie:Deutscher Idealismus,S.9663(vgl.Fichte-W Bd.6,S.332)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A〕.梁志学.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文中以中文参阅为主】
〔28〕许地山.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对北京大学学生讲〔A〕.范桥,欧阳京.许地山散文〔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9〕翁文灏.回头看与向前看〔A〕.李学通.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C〕.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