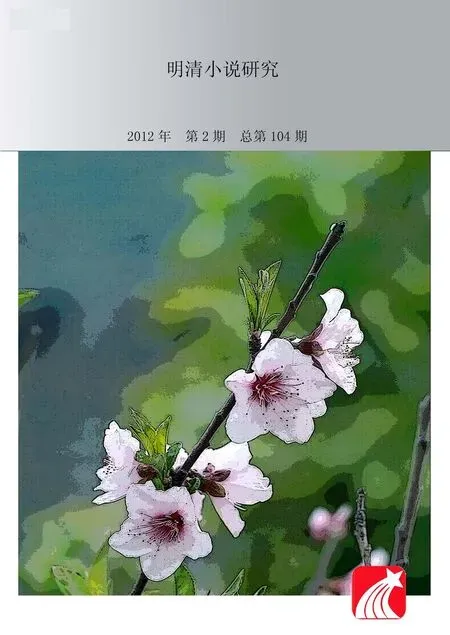《西游记》乌巢禅师探秘
2012-12-17··
· ·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文学杰作。作者不仅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活泼生动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妖魔形象,而且还以独特的知识视野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神佛世界。这个神佛世界中既包括了佛教神、道教神,也包括了民间传说神。其中有些神佛点到即止,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印象,乌巢禅师就是其中一位。乌巢禅师虽在小说中昙花一现,但其所蕴藏的文化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从《心经》看乌巢禅师
乌巢禅师的正面形象只在《西游记》第十九回中出现过一次。书中描写当时唐僧三众行过乌斯藏界,抬头见到浮屠山,八戒称此地是乌巢禅师居所,从而引出乌巢禅师。书中描写禅师所居胜境“山南有青松碧桧,山北有绿柳红桃。闹聒聒,山禽对语;舞翩翩,仙鹤齐飞。香馥馥,诸花千样色;青冉冉,杂草万般奇。涧下有滔滔绿水,崖前有朵朵祥云。真个是景致非常幽雅处,寂然不见往来人。那师父在马上遥观,见香桧树前,有一柴草窝。左边有麋鹿衔花,右边有山猴献果。树梢头,有青鸾彩凤齐鸣,玄鹤锦鸡咸集”①,活脱脱就是一个珍禽异兽、奇花仙草荟萃之地。三藏纵马加鞭,直至树下,看到禅师离了巢穴,跳下树来。在唐僧的百般恳求之下,禅师传了唐僧《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随后,那禅师“踏云光,要上乌巢而去”,被三藏扯住问西去路程,说了一些谶语之后即“化作金光,径上乌巢而去”。行者被其言语触怒,举棒捣其巢穴,却“莫想挽着乌巢一缕藤”。最后在猪八戒的劝说下,“行者见莲花祥雾,近那巢边,只得请师父上马,下山往西而去”②。此后乌巢禅师的正面形象就再也没有在文中出现,乌巢禅师的活动也似乎就此终结了。不过,唐僧师徒在后来西行途中却多次提及乌巢禅师授《心经》之事。如第三十二回孙悟空说:“你记得那乌巢和尚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③第四十三回写孙悟空说唐僧忘了《心经》中“无眼耳鼻舌身意”一句,劝他祛褪六贼。屏息招惹六贼之念。第四十五回、八十回写唐僧危难时念诵《心经》。第八十五回写唐僧见山峰挺立,暴云飞出,隐现凶气而神思不安时,行者又说唐僧忘了乌巢禅师的《多心经》,并由此引出一番精彩对话,文中说:
行者笑道:“你把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记得。”行者道:“你虽记得,还有四句颂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惰懈,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且莫胡疑,随我去。”那长老闻言,心神顿爽,万虑皆休。④
第九十三回师徒快近灵山,唐僧问及路程远近,行者称其忘却了乌巢禅师之《心经》,并称其只是念得,却不曾解得,由此又引出了唐僧“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之语。
由全书的故事情节发展可以看出,乌巢禅师在文中虽只是昙花一现,但他所授《心经》却一直贯穿着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因此,乌巢禅师在文中并非只是一个路人这么简单。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对作品结构又有何意义?
探讨上述问题还得从《心经》的传授说起。据玄奘弟子慧立、彦悰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般若心经》为一病僧所授,文中说: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⑤
在唐人李冗所作的《独异志》中,也有玄奘学习《心经》一节,书中说: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⑥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中,《心经》为一病僧感玄奘之恩而授,名为《般若心经》,其功能在于“在危获济”。而在《独异志》中,病僧已变成了一位“莫知来由”的老僧,虽“头面疮痍,身体脓血”,仍不掩其神异之迹,所以由其所授的《多心经》能令“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不过这一故事发展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又有了变化,《取经诗话》写三藏至鸡足山取得经卷之后,“点检经文五千四十八卷,各各俱足,只无《多心经》本”⑦。随后又讲到香林寺受《心经》的故事:
竺国回程,经十个月,至盘律国,地名香林市内止宿。夜至三更,法师忽梦神人告云:“来日有人将《心经》本相惠,助汝回朝。”良久惊觉,遂与猴行者云:“适来得梦甚异常。”行者云:“依梦说看经。”一时间眼润耳热,遥望正面,见祥云霭霭,瑞气盈盈;渐睹云中,有一僧人,年约十五,容貌端严,手执金环杖,袖出《多心经》,谓法师曰:“授汝《心经》,归朝切须护惜。此经上达天宫,下管地府,阴阳莫测,慎勿轻传。薄福众生,故难承受。”法师顶礼白佛言:“只为东土众生,今幸缘满,何以不传?”佛在云中再曰:“此经才开,毫光闪烁,鬼哭神号,风波自息,日月不光,如何传度?”法师再谢:“铭感,铭感!”佛再告言:“吾是定光佛,今来授汝《心经》。回到唐朝之时,委嘱皇王,令天下急造寺院,广度僧尼,兴崇佛法……”⑧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也强调了《心经》的神异性,不过因为故事中有了一位神通广大的猴行者,《心经》的护法作用已明显弱化。文中所授经文或称《心经》,或称《多心经》,其具体传经的时间不在西行的路上,而是在取经回来的路上。尽管文中说此经能“上达天宫,下管地府”,开经后有“毫光闪烁,鬼哭神嚎,风波自息,日月不光”等异相,但其功能却主要体现在助法师回朝,《心经》出现的意义更倾向于令皇王“急造寺院,广度僧尼,兴崇佛法”,明显带有弘扬佛法的目的。不仅如此,《诗话》中《心经》的传授者已不再是什么病人或老僧,而是佛教中赫赫有名的定光佛了。
故事发展到百回本《西游记》时,其间依然保留了传授《心经》的情节,不过,传经时间是在西行不久,传经者正是巢居树上的乌巢禅师。他对三藏说:“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障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⑨在《西游记》中,唐僧遇难的关键时刻都是由大弟子孙悟空出来救灾解厄,孙悟空是降妖除魔行动的实际执行者,而《心经》所发挥的却是唐僧师徒往西天取经的精神动力的作用。由一种坚韧的精神动力(《心经》)来指导实际行动(排除万难),传授《心经》的乌巢禅师在故事中的地位也就显而易见的了。
由《心经》传授的发展过程来看,不管是《法师传》中的病僧、《独异志》中的老僧、《取经诗话》中的定光佛、百回本《西游记》中的乌巢禅师,还是程毅中先生考证出来的“胡僧”⑩,无一例外地都与佛门中人有着特殊的联系。
二、从历史文献看乌巢禅师
《心经》的传授者与佛门中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我们从百回本《西游记》的描写中也看得十分清楚。《西游记》第十九回写唐僧三众行过乌斯藏界,猛抬头见一座高山。猪八戒说:“这山唤做浮屠山,山中有一个乌巢禅师,在此修行,老猪也曾会他。”后文又几次写到禅师要踏云光,往乌巢而去,最后离去之时更是莲花万朵,祥雾千层。从书中对乌巢禅师的形象描写来看,乌巢禅师应该是一位修行的佛门中人,他在山中修行并傍鸟巢而居。
翻检中国古代典籍,近似《西游记》这一描写的确有其人。其一是齐梁时期的宝志大士,其二是唐代的鸟窠和尚。前者专修禅观,并多有异事载籍,曾依止江东道林寺,据称其幼时为一朱氏妇女从鹰巢中所救,手足皆如鸟爪;后者名讳道林,其母亦姓朱,初修习华严,后也曾修习禅那,据称其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如盖,因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窠禅师。由古籍所载,此二人形象与《西游记》中的乌巢禅师颇多相似之处。
据《神僧传》载:“释宝志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妇闻儿啼鹰巢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钟山僧俭出家修习禅业,往来皖山剑水之下。面方而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止江东道林寺。”宝志神奇的出生经历给他的一生蒙上了神秘色彩,所以载籍多有对其神异事迹的描写,如《高僧传》就曾记载了齐太尉司马殷齐之因宝志画乌而得救之事:“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一树,树上有乌,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乌,如志所画,悟而登之,乌竟不飞,追者见乌,谓无人而反,卒以见免。”另据《佛祖历代通载》载,梁武帝初年,帝令张僧繇画宝志像,繇下笔则不自定,竟不能画。“他日(志)与帝临江纵望,有物泝流而上,志以杖引之,随杖而至,乃紫栴檀也。即以属供奉官俞绍雕志像,顷刻而成,神采如生”。紫栴檀木因宝志的指引而得以供奉刻成雕像,解决了之前不能竟画的难题,结合宝志手足如鸟爪而又出生奇异等事迹来看,历史上的宝志就如神人一般。
《西游记》一百回在描写唐僧师徒功德圆满之后,如来叫唐僧等近前受职说:“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经,甚有功果,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所谓“旃檀”,即是檀香木,“功德”是供人瞻拜而种福田求功德的。在佛教诸神中,旃檀功德佛实有其人,他位于佛陀的西北方,身蓝色,右手触地印,左手定印。而在宝志故事中却有旃檀木因其导引而得以刻成神像供人瞻拜的情节,这与《西游记》中乌巢禅师授唐僧《心经》指引他一路遇难呈祥的故事架构如出一辙。唐僧从乌巢禅师那里学得《心经》之后,每每遇到险山恶水,总不忘将其提出来讨论一番,其中就多次提到修心的问题,如第八十五回行者所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就与宝志大士语录有许多相似之处。《景德传灯录》载《志公和尚十四科颂》也有这样的偈语,如《菩提烦恼不二》:“众生不解修道,便欲断除烦恼。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须别处寻讨”;《迷悟不二》:“欲觅如来妙理,常在一念之中”等等,与唐僧师徒由《心经》而展开的讨论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乌巢禅师的形象还吸收了唐代鸟窠和尚的部分特征。据宋普济《五灯会元》载,杭州鸟窠道林禅师“姓潘氏。母朱氏,梦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诞,异香满室,遂名香光。九岁出家,二十一于荆州果愿寺受戒。后诣长安西明寺复礼法师学《华严经》、《起信论》。礼示以真妄颂,俾修禅那……后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窠禅师。复有鹊巢于其侧,自然驯狎,人亦目为鹊巢和尚”。鸟窠和尚不仅出身奇特,身兼多种异质禀赋,而且还与唐代文学大家白居易有着不寻常的交情。据称元和中,白居易“入山谒师。问曰:‘禅师住处甚危险。’师曰:‘太守危险尤甚!’白曰:‘弟子位镇江山,何险之有!’师曰:‘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礼而退”。鸟窠禅师自身宿于危巢之上不觉其险,反而以位镇江山的太守居险示警,其言本已不俗,又以三岁孩童与八十岁老人为喻,劝化世人勤修善行,其神异之迹在他平淡的言语中跃然纸上。关于鸟窠禅师结草庵修行之事,白居易曾写有《鸟窠和尚赞》诗一首,称:“形羸骨瘦久修行,一纳麻衣称道情。曾结草庵倚碧树,天涯知有鸟窠名。”
鸟窠禅师除在《五灯会元》“白居易侍郎”条中出现外,在《释氏稽古略》中也有记载。《释氏稽古略》云鸟窠禅师讳道林,“母朱氏,诞时异香光明满室,因名曰香光……后见西湖之北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窠禅师。有鹊巢于侧,人又曰鹊巢和尚”。明代另有《鸟窠禅师度白侍郎宝卷》说白居易前身是金妃宫太子,鸟窠禅师是布袋罗汉,可见有关这位佛门高僧的事迹和传说都很奇特。此外,明人何乔远在其《闽书》中也提及鸟窠禅师,不过文中说鸟窠禅师的栖息之所不是《西游记》中的浮屠山,而是白屿山(一名“陈田山”)鸟窠岩,后禅师又曾游杭并巢木杪而居。由以上种种文献可见,唐代的鸟窠和尚不仅亦修禅那,且巢木而居,这与《西游记》中所塑造的乌巢禅师如出一辙。《西游记》第十九回描写乌巢禅师从树上下来,又几次欲返乌巢之上,最后孙悟空举棒捣其巢穴等情节,展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结草庵倚碧树”的鸟窠和尚形象。
百回本《西游记》既为吸收多种文化成果而成,乌巢禅师糅合不同时期的多个人物形象也就并不稀奇。不过百回本《西游记》中还设置了一个有趣的情节,即乌巢禅师与唐僧三众见礼时直接与猪八戒答语,却不知孙悟空是谁。由这个情节可以推断,猪八戒与乌巢禅师是旧时相识,而与孙悟空却略显生疏。从他离去之时所念“多年老石猴”之语来看,似乎又是了解孙悟空底细的,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对其知之甚少而已。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之前闹天宫、闯地府是何等威风,禅师既有参透天机之能,安能不知此人?但他显然又无缘结识孙悟空,说明他与孙悟空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并不重合,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乌巢禅师的主要活动时间应在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之后。书中说五行山是王莽篡汉之时从天而降,此时在公元九年左右,下距唐僧救孙悟空出山时已有六百多年,而猪八戒与禅师的交往当在这六百年间。从这一时间段上推测,乌巢禅师的主要活动时间应在汉魏六朝年间,而符合这一历史时段的又以齐梁时期的宝志大士略胜一筹。
三、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看乌巢禅师
宝志大士既从鹰巢中得生,而鸟窠和尚也不过是傍鹊巢而居,那么《西游记》为何又以“乌巢”为名来给唐僧安排一个引路人呢?这要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及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形象说起。
乌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形象几经嬗变:先秦两汉时期,乌鸦常以一种神鸟的面目出现。至汉魏六朝时期,注入了很多忠孝伦理的成分。宋以后人们对乌鸦的态度出现了细微的变化。据《容斋续笔》载:“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在北方人的心目中,乌鸦仍然是一种吉祥的鸟类。但在南方,乌鸦却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恶鸟,它的出现往往预示着一些厄运和不祥,所以人们一见到乌鸦就要张弓挟弹,必欲驱之而后快。乌鸦在南方人心目中地位的变化,可能与它常出现在坟茔、腐尸聚集之地等自然习性有关。尽管如此,乌鸦与太阳神相伴生的文化底蕴却顽强地保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中,而其中作为太阳精魂被羿射落人间的九只三足乌形象更是定格在古代的神话作品中。
据上古传说,上古有十个太阳住在扶桑树上,它们每天轮流出来照耀大地,不料有一天,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于是天帝令神射手羿到凡间解救危难,羿弯弓搭箭,一下射下了九个太阳,这些太阳落到地面却变成了九只颜色金黄、体形硕大的乌鸦,乌鸦从此成了“日之精魂”的化身。乌鸦在古代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也伴随着人们对太阳神的崇拜而展开。太阳和乌鸦的联系始见于《山海经》。据《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高诱注曰:“踆犹蹲也,谓三足乌。”《五经通义》也说“日中有三足乌”,所以后世常把太阳称为“三足乌”或“金乌”。可见,太阳神崇拜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何新先生认为:“上古时代的中国曾广为流行对太阳神的崇拜。这些崇拜太阳神的部落也许来源于一个祖系,也许并非来源于一个祖系,但他们都把太阳神看作自身的始祖神,并且其酋长常有以太阳神为自己命名的风俗。”正因为如此,那些作为太阳精魂化身的乌鸦也具有了与众鸟不同的神性。
尽管乌鸦形象几经变迁,但乌鸦作为一种神鸟和祥瑞的象征在一些神话传说中却根深蒂固。在这些作品中,乌鸦首先是一种祥瑞,是天意的象征,在有乌鸦出现的地方,往往伴随着政治清明、天下承平等一系列祥瑞之事的发生。据《礼斗威仪》载:“江海不扬波,东海输之苍乌。”又云:“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输以苍乌。”《尚书纬》称:“火者,阳也,乌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业,故乌瑞臻。”《吴历》曰:“吴王为神主表,立(原书作“五”字,引者改)庙苍龙门外,时有乌巢朱雀门上。”王隐《晋书》说:“虞溥为鄱阳内史,劝励学业,为政严而不猛,宽裕简素。白乌集郡庭,止于枣树,就执不动。”此外,乌鸦的神异性还在于它是天命的体现。据《吕氏春秋》载:“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墨子》中对此事也有记载:“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国。”在周代商之际,人们以乌鸦衔玉珪降临周的祭坛象征周文王代殷,又在武王伐纣之际,以乌鸦的神秘出现作为天命的象征。
汉魏六朝时期乌鸦的形象注入了很多忠孝伦理的成份。东汉许慎著《说文》即称乌为孝鸟。《春秋元命苞》曰:“火流为乌,乌,孝鸟……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孝子传》记载:“李陶交趾人,母终,陶居于墓侧,躬自治墓,不受邻人助,群乌衔块,助成坟。”《异苑》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阳颜乌,以纯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所居之村,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至孝,故慈乌来萃,衔鼓之兴,欲令聋者远闻。”乌鸦从神鸟到孝鸟形象的转变,一方面可能与汉魏时期的社会审美思潮有关,另一方面,这些作为“孝鸟”形象出现的乌鸦并没有改变其作为瑞鸟的灵气,所以民间还普遍流行着乌卜的习俗。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对乌卜之事多有记载,如汉景帝三年,“有白颈鸟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泅水中,死者数千”。后人以其预示楚王刘戊谋反兵败,堕泅水而死之事。在这些故事中,乌鸦不仅具有神性,且代表着正义的一方,这与民间传说中三千乌鸦兵捍卫孔子理想的故事也是一脉相承的。相传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在各诸侯国施行,由此危及到许多大臣的利益,因此有人千方百计要谋害孔子。这天,孔子带几个弟子猎于尼山,忽然许多匪徒从四面八方围来,孔子与弟子们在斗争中伤亡惨重。就在这时,数不清的乌鸦从天而降,冲向兵匪,保护孔子和弟子们化险为夷,并护送他们安全地回到家中。据说孔子去世后,这些神勇的乌鸦仍然不肯离去,他们世世代代地守护在孔子的墓园——孔庙,从而形成了“孔庙乌鸦成群,孔林乌鸦不栖”的神奇现象。尽管这个故事只是民间传说,但其文化底蕴却是十分深刻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数千年文化的奠基者和引导者,同时也是“圣人”的化身。在古人的心目中,孔子身上实际上寄托着人们对正义和理想的向往,所以,在“三千乌鸦兵”的传说中,乌鸦已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和人类理想的忠实捍卫者。
在《西游记》所构建的庞大神仙体系中,并没有出现太阳神,但却在第七十二回中提及羿射落九日之事,书中说:“太阳星原贞有十,后被羿善开弓,射落九乌坠地,止存金乌一星,乃太阳之真火也。”乌巢禅师是否与“太阳星”或坠地“九乌”有关,作品没有交代。但佛教典籍中却有将太阳称为“乌巢”的记载,如《物初大观禅师语录》有“休论凤箭射乌巢,看取虚弓落九包。收放若为逃羿手,控弦傍助亦徒劳”之语,其中就将羿所射的太阳称为“乌巢”。由此看来,《西游记》在书中设计的这位乌巢禅师实际上是扮演着真理护卫者的角色,他在路上传给唐僧的《心经》,实际上就是唐僧战胜千难万险的精神动力,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乌鸦捍卫理想、太阳神指引人类走向光明大道的主旨是一致的。《西游记》虽是小说家之言,但它融汇多种文化知识,广建诸神谱系,同时也吸收了民间故事及神话传说中的诸多元素。书中所涉神怪遍及天上、地下、人间、海岛,却独独缺少了从上古流传至今能引导人们走向光明和真理的太阳神,如果我们以为这是作者的疏漏,显然是不太合情理的。事实上,作者早已在书中安排了一位乌巢禅师,或明或暗地一直指引着唐僧西行的光明之路。所以,乌巢禅师这一形象的设立绝不是《西游记》作者的无意之举。
结语
从以上对乌巢禅师这一形象的文化追索中可以看出,《西游记》立意绝不仅仅在于为读者讲述一些老妪能解的故事传说,更重要的是在那些表面奇幻或滑稽的故事中隐含深刻的历史文化信息,以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诉求。只有了解了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发展以及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的文化趋势,我们才能理解《西游记》对儒、释、道及中国民间文化各有所取,而又对其不断加工、整合的历史文化特征。这又一次印证了《西游记》不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部不朽之作。
注:
⑤[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⑥[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第2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6页。
⑦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影印,第86、87-88页。
⑩程毅中先生认为,《独异志》里传授《心经》的老僧是一个“胡僧”。见程毅中《〈心经〉与心猿》,《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