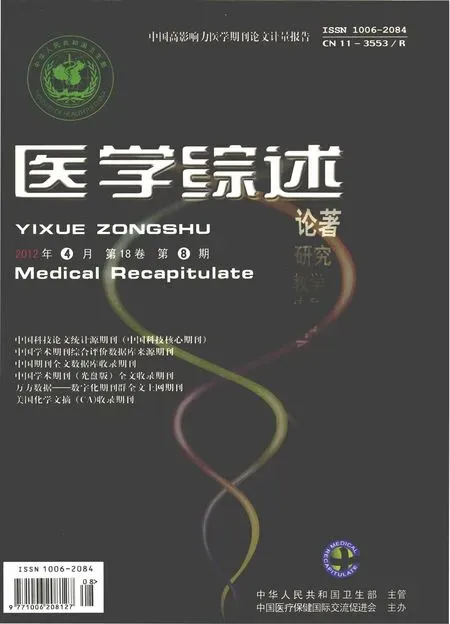脑卒中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健康状况和干预方法研究进展
2012-12-09徐世海综述审校
徐世海(综述),王 凯(审校)
(1.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人民医院康复科,新疆喀什843800;上海市静安老年医院康复科,上海200040)
脑卒中从病死率和致残率来说,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健康问题,在未来的20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脑卒中有增长的趋势。随着急诊医疗水平的提高,许多脑卒中患者生存了下来,但常伴有躯体和认知功能障碍,如肢体痉挛、认知和行为障碍、抑郁、尿失禁等,被家庭照顾者需要长期的照料,导致巨大的社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约150万人,幸存者为500万~600万人。其中有70%~80%遗留不同程度的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者高达42.3%[1]。香港地区的一项研究中显示,脑卒中后3个月仅有46%的患者基本生活能独立,1年后超过50%以上的患者生活需要依赖[2]。在美国每年约有75万美国人有新发或复发卒中,平均每5个美国人有4个受到卒中的影响,在加拿大约1/8成人在社区从事各种老人慢性病的照顾,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情况也类似[3]。由于脑卒中恢复慢,家属为控制医疗支出,必须缩短住院康复治疗的时间,增加了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护理工作。对于脑卒中的家庭照顾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照顾患者的过程中,由于过度的体力透支、社会活动受限而导致健康状况下降,如身心健康下降,生活质量降低等,研究显示当照顾者出现健康问题,患者的康复过程也会受到影响[4]。所以要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必须考虑家庭照顾者的健康状况。
1 照顾者的健康状况
脑卒中恢复过程为突然发病,急诊住院,康复治疗,然后社区生活。患者的康复需长期的日常生活帮助、情感支持、经济援助等。在国内,由于缺乏社区康复中心、日间照顾等服务机构,患者出院后主要回归家庭,对此家属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患者回家后生活活动常发生困难,并持续多年,他们需要大量的照顾,通常家属很少准备承担照顾者的角色,如不能适当地作出调整和寻求支持,就会成为潜在的患者。在早期他们通常表现为焦虑、疲劳、无助,需适应和情感支持。长期工作受影响,收入下降,部分照顾者干脆放弃了工作[5]。据统计,家庭照顾者的80%来自亲属,72%来自女性,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女性照顾者常处于被动角色,传统道德限制了她们表达需求和寻找帮助,常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感觉有义务承担,另一方面希望能摆脱这种负担。妻子作为照顾者,对婚姻的幸福感下降[6]。老年女性照顾者有更多的问题,长期护理患者会影响她们的健康,甚至影响家庭照顾的维系[7]。脑卒中后患者如有认知障碍,他们在家的活动空间很小,生活质量很差,家庭照顾者指导患者从事日常生活活动非常困难,常导致焦虑、抑郁和孤独感[8]。研究发现,照顾者感觉过度的负担、抑郁和孤独,对生理上也产生不良影响,如自我健康状态不良,多有心血管疾病等[9]。Chen等[10]研究了香港脑卒中的家庭照顾者,发现家庭照顾者的抑郁状况对他们本身生活质量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发现,随着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的提高,照顾者的抑郁等不良心理状况会减轻[11]。
2 照顾者的需求
脑卒中患者回家后会处于活动能力下降、跌倒后损伤等危险状态,家属作为自然照顾者,并未做好准备,所以出院前了解照顾者的需求,对他们进行培训,掌握康复护理技巧,对照顾者适应新角色,维持他们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认为医务人员对家庭照顾者的教育是不足的,方法需要进一步提高[12]。Hafsteinsdóttir等[9]系统回顾了 2009 年前发表的21篇有关患者和照顾者教育需求的研究论文,发现患者和照顾者在不同治疗和康复阶段有不同的多种教育需求,常得不到满足。患者和照顾者均希望了解脑卒中的诱因、症状、治疗、恢复情况。照顾者最基本的教育需求是有关患者身体上的照顾、移动、锻炼、心理方面的问题(如抑郁),以及营养问题,他们均希望同时得到书面资料,他们还希望能在不同康复阶段采取针对性的个体教育。Sue等[13]对70位香港家庭照顾者,在家中对脑卒中患者进行了3个月的看护后,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家庭照顾者整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和他们的抑郁及健康状态高度相关。提示医护人员应注意脑卒中的护理技能教育,提高照顾者的问题解决能力,继而提高他们的健康状况。张华等[14]对62位脑卒中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进行家庭入户问卷调查,发现居家康复的脑卒中患者遗留有多种功能障碍,缺乏家庭康复训练,家庭设施未行相应改造,患者的综合自理能力及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能力均较差,因此应加强家庭康复护理教育指导工作。许多研究还发现[15],为家庭照顾者提供脑卒中康复的知识有助于提高患者和照顾者的健康,教育有利于照顾者对脑卒中患者康复过程进行正确的管理,预防再次脑卒中,缺乏教育使照顾者误解、焦虑、抑郁、健康状况下降等问题。目前在患者康复出院前对照顾者的评价常被忽略,如能在出院前对照顾者的文化程度、技能进行评价,就能帮助康复小组制订针对性的出院治疗和教育计划,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和照顾者的健康状况[16]。
3 干预措施
国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包括减轻家属照顾者的负担和压力,提高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方法。研究包括信息提供(疾病知识、服务资源)、指导(帮助训练、日常生活、社区服务)、情感(心理疏通、倾听问题)、鼓励(正确护理的反馈)等方面,但结论不一,认为需扩大研究[17]。White 等[18]介绍了认知障碍的照顾者利用在线的邮件组发布和寻找信息、分享经验和意见,提供鼓励。Finn[19]发现,互帮小组重点工作放在患者功能损害问题,强调相互问题解决;信息分享,表达感受,支持和同情,证明了网络系统能对家庭脑卒中照顾者进行支持和教育,家庭网上可作为一种对脑卒中照顾者追踪护理、继续支持和治疗的补充手段,特别是对于高度需求但缺乏条件(有限的时间,地理位置,交通限制,缺乏照顾替代者)尤其有价值。Réjean等[20]在加拿大魁北克对158位脑卒中痴呆照顾者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通过对研究组照顾者15周,每周2 h的医学知识教育,识别患者症状和行为,指导处理方法,寻求社会支持;结果研究组照顾者对患者异常行为处理能力增加,心理压力减轻。闵凡云[21]将112例住院脑卒中患者和家属照顾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试验组照顾者按健康教育路径模式进行健康教育,分入院阶段、康复阶段、出院指导,结果试验组照顾者对疾病相关知识、康复护理知识掌握情况、住院满意度调查满意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也显著低于对照组。随访3个月后,试验组患者运动功能评分及Barthel指数评定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王丽等[22]采用纽曼健康系统模式的三级预防措施,对118住院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压力进行干预,一级预防使主要照顾者获取脑卒中疾病相关知识和压力防御知识,提高照护患者的能力和应对压力的能力,机体出现压力反应时,启动二级预防措施,结果照顾者减少接触压力源,正确面对压力,减轻压力反应,维护自身健康,更好地投入到家庭照顾中。
4 提高干预效果的进一步设想
目前对脑卒中患者照顾者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效果不一。一些学者在总结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干预模式。①适时干预模式:Cameron等[23]提出,根据脑卒中康复5个时期,照顾者的不同需求,适时地对照顾者采取不同的支持和教育,使患者的康复治疗得到延续,减轻了家庭照顾者的负担。急性突发期:家属重点关注患者的健康状况和治疗,医师尽可能给家属进行脑卒中及功能损害知识宣讲,在卒中发生时及以后的治疗程序,也可通过书面的形式介绍。稳定期:照顾者经常询问卒中后存留的躯体和认知功能和精神状态,想了解患者可能的恢复程度。准备期:面临出院时,家属非常想了解医学信息和接受培训,继续学习照顾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技巧,家属照顾者需要来自社会、家庭、朋友的支持。实施期:患者开始学习怎样适应在家庭环境中生活。家属在家里边试边学护理活动。家属在帮助患者转移、实施预防复发措施(药物、饮食控制、生活习惯)时会感觉困难,在情感上因力不从心会感觉迷惑和焦虑。开始考虑由于长期照顾患者而带来自身的不良后果,如情感、躯体功能、社会参与。适应期:患者的能力有所提高并趋于稳定,家属照顾者的重点常转移到帮助患者参与有意义的社区活动和休闲活动,更加重视从事社区康复和护理以来的自身结果。②案例管理模式:Lutz等[24]提出这种模式,包括了患者出院前的家庭评估、患者出院后的治疗需求、家庭照顾者的教育、支持需求,需要机构提供的服务,使患者成功地、无缝隙地从医院回到家里。首先,对家庭照顾者进行一次出院前的全面评估,了解照顾者的能力、技术,能否满足患者出院后的照顾需求;然后,基于评估,提供高度个体化的案例管理计划,帮助照顾者获取所需技术,提供必要的服务;最后,出院后进行随访,技术指导和咨询,通过网站、电话,个体化地满足照顾者的需求。
5 结语
我国脑卒中人数为世界第一,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可以预测未来家庭照顾者需求量会同步剧增,家庭照顾者的健康问题会显得越来越突出。由于文化背景和医疗体制不同,国内家庭照顾者的健康状况和国外相比很可能不一,然而国内康复界在该领域研究得较少,缺乏大量调查和前瞻性干预方面的研究,仅有护理方面的一些报道,因此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1]黎明.内科护理学[M].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607.
[2]Lo RS,Cheng JO,Wong EM,et al.Handicap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change in stroke survivors:one-year follow up study[J].Stroke,39(1):148-153.
[3]Sussman T.The influence of service factors on spousal caregivers'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services[J].J Gerontol Soc Work,2009,52(4):406-422.
[4]Visser-Meily A,Post M,Gorter JW,et al.Rehabilit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need a family-centred approach[J].Disabil Rehabil,2006,28(24):1557-1561.
[5]Norris VK,Stephens MA,Kinney JM.The impact of family interactions on recovery from stroke:help or hindrance?[J].Gerontologist,1990,30(4):535-542.
[6]Enterlante TM,Ken JM.Wive'reported role changes following a husband's stroke:a pilot study[J].Rehabil Nurs,1995,20(3):155-160.
[7]Kao HF,McHugh ML.The role of caregiver gender and caregiver burden in nursing home placements for elderly Taiwanese survivors of stroke[J].Res Nurs Health,2004,27(2):121-134.
[8]Ory M G,Yee JY,Tennstedt SL,et al.The extent and impact of dementia care:Unique challenges experienced by family caregivers[M].New York:Springer,2000:1-32.
[9]Hafsteinsdóttir TB,Vergunst M,Lindeman E,et al.Educational needs of patients with a stroke and their caregivers: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Patient Educ Couns,2011,85(1):14-25.
[10]Chen Y,Lu J,Wong KS,et al.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amily caregivers of stroke survivors[J].Int J Rehabil Res,2010,33(3):232-237.
[11]King RB,Carlson CE,Shade-Zeldow Y,et al.Heinemann AW.Transition to home care after stroke:depression,physical health,and adaptive processes in support persons[J].Res Nurs Health,2001,24(4):307-323.
[12]Rodgers H,Bond S,Curless R.Inadequacies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o strok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J].Age Ageing,2001,30(2):129-133.
[13]Sue Y,May HL,Fiona R.Family carers in stroke ca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solving,depression and general health[J].J Clin Nurs,2007,16(2):344-352.
[14]张华,冯正仪,胡永善.社区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现状调查分析[J].中国临床康复,2002,7(6):949-950.
[15]Smith J,Forster A,House A,et al.Information provision for stroke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J].Clin Rehabil,2009,23(3):195-206.
[16]Lutz BJ.Determinants of discharge destination for stroke patients[J].Rehabil Nurs,2004,29(5):154-163.
[17]Sorensen S,Pinquart M,Duberstein P.How effective are interventions with caregivers?An updated meta-analysis[J].Gerontologist,2002,42(3):356-372.
[18]White M,Dorman S.Online support for caregivers:analysis of an Intern et Al zheimer mailgroup[J].Comput Nurs,2000,18(4):168-179.
[19]Finn J.An exploration of helping processes in an online self-help group focusing on issues of disability[J].Health Soc Work,1999,24(3):220-231.
[20]Réjean H,Louise L,Jean V,et al.Eficacy of a psychoeducative group program for caregivers of demented persons living at home: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2003,58B(1):58-67.
[21]闵凡云.脑卒中照顾者健康教育路径的设计与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09,15(21):25-27.
[22]王丽,亢巧玲.纽曼健康系统模式对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压力的影响[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9,6(7):15-17.
[23]Cameron JI,Gignac MA."Timing it Right":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the support needs of family caregivers to stroke survivors from the hospital to the home[J].Patient Educ Couns,2008,70(3):305-314.
[24]Lutz BJ,Young ME.Rethink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stroke family caregiving[J].Rehabil Nurs,2010,35(4):15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