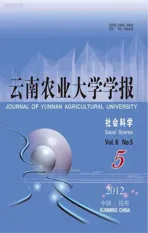唐宋之际的文学功能观
2012-12-08陈毓文
陈毓文
(闽江学院 中文系,福建 福州 350011)
2012-06-18
2012-07-21 网络出版时间:2012-9-29 15:43
陈毓文(1973-),男,福建龙海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民间文学研究。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20929.1543.201205.114_052.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2, 6(5): 114-117
10.3969/j.issn.1004-390X(s).2012.05.025
唐宋之际的文学功能观
陈毓文
(闽江学院 中文系,福建 福州 350011)
唐宋之际的割据动乱引发了社会心理的变迁,注重实用、追求享乐、逃避现实等心理成为时代主旋。文学功能亦随之发生改变,实用交际、娱乐、审美等功能取代了传统的政教功能。文学功能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此期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艺术风貌等方面,宋型文学的一些基本质素也在此期逐渐形成。
唐宋之际;文学功能;实用交际;娱乐;审美
唐宋之际①本文对唐宋之际的时间界定主要从文学自身发展的一贯性考虑,将唐昭宗朝至宋真宗朝之前(889~998)这一段时间(即传统意义上的唐末五代宋初)纳入考察范围。,儒学衰坠,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关注反映现实的传统政教功能在注重实用、追求享乐、逃避现实等时代心理的作用下逐渐弱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交际、娱乐、审美等功能。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艺术风貌等亦因之而变。在唐宋文学转型中,此期文学担负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是我们认识文学由唐至宋转变的关键阶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此期文学功能观的变化,为进一步认识唐宋之间的文学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一、唱和之风与实用交际功能
唐末五代,各割据统治者大多为武将出身,需要的是实用型人才,五代科举亦以选拔实用人才为主。后唐长兴元年,翰林学士刘昫奏请停试对治理国家没太大用处的诗赋[1]。天福五年,礼部侍郎也奏请停废明经、童子两科,盖因明经科举子“多不究义,惟攻帖书,文理既不甚通”,童子科“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2]。在科举导向影响下,讲究实用日益成为一种普遍心理。而时代动乱所带来的家人、朋友天各一方、生死相隔的痛苦也使得诗歌适时充当起承载亲情、友情的重任。文人之间以诗酬唱赠和,传递心声。可以这么认为,唱和诗在五代时期的大量出现,是此期文学实用交际功能的最直接体现,它已经广泛渗透于士大夫生活之中。
唱和风气在唐代已颇盛行,尤其是中唐以后,唱和之风更是大兴。以白居易与韩愈为中心构成的两大唱和群落,几乎涉及当时所有著名文人。晚唐时期,在苏州有皮陆唱和;在襄阳有段成式、温庭皓、韦蟾等人的唱和;在成都,有李珪、郭圆、来择、薛重等人的唱和。进入五代,唱和则已扩大成为一种时代行为。不分地域南北,也不分地位贵贱,上至君王大臣,下至一般下层文人,莫不唱和。北方有后唐秦王李从荣与幕客高辇等人的唱和。南方除了文学较盛的西蜀、南唐唱和文人群外,楚地有徐仲雅与湖湘诗人的唱和。就连当时地处偏远的闽地,也有黄滔与翁承赞等闽瓯诗人的相互唱和。在这些唱和群体中,南唐唱和最有代表性。其唱和活动主要集中在五代后期。元宗、后主本为儒雅文人,南唐又人才济济,唱和风气相当兴盛。尽管五代战乱,文献丢失甚巨,但现存五代诗歌仍有七千多首,从中可以推测当时诗歌创作的兴盛局面。虽然这种兴盛并没有带来其相应的文学地位。诚如后人所评,五代诗歌成就普遍不高。但这与五代时代背景有关,与当时文人知识水平不高有关,而占据了五代诗歌相当数量的唱和诗,也应是其中原因之一。深受白居易影响的五代文人发展了元白唱和诗的写作手法,追求平易的诗风,不管大事小事,叙事议论,都用诗来表达。因此唱和诗的盛行,对于诗歌的进一步日常生活化有着一定意义。可惜多数为平庸之作,诗歌前进的步伐非常缓慢。
另一方面,唱和诗创作中文人之间在艺术手法上的争奇斗巧也对宋诗特色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随着割据局面的出现,文人大量集中于各割据政权之中。各割据统治者一方面需要这些幕府文人为其处理政事,同时也有与其他统治者争胜的念头,即如赵翼所云“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3]。而就文人自身而言,割据的现实使很多友人分隔两地,只能采取酬赠寄答的方式表达内心情意。唱和诗不仅能满足这种需要,还能表现出自己的才华。正是在这种互相争胜的创作心理驱使下,唱和诗表现出浓厚的竞巧意识。在同一题下,文人们字斟句酌,旁征博引,使事用典,务求超过原唱,表现出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当然,这一倾向自中唐以来就已出现,元白唱和已显示出夸多斗靡,因难见巧的创作心理,晚唐皮陆之间的唱和更是争奇斗巧。到了五代时期,唱和诗则以其广布天下的巨大声势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潮,宋初的唱和诗即顺承这一走向,并在西昆体中发挥到极致。杨刘等西昆作家“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抱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刘筠尤注重“初学记”[4],杨亿则专门搜检故事出处,用小纸片录出,以备作诗文时填用方便。而且宋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均成书于北宋前期,更是为这种作诗法提供了方便。欧阳修就对此作出评价:“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5]西昆唱和乃是翰林大臣们编写《册府元龟》之余的消遣活动,其实用交际功能固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之中,西昆诗人所表现出的对语词雕琢和华丽的共同追求又隐含着改变诗风的革新意识,是以“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从而揭开了宋诗自立面目的序幕。
二、享乐之风与娱乐功能
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是儒家传统的观念。然而唐末五代儒学的崩溃,却使这一传统失去了落脚之处。承继中唐以来世俗化的浪潮,咸通以后,随着末世的来临,及时行乐的思潮蔚然成风。懿宗、昭宗时期,朝野上下忙于宴饮与冶游,表现出了追求声色之好的共同目标。享乐主义成为时代的风气。另一方面,儒学一尊的局面被打破,各种思潮应运而生。传统的情志观发生分化,志被削弱,情得到了张扬。咸通乾符年间,诗坛上弥漫着一股香艳之风,即所谓“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6]。男女艳情成为重要题材。韩偓在《香奁集》序中就明言其艳诗之写作乃不能忘情。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在当时较为稳定的西蜀、南唐地区,文学的娱乐功为多数文人自觉接受。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西蜀文学。阻隔了战乱的闭塞的地理条件、安逸的社会环境、不思进取的西蜀君臣共同促成了西蜀地区浮靡享乐的社会风潮,如前蜀后主王衍,“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7]。后蜀后主孟昶出游浣花溪,则是“帝游浣花溪,御龙舟观水嬉。时百姓饶富,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罗绮,名花异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7]。上行下效,文学的娱乐功能在西蜀成为主流:“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王衍《醉妆词》)[8],词成为满足享乐需要的载体。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也倡言词之用途乃在于:“用助娇娆之态”、“用资羽盖之欢”[9]。
南唐的文学功能观与西蜀有相似之处。李昪建立南唐后就着手设置教坊,专掌乐事。到李璟入主东宫后,“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10]。南唐地区的歌舞娱乐事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李煜,更是大展教坊,广开第宅,南唐亦因此多奢侈浮糜之风,如《旧五代史》卷131《孙晟传》云:“晟以家妓甚众,每食不设食几,令众妓各执一食器,周侍于其侧,谓之‘肉台盘’”[2];马令《南唐书》卷22《刘承勋传》记其“家畜妓乐,迨百数人,每置一妓,费数百缗,而珠金服饰,亦各称此”[11];南唐文学的娱乐功能亦颇为突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政治环境、地理条件、创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南唐文人对文学的态度不仅仅停留于娱乐层面,还进一步表现出对政教与审美功能的重视。前者主要表现为以词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让词在一定程度上也担负起诗歌的职责,如《南唐近事》所记乐工杨花飞歌“南朝天子好风流”谏李璟之事[12];《江邻几杂志》亦记有韩熙载以“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谏李煜之事[12]。后者则以李煜为代表,以词作为抒写个人主观情思的载体,表现出对词的审美功能的关注。
宋初文坛构成以西蜀、南唐入宋文人为主,再加上宋初统治者对宴飨娱乐之风的提倡,文学的娱乐功能也顺利延传到宋初。杨亿就曾说《西昆集》的结撰是他在“忝佐修书之任”时,“得接群公之游”时所作,其目的不过是为了“雅饮欢娱洽”(《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雕章刻烛催”(杨亿《夜谦》)[13],满足无事可干之时娱乐的需要罢了。
三、苦吟之风与审美功能
在一片喧嚣与欢乐之余,在士大夫文人们忙于追求享乐与酬唱交际之余,还有一些文人们则默默地耕耘着,在诗歌中表达对人生,对生命的思索与回味。他们甘于淡泊,执着地探索文学创作的奥秘。然而正是在他们手中,完成了由注重思想内容的政教功能向关注诗歌本体的审美功能的转变。这一功能的转变,则源于唐末五代以来的苦吟之风*这一问题,学界已颇多成果,具体可参见吴在庆《略论唐代的苦吟诗风》(《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李定广《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时代的动乱给予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给文人们提供了一条逃避现实、回归内心的创作道路。尽管这种向内心的退缩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呈现为一种缓慢状态,而五代的动乱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使之成为一种时代心理。通过苦吟,暂时消解世事的纷扰,暂时忘怀人生的苦痛,化解愁闷,安顿心情。于是,苦吟就有了时代的意义,它所表现的是动乱时期人们对生存的艰难、创作的痛苦的深刻体会,以及从这一切当中所获得的一种对个体所付出一切的告慰。苦是一种对生命的感受,对生命的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苦吟诗人的诗歌创作已经有了一种回归诗歌本体的创作自觉。这可以从他们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上看出来。这方面例子很多,典型的如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苦吟》)[14]又如李洞,“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15]。这些苦吟诗人对待诗歌态度是极其认真的,甚至是一丝不苟。一方面,现实生活给这些文人带来的巨大苦痛,使他们自觉远离现实,逃避现实生活的种种困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自己构建的狭小世界中从诗歌创作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五代十国时期,苦吟诗人主要以隐逸诗人和诗僧为代表。他们的诗歌进一步表现出了对诗歌审美功能的体认。
五代时期的隐逸诗人主要集中在楚与南唐区域。楚有衡山处士廖融,逸人王玄、王正己、任鹄以及翁宏、伍彬、李韶、狄焕等皆以其为宗主。南唐则以隐居庐山紫霄峰下的陈沆、陈贶叔侄最为出名,他们子弟众多,黄损、熊皦、虚中都曾往师陈沆、陈贶,时士也多师事之,江为、刘洞为能得“二陈”真传的真正弟子。与刘洞并称的夏宝松则向江为学诗,且再授弟子。南唐曾入庐山国学的李中、伍乔等一群也多为此系传人,从而形成了师徒承传梯队,诗简往还,彼此影响。而当时学者之所以多取陈贶为法,其关键也在于他的诗深得贾岛之奇峭。这些隐逸诗人普遍以贾岛为师法对象,潜心于诗歌技法。平和宁静的创作心态使他们的诗歌表现出一种清新淡雅的艺术风格。如王贞白于天复元年归隐永丰,“笃志于诗,清润典雅”[15];张乔隐居九华,十年不窥园,“诗句清雅,迥少其伦”[15];崔鲁诗“善于状景咏物,读之如嚥冰雪,心爽神怡,能远声病,气象清楚,格调且高,中间有一种风情,佳作也”[16]等都表现出了对清雅风格的追求。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则从理论层面表达了对清丽诗风的企慕,盛赞王维与韦应物的诗“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6]。韦庄编选《又玄集》也通过对清丽诗风的肯定来表现一种淡泊的主体情致,这是五代时期对诗美追求的具体体现,尽管这一审美功能与当时占据主流的娱乐、交际功能相背,但却反映了五代人对盛唐诗歌的一种追慕。
诗僧群体则是五代时期一独特的文学群落,正如孙昌武先生所说,他们是“披着袈裟的诗人”[17]虽然身在空门,却没有一丝僧人的意味,而是混迹于世俗之中。贯休、齐己、尚颜、虚中、栖白、栖蟾、栖一、处默、修睦、可朋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诗僧对原本就是僧人的贾岛有着难以言明的好感。再加上自身为僧的身份,更容易走上贾岛诡奇入僻的创作道路,而同属韩孟诗派的李贺诗中那怪异瑰丽的创作风格同样也引起僧人的共鸣。他们对诗的态度同样是非常认真的,甚至把诗比作“经天纬地物”(贯休《诗》)[14],把诗作为一种人生追求,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余生终此道,万事尽浮云”(齐己《寄南徐刘员外二首》)[14]、“诸机忘尽未忘诗,似向诗中有所依”(尚颜《自纪》)[14]。不仅如此,这些僧人还热衷于对诗艺的探讨,现存诗格类作品就多为诗僧所作,如齐己《风骚旨格》、虚中《流类手鉴》、神彧《诗格》、保暹《处囊诀》等。他们努力探讨诗与禅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变了当时处在主流地位的对外在的交际、娱乐功能的追求而进入到更为内在的对“文外之旨”的探讨。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18]然此三体之形成明显与五代时期有着沿承关系。唱和诗、闲适诗、隐逸诗的盛行表明,文学的实用交际、娱乐、审美功能在宋初仍在发挥作用。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如何重新树立文学政教功能的主导地位,也就成了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任务所在。
[1][宋]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M].北京:中国书店,1987.
[4][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 [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清]董诰等编.全唐文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清]吴任臣.十国春秋 [M]//傅璇琮,徐海荣,等.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8] 曾昭岷.全唐五代词 [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 [M]//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五代]郑文宝.南唐近事 [M]//傅璇琮,徐海荣,等.五代史书汇编.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1][宋]马令.南唐书 [M]//傅璇琮,徐海荣,等.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宋]杨亿.西昆酬唱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清]彭定求.全唐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 [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18][宋]方回.桐江续集 [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OntheFunctionofLiteraturebetweenTangandSongDynasties
CHEN Yu-wen
(Chinese Department,Min Jiang College, Fuzhou 3501081,China)
Turmoil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ed to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times,especially amusement,comfort,and practical utili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Which ref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is mainly for the changes of literary functions,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recreational and aesthetic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unctions. This chang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face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entertainment; aesthetic
I 206.2
A
1004-390X(2012)05-01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