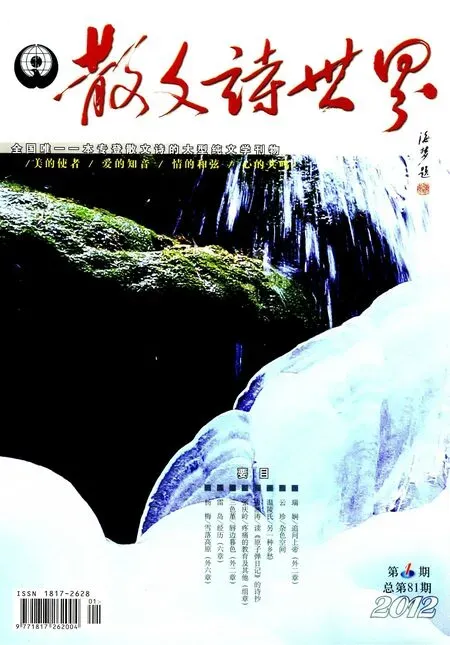散文诗四章
2012-11-24安徽钱钟龄
安徽 钱钟龄
一根断裂的树枝
在老家的院子里,我无意中踩折了一根树枝,啪的一声碎响,像大地上断裂的一根骨头。泥土不愿埋葬它,想必它终究会成为泥土的一部分。它不是火焰,也不是一块炭,只是乡村安宁的一截朽木,在彻底腐朽之前,终于有人听到了它爆发的音乐。
那肯定不是生命的绝响。
也许,它会被母亲拾起,放在灶膛里。——它还会跳火辣辣的热舞。
也许,它还会被顽皮的孩童抛在空中。——它像一只鸟一样作短暂而美妙的跳跃。
也许……
总之,它还是有生命的,只不过它将心中的森林藏在枯瘦的外表下,将心中的蔚蓝藏在身上的尘埃里。
它的每一条枯死的茎脉,都凝固有风雨雷电。
你见过固态的风、雨、雷、电吗?没有,肯定没有。
但它实实在在地写出了村庄浓缩的历史和风暴。它和踩裂它的人都是历史和风暴里的一粒历史和风暴。
冬 树
冬树像人一样,分化不可避免。一部分颓废,只剩 露的脊梁,只有大雪来时才能证明它的清白;另一部分仍然葱葱郁郁,坚守思想的绿,它们在严寒中修炼自己。
绿是大时代的趋势和必然。
街道上的冬青树、香樟、广玉兰,院子里的柑橘树等等都是绿的代表,城市的建设者们赋予它们代表的资格。
它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它们会认真地聆听鸟儿的倾诉,必要时会赠送它们安详的鸟巢。
它们会和环卫工人一起,打扫天下。一个清扫地面,一个清扫天空。
它们当中也会掉下几枚枯叶,那是甩掉陈旧的理念或包袱。它们轻装上阵,在沧桑里匆匆赶路。有时,它们也惊鸿一瞥,那是夕阳的光辉。
橘子树还背负着一袋袋行囊,在疲乏时就会取出一瓣瓣酸甜的月光。让橙色的风暴融入白色的风暴里。
这是温暖而宁静的风暴。
冬树,伸出的枝枝桠桠是街道的一部分,挤满着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就像它的叶儿,密密麻麻地结在枝头。
有一些树最终会枯萎、死亡,会有另一些及时填补大地的空虚。
一朵枯萎的腊梅
在幽深的小巷,我忍不住偷摘了一朵,把芳香带到办公室。我注视着它黄色的花瓣,像透明的聚拢起来的一片心思。
像浓缩的一页历史,今天被我悬挂在我的枝头;明天,我将像它一样,被别人挂在沉寂的枝桠上。也许我只是一枚浸透了春秋的叶,只有透明,没有芬芳。但并不妨碍,我和它都是天地间的一束火焰。
大雪还未到。
未到之前,它是温暖的雪。
一粒在血液里不会融化的雪。
枯萎了仍然是最纯洁的雪。
它是苍茫世界里被镶嵌在疤痕或疼痛里的一道神经,与宇宙相连、天地相连、人生相连。
勾勒出生命的线条和色彩。
它像鹰的眼睛,击碎冬天巨大的虚空。
它不能在高空盘旋,但它站在一个高度收集盘旋者孤傲的足迹。
它是水做的骨头,将柔情藏在内核。
暗香溢出在外面,你无法控制。
现在它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它枯萎了,仍然会有芬芳的气息。
我承让我是这场血案的制造者。
但它不会就此死亡。
有时死亡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灵魂。
冬日的鸟鸣
冬日的鸟鸣在形式上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本质上更清澈、更晶莹,像冰里流窜的音乐,寒冷囚禁不了它。有时是一粒、二粒,更多的时候无数粒音符拥挤在一起赶集,热闹而温暖。
叠加的鸟鸣像叠加的果实,我想象它是一串串葡萄,挂在天空深邃的枝头,成为云朵的口粮。
不自觉地你走进去,走到天地舒展的枝头,你也成了枝头的鸟鸣。你在歌唱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歌唱。
你也是一株在尘世奔跑的植物,严寒不可避免地将你理想的叶儿一片片剥离,扔给你一枝枝黑漆漆的孤独。这时,有一只、二只鸟停在你的枝桠,就会像结在你身体上的炭。
大雪会把它点燃。
燃烧到极致时,没有灰烬,只有透明的韵脚。
鸟走时,还会留下飞翔的芽尖。
每株植物都会枯败,就像人会衰老。
要及时搬走体内的腐朽,让西风掏空树洞里不合时宜的词汇。
把新鲜的鸟鸣灌进去,让浑浊的身体不在沉寂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