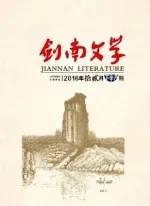收 藏
2012-11-02吴嘉明
◆ 吴嘉明

七月流火,知暑渐退而秋将至。
本该是渐凉的天气,却依旧炎热异常,坐在家里百无聊赖地翻看着前几年的各种文字各种心情,有了一种忽然恍如隔世的感觉。前几年我讲过的Bill,曾经那么刻骨铭心地留下那些痕迹,如今的他却已去了成都上学,选择了一个他自己不怎么喜欢的学校依旧执着地追求音乐事业,同学录上去北京的豪言壮语,业已渐行渐远终不可闻。现在我们早已失了联系,即使知道对方的联系方式,即使是翻开手机电话薄,也很难再去开口说些什么。偶尔还能在QQ上看到他,看看他的新动态,随便地寒暄寒暄。可毕竟彼此再不是当年印象中飞扬跋扈无话不谈的少年,所以那些在《瓦解》中遗失的时光和梦想,青涩和不羁,渐渐变得遥不可及,如同被收藏的默片,轻易就扯开相关回忆,却变成虚无难以寻觅。
天气终于没有如我所料的那样,一天一天凉爽,温度如同小孩发烧的脸不肯褪去。快要返校的时候看到了包子,牵着他可爱的女友漫步在河边,谈笑间只是觉得那段和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愤青的时光变得有些悠长而遥远,不经意间自己居然离开母校快三年了。三年,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有谁道过,谁有牵起了谁的手,谁有背弃了当初的承诺,谁还驻足在那儿成为你的过往纪年。
只是一种怀念,怀念当年他们的笑靥,怀念傲颜在老旧的笔记本中写下的——有一天,你说会站在光阴的尽头等我,是自己给自己的承诺,还是你又在骗我,那么不知死活。
这一切都无关现实,抑或是折射出来的梦想。站在二十岁出头的转折点上,看着所有年少的记忆都渐渐被时间过滤成一种劣拙的文字,一种不复再有的冲动,一种尖锐的狂妄,以及莫名混乱的信仰,终于明白,那一种坐在麦地里无知地唱着笑着哭着闹着根本不去在意前途未卜的生活,渐渐变成坐井观天的浮夸,最后终于留在象牙塔里面,变成无人喝彩的踽踽独行。
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十字路口迷路、徘徊,曾以为迷途只是暂时的,但时至今日却依旧如此迷茫。以前以为无知只是因为年纪尚小而阅历不足,现今走过更多路见过更多事只是觉得自己愈发无知愈发迷惘。正如《海上钢琴师》里面的蒂姆·罗思仰起平静的脸说的:“我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在一个找不到尽头的世界生活,我之所以走到一半停下来,不是因为我所能见,而是我所不见……”这个世界,终是难以触及到它的一隅,尽管它广阔无比。而所谓远方,不过是诗意化的一种自我救赎罢了。现在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忽然想起白岩松说,一个人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一个人的战争。
所以我明白一直以来,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即使兵荒马乱,天翻地覆。
当自己还在感慨十八岁的复杂心情,自嘲着二十岁的挣扎劳顿时,二十一岁快要来到却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亲人渐渐老去,朋友的徐徐改变,找工作的窘境,房价的居高不下,社会的深不可测……目睹着未来以一种完全陌生的姿态正在逐渐靠近,内心连惶恐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前所未有的迷惘填满。
转眼间已是一个有关毕业和新生的季节,站在属于大二的窗台上,往往能看见许多大一新生从眼前走过,脸上笑容足够生动,洋溢着他们刚刚结束高三生活后那种满怀希冀憧憬的味道。我默不作声地转头,又是老社长和学长学姐们离开时潇洒却有点伤感的背影,就这样眼见着老故事一轮又一轮地重演着。我无话可说,只好穿过他们的笑容,穿过他们的落寞,一声不吭地。这时的我早不是少年,那时的Bill不曾离去;亦不是最苦的蜕变时刻,傲颜和Jordan始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能了解那种无可诉说的寂寞。
闲来无事把旧片翻出来翻来翻去的看,再一次看了《阿甘正传》,依旧无限唏嘘。奔跑的孩子跑过他的少年,青年,中年,背景是那个疯狂的年代,越战、总统遇刺、乒乓外交、水门事件……我实在无法想象当时已近四十岁的汤姆汉克斯是如何把这个永远长不大的阿甘诠释得如斯惟妙惟肖。我们看着阿甘没有目的地奔跑——跑过农场,跑过球场,跑过战场,直至跑过大半个美国。直至影片结尾,他仍旧没有弄明白,是如珍妮所说,不断地奔跑,不断地反抗,命运才得以扭转;还是如母亲所说,“人生就像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种。”最后阿甘略带忧伤略带沧桑地在珍妮墓前说道:我不懂我们是否有着各自的命运,还是只是到处随风飘荡——我不知道你们谁说得对。那一刻开始,阿甘不再是孩子,为了残酷的成长,以过往、青春,以曾经爱过的和被爱的,为代价。
再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捣鼓那些文字,周遭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包围着,生活上的,学习中的,社团里的……林林总总的一大堆。曾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经过平淡的小学毛躁的初中嚣张的高中的自己有无数可以自视甚高的资本,却不知自己就像一只在原地自娱自乐,沐猴而冠。现在想想当年拿着笔在课堂上在老师的眼底下默默写着或者迎着成绩上的红灯而毫不在乎地奋笔疾书的那段岁月,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小天地,那种感觉未尝不是一种卑微的幸福。
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认真地去和他们讨论尼采萨特加缪,却总是被说成不务正业或换来无数白眼;晚上躺在床上发疯似的去给所有认识的人发短信诉说白天不敢倾诉的思想,得到的回复却是冷冰冰的不能理解,然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另一个不被读懂的世界。尽管如此,我能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总是浮现起生命中未有过的鲜活感。
那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阅历,弥足珍贵的经历——我深深地了然。
时至今日我依旧非常熟悉那种美好的感觉。抑或是怀念,是的,怀念。
只是许嵩在唱,我怀念,别怀念,怀念也回不到从前。
这两天收拾以前的一些旧书旧报纸,翻箱倒柜之余,居然发现了Bill送我的理想国。那是在初三的时候,一个没有征兆的早上,我在铃声的余音中狂奔进了教室,还来不及歇一口气,就发现面前递过来一个口袋。我抬起头,Bill的笑脸在初夏的阳光下镀上一层浅浅的明亮。我接过口袋打开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它的扉页上,这样写着——这是我的理想国度,这里有快乐,幸福,以及我们所希望的一切。
只是依稀记得当时是怎样一种欣喜和愉悦,却不知道往后会有怎样的痛苦。
那是Bill送我的第一本书,也是临走之前,送我的最后一本书。
我难过到无以复加,那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随着Bill的离开,演绎得愈发强烈。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孩子,可以互诉衷肠,可以相互取暖,可以相濡以沫。再不会有。
Bill。
现在我坐在大学的课堂上,抬头就会看见窗外碧空如洗或是乌云阴霾,偶尔的抬头还有飞鸟的翅膀啪啪作响。耳朵里塞着耳机,手中拿着一本村上春树或者冯友兰。总是很容易的,记忆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侧头仿佛就看到Bill拿着它走之前送给我的那本厚厚的《理想国》,缓慢而虔诚地诵读着其中的的片段,不时地抬起头来对我微微一笑;转身傲颜就在一旁,头微微倾斜地写着那些明亮鲜活的文字,姿态安静动人;SU又凑了过来,兴奋地向我讲诉沧月,古龙和海子……尽管我是那么地明白,每一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离开,离开那段记忆,虽然他们依旧以各种方式各种姿态出现在我的身边;正如我蹲在角落,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离开时映在回忆中隐隐约约的背影与陷在梦中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任凭大雪铺天盖地。
正如Jordan所说,这个世界,其实是温暖的灰烬。我的文字总是在反抗所谓世界的冰冷,而这冰冷,却源于我自己的想象。
两年前我不赞同她的这段话,只是觉得她一定和我有过类似经历和感触;两年后的今天我才深深了然,世界曾经温暖,我们的心却开始黯然。
Bill以前总是说我性格脆弱,如同骨子里蛰伏着一个悲观的哲人,令人担忧心疼。我完全能够想起有一次Bill忽然问我,如果他有一天离开了我我会怎样。我说我会坚强起来给你看,然后Bill就一字一顿地,在屏幕上敲出来三个字——“我不信”。当时只是觉得Bill对我太没信心,抑或是低估了我的决心,而在很久很久以后蓦然发现当时不够成熟的还是自己。轻轻的三个字如同匕首般锋利,那么轻易地刺进心里,令自己猝不及防,深深地哀伤。是不是一定要在他和他们离我远去以后,很久很久,才会懂得那些欲言又止的心情,才知道自己如此不堪一击。世界是温暖的灰烬,我转过头来,终于开始明白,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充满太多幻想和奢望,一旦破灭就会对其失望,开始认为这世界冷漠,正如我们以同样的冷漠姿态去面对她一样。
尽管这世界只是一片灰烬,可其中残留的温暖依旧值得我们去收藏,去寻觅。
于是我明白,仅此而已。
所以兰波说,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她。
昨夜父亲打来电话,告诉我外公去世的消息,我翻着手机上几个月前挚友父亲因事故不幸离去的短信,又想起过年的时候精神头还不错的外公那洪亮的嗓门,久久不能自已。第一次深深地意识到到无常和死亡到底是离自己有多么的近,原来所谓的成长,不外如是。如玫瑰,芬芳却易伤人伤己。
默不作声地一头扎进浴室中,任喷头将热水倾洒在裸露的皮肤上,想哭却没有眼泪。一种抓不住的苍白感袭满全身,抬起头,浴室的灯光在水汽的渲染下格外迷离,而内心有什么东西正被一点一点腐蚀掉。
但是我忽然就倔强了起来,决定出门散步,顶着绵阳夜晚常有的零星小雨,橘红的路灯下,校园的道路被雨沾湿,一点一点地绽放出妖冶的色彩。我蓦然停下脚步,忆起《蓝莓之夜》里的一个桥段,裘德•洛问琼斯:你还保存着那串钥匙么?我记起了所有人曾经的脸,曾经爱过的和被爱过的,问问自己心中的那串钥匙,到底还在不在。
于是整夜地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想给Bill打电话。电话薄上没有Bill的名字。
正如某个半夜时分自己因为睡不着而爬起来,在微弱的灯光下莫名其妙地开始读一本晦涩的小说,忽然为一段文字心声感慨,翻出手机,打下一大段一大段的话语,却在电话薄的一栏心生犹豫,收件人的名字被藏匿在窗外的风里。
一如往年的青春密码无可找寻。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各种美好存在着。
这一年我二十岁零七个月。
某一天的晚上,我蜷缩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完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时,枕边的手机“呜呜”地震动起来。翻开,点击,SU的一首诗让我眼眶禁不住湿润起来:
知情者
该如何告诉你我所知晓的一切
关于那些我无法祛除的情结
是的 我是唯一的知情者
我目睹你的爱与寂寞
只是我再不会开口说
说 说什么呢
请原谅我的欺瞒
若这已成习惯
权当它是誓言
我们并非身处博物馆
用不着海枯石烂
我不打自招 我无可奉告
我隐藏凶器 我熟能生巧
磕破佛像的红唇艳鬼
我是棵野草 我虚无飘渺
我戴着孤独的脚镣舞蹈
而你在我耳边呢喃
其实我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