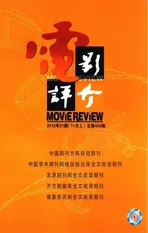1930年代上海私营电影公司经营策略初探
2012-09-28林子青
一、民国时期上海电影产业宏观环境
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在北京,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电影发展的中心却是上海。根据1927年的《中华电影年鉴》统计,当时全国共有电影公司179家,其中设在上海的有142家,也就是说,上海的电影企业占到了全国的约79%。到1930年代中期,上海电影产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此时的上海电影企业以资金来源加以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外资、私营和官营,其中,私营电影公司占到了90%以上。
在这三十七年中,上海电影产业所处的环境非常复杂。这一时期,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交通运输的枢纽,这种国际性和现代性,在客观上成为了上海发展私营电影业的必要条件。
1.地域因素。1912年至1930年代中期,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的贸易中心,也是金融中心及国内最大的轻纺工业基地,此时的上海,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据1935年的资料,当时“全国共有银行164家,总行设在上海的就有58家,占35%。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总数(己缴资本十存款十公积金+兑换券)共计达327191万元,占全国金融资力总数683920万元的47.8%”[1]。同时,这一时期的上海有着特殊的“租界”环境,这使得上海的人口结构组成非常适合电影业的发展。电影消费是娱乐消费与艺术消费的结合,而“为上海繁华生活或是商业社会发财机会而来的移民,既无清晰民族意识及排外心理,自然乐于接受西方物质文明,”[2]当时的上海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为电影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宏观环境。
2.资本因素。资金的储备是民国时期电影产业发展的基础,“资金的来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实业资本转变而来;二是外国资本的进入。虽然外国资本的进入带有侵略性,但是也推动了当时电影产业资金的积累和流动。”[3]
中国电影诞生之初,海外资本就活跃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民间资本的抵制及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外资电影公司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很小,并且其中的大部分都以合资的面貌出现。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意识到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在宣传上的重要意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提出了官营电影的中心思想。[4]虽然由于战争和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官营电影的发展并没有像小册子中设想的一样顺利,但仍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教育、制作及审查机制。
与海外资本和政府支持相比,当时的民族电影企业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但由于早期影片生产的成本并不十分高昂,且产量有限,“以1927年的物价算,一部影片成本最低4000元足矣,而影片放映收入却是成倍增加。”[5]因此,电影的可见利润使得广大国内的投机商趋之若鹜,民间资本的大量进入,使当时上海的私营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些私营电影公司依靠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以经济利益为基本动力,通过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外资电影公司进行对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客观上建立起了民族电影工业。到1930年代中期,私营电影公司占到了当时电影企业的90%以上。
3.文化因素。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春柳社”的成员回国开始投入国内的演出,展开了文明新戏运动。文明新戏不仅培养了中国民众“看戏”的观念和习惯,也为中国电影储备了相当一批演员、编剧、导演等从业人员,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此外,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浪潮的兴起,也为以此为剧本拍摄的影片提供了良好的观众基础,迎合了中国观众“重故事”的观赏习惯,为电影市场的繁荣提供了一片沃土。据《中国电影发展史》,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大多数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创作。[6]还有不少电影公司请鸳鸯蝴蝶派作家做电影的编剧,如包天笑、朱瘦菊、周瘦鹃等。仅二十年代包天笑就为明星公司编写了10个电影剧本,均拍成电影,另有两部小说由郑正秋改编成电影。[7]
二、民国时期上海私营电影公司发展历程
据相关史料记载的数据分析可得,从1910年代至1940年代,上海私营电影公司的数量及出品影片的产量都在不断变化。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曲线理论,一个产品从投入市场到被淘汰的这一段时间里,其销量会形成类似倒“S”形曲线,根据曲线的变化可以把产品生命周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投入期,产品刚刚投入市场,销量不大,增长缓慢;第二阶段的成长期,产品逐渐被消费者接受,销量迅速增长;第三阶段的成熟期,产品销量到达最高点;第四阶段的衰退期,产品销量迅速下滑,直至被市场淘汰。
以1913年至1936年这二十三年间的数据(见表一)为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上海私营电影企业发展按照以上理论,可以大致分为萌芽期、成长期、鼎盛期和衰退期这四个时期。
1.萌芽期(1912-1922)
在这一时期,上海私营电影公司的数量较少,每家公司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每年出品的影片数量也有限,出品的影片主要是一些时长较短的短片,内容则以新闻、纪录、滑稽为主。
表一:1913年至1936年上海私营电影公司数量及出品数量统计[8]

年份 公司数量出品数量1913 2 15 1927 29 111 1916 1 1 1928 26 106 1919 1 2 1929 26 126 1920 1 7 1930 27 100 1921 5 9 1931 19 100 1922 3 11 1932 10 56 1923 3 6 1933 26 84 1924 11 16 1934 31 86 1925 34 66 1935 17 55 1926 37 103 1936 13 43出品数量年份 公司数量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私营电影公司在资金及人才上的短缺,需要依靠拍摄短片来控制成本、加快资金周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认知仍停留在“是其他娱乐方式的附属品”上,尚未形成专程观影的欣赏习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人尚未完全掌握摄制电影的基本技术,在这些客观条件的共同制约下,此时的上海私营电影产业仍处在萌芽期。
2.成长期(1922-1930)
之所以以1922年为分界,是因为在这一年3月,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了。而以《阎瑞生》、《孤儿救祖记》等长片的放映和轰动为标志,电影业成为新的投资焦点,电影公司大量涌现,影片产量迅速增加。上海影戏公司、新亚公司商务印书馆等电影公司纷纷开始拍摄长故事片,掀起了中国电影长故事片的第一个高潮。
1926年,以天一影片公司的《梁祝痛史》大受欢迎为开端,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股古装片热潮,仅仅一年后,古装片逐渐被武侠片取代,中国电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显现出了类型化的特征。但是,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制片公司仍然采取低成本、短周期、大批量的制片和营销策略,因此从数据上来看,私营电影公司数量与影片产量都有大幅提高。
3.鼎盛期(1931-1935)
从1931年开始,联华公司在电影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形成了与老牌的“明星”、“天一”三足鼎立的态势,而在有声电影逐渐取代无声电影的这一历史时期,艺华(1932)、新华(1934)、昆仑(1945)、文华(1946)等电影公司纷纷成立,并拍摄了一些较受欢迎的影片,使得电影业进入了相对有序竞争的状态。
尤其在1934年度,四大电影公司产量都有大幅增长(见表二)。
表二:1934年度四大电影公司产量增长统计[9]

明星公司 联华公司天一公司艺华公司1933年度 51.229 32.017 26.975 6.092 1934年度 65.938 49.962 40.002 19.185增长百分比 28.7% 56.0% 48.3% 214.9%
此外,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展开和大批左翼电影人的加入,中国电影开始广泛关注现实,拍摄了许多反映社会中下层工人、农民、市民生活疾苦的影片,这些影片因为关注时事、贴近市民,因此深受好评,在艺术上较有成就,经济上也获得了较好的收益。在这一基础上,各个电影公司不仅大量吸收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更加开始注重对影片的宣传和营销。
可以看出,在鼎盛时期,私营电影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前一阶段单纯的数量竞争转变为更为良性的质量竞争。
4.衰退期(1935-1940)
上海私营电影产业的发展,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1935年,抗日战争爆发,直接导致中国电影市场萎缩,电影发展的大环境也随之恶化。同时,国民党政府加大了对文化的审查与控制,利用电影审查制度,对影片从创作到放映的整个过程进行了全面控制,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3月,短短5个月时间,被禁止拍摄的电影剧本就达83个之多。[10]除了加强电影审查,国民党政府还对左翼电影人进行了迫害,导致各大电影公司的创作能力被大大削弱。
从内部原因来看,规模较小的私营电影公司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下难以为继,规模较大的私营电影公司则由于人才流失导致影片质量下滑,直接影响了收入。
三、私营电影公司的经营策略
民国时期上海的私营电影企业根据其资金的来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家庭式独资、合伙型、股份型。在规模较大的私营电影公司中,上海影戏公司、天一影片公司是家庭式独资企业的代表;新民公司、幻仙公司、中国影戏研究社等是合伙型公司;明星公司、联华公司这些大公司则是股份型企业的代表。
虽然这些私营电影公司具有以上这些不同的体制和管理模式,但在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相同的经营目标下,它们的经营策略仍可以被共同加以提炼和总结出来。
1.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平民化营销。
电影从一开始就与娱乐化和商业化紧密相关,因此,中国电影的市场环境决定了最初一批受众是市民阶层,当时对于电影创作的普遍看法是:“第一要明白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中下层社会的人,最要紧的是迎和他们的口味,情节一热闹,穿插要多,无理取闹、节外生枝都不妨。只要博得他们的欢心、使得他们高兴、笑、拍手,你就丰衣足食了。你如要顾到自己的名誉,用高尚的思想向艺术上做出,欲博知识界的荣誉,除非你是个仙人,不吃烟火食。否则知识界给你的报酬,只能买些白水喝”[11]。所以,大部分私营电影公司在进行宣传和营销时,十分注重迎合平民的审美和趣味,例如在影片放映过程中进行戏剧表演,以明星或戏剧演出吸引观众等。
2.开辟类型电影市场。
与走平民化营销路线的目的相同,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电影创作者们将目光放在平民的生活中,拍摄出了《孤儿救祖记》这样的“解题式”影片,受到了广泛欢迎。之后,以《梁祝痛史》、《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古装武侠神怪片开始兴起;以《滑稽大王游沪记》、《大闹怪剧场》为代表的滑稽电影也开始出现;直至1930年代,以有声片的出现为契机,更出现了歌唱片这样的新兴电影类型。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片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带有能够吸引受众的娱乐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类型电影也正是上海私营电影公司采取经营策略的产物之一。
3.引进人才与技术。
各个私营电影公司为了提高竞争力,都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在民国时期私营电影产业的萌芽期,对人才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各个电影公司都会开设电影学校,培养可供使用的相关人才。而到了发展期和鼎盛期,各大电影公司都比较注重对现有人才的吸引和争夺,例如1933年10月,天一公司与明星公司的演员聘任之争。
电影从诞生之初就离不开技术的发展,因此,技术是影片质量的重要保证,私营电影公司都非常注重对技术的引进和使用,这一点在有声片出现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当时在资金、环境等许多方面都受到限制,许多私营电影公司还是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有声电影设备的采购和拍摄,1931年8月,明星公司购置了拍摄有声片所需要设备并聘请了技师,将一座无声摄影棚改成了有声摄影棚。1933年,联华公司更赴美购置了有声电影的摄录设备。
4.明星与品牌策略。
1925年,上海新世界游艺场组织开展了一次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候选人均为当时的一线女演员,包括张织云、阮玲玉、黎明晖、韩云珍、杨耐梅、王汉伦等,最终,张织云票数最高,当选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由这次活动带来的巨大反响及花边新闻,使得私营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们看到了明星的巨大号召力和票房保证,为此,各大公司都开始宣传本公司的明星品牌,带动影片的消费。当时较为著名的有明星公司的影后胡蝶及“七小生”,天一公司的陈玉梅,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和电影皇帝金焰等。
除了明星,各电影公司还力推本公司的著名导演,力图创造出导演品牌。当时较为著名的有明星公司的张石川、郑正秋,天一公司的邵醉翁,联华公司的蔡楚生、孙瑜等。
在政治环境、资本环境、需求环境等多方面存在不利因素的民国时期,中国电影产业同时面临西方电影的倾轧与当时技术条件局限的双重压力,而上海的私营电影产业却取得了不俗的艺术与商业双赢的成就。产生这一局面,正是因为上海众多的私营电影企业通过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平民化营销、开辟类型电影市场、引进人才与技术、强调品牌效应等诸多策略,探寻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私营电影产业发展道路。哲学家、文学家赵鑫珊曾经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允许国外集团与私人在国内设立电影公司的关键时刻,民国时期上海私营电影企业的经营策略,对目前中国民营电影产业的发展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潘君祥、王仰清主编《民国经济》,《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Pll-14。
[2]叶晓青《上海洋场文人的格调》,《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汪晖、余国良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27。
[3]沈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业产业经济学初步分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08期,P25。
[4]杨燕、徐成兵《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29。
[5]杨燕、徐成兵《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2。
[6]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二版,P56。
[7]封敏《包天笑与中国早期电影》,《当代电影》1997年第1期。
[8]数据来源: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版;朱天纬等主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申报》1920-1937年。[9]卢莳白《提倡国产影片的眼中问题》,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年会专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1935年8月,P46。
[10]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版,P304。
[11]《记<冯大少爷>影片》,《申报》1925年9月24日,本埠增刊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