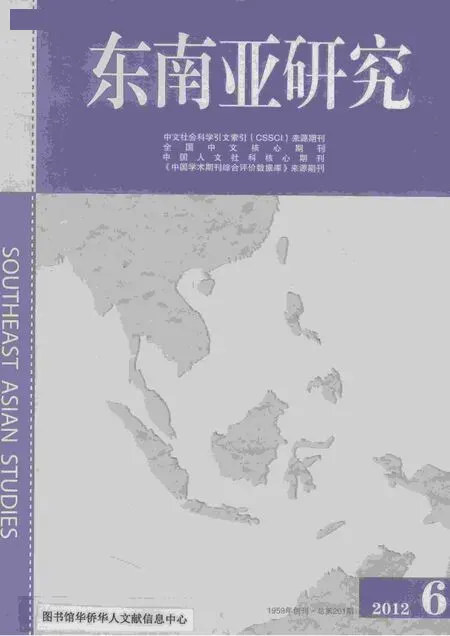印度对印尼的软实力外交与两印关系新发展
2012-09-22李志斐
李志斐 唐 翀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与亚太战略研究院 北京100007;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州510630)
软实力作为一种非物质力量,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一方面可以整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自然资源,以此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重视对国家综合安全的维护和保障,注重良好的国际形象的树立,有助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印度与印尼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两个文明在政治、商业、社会等方面存在着持续的交流,印度对印尼文化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印度与印尼在各自独立的斗争中就相互支持,尼赫鲁总理和苏加诺总统形成了密切合作,携手支持亚洲和非洲的独立事业,这成为了两国独立后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和后来的不结盟运动 (NAM)中相互合作的坚实基础。1959—1966年印尼激进的外交政策对印—印关系构成了短暂的冲击,但随着苏哈托军人政府的上台,双边关系很快重新恢复正常[1]。
在当今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中,印尼在地理、经济、政治、宗教、资源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任何一个关注该地区的大国都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迅速崛起的大国,印度近些年在对印尼的关系构筑中日益强调软实力外交的运用,力图从根本上为“东向战略”的实施注入更多推动性因素。在本文中,笔者将系统地分析印度在对印尼的外交关系发展中,如何巧妙而又娴熟地运用软实力外交手段来全力推动两印关系的新发展。
一 印尼在印度“东向政策”中的关键地位
印度把与东盟开启的和平进程称之为“面向东方的命运”(look east destiny)[2]。冷战的结束对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冷战时代经济领域的竞争成为了主权国家竞争的新方向。随着东亚新型工业国家的经济崛起,印度开始把外交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及东亚的邻国。1991年,印度拉纳辛哈·拉奥 (P.V.Narasimha Rao)政府在外交中正式提出“东向政策”。有学者指出,“东向政策是印度新现实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它旨在推进与东方的邻国形成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印度与东盟的接触也部分反映了印度精英们对东南亚地区在印度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的重视。”[3]
从1991年开始,印度对东盟的外交重点是修复并积极拓展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印度在1992年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5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1996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完成了与东盟组织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同时印度与东盟老五国的经贸关系也取得很快的发展。由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影响,印度“东向政策”在1997—1999年之间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印度核试验问题的逐渐淡化,以及由中国掀起的地区合作热潮的冲击下,瓦杰帕伊于2000年提出“再次向东看”,加大了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与越、老、柬、缅和泰签署《万象宣言》,成立“恒河—湄公河合作组织”,寻求通过旅游、人员、文化及交通合作来密切与新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另外,印度加强了与东盟的高层互访,确立了与东盟合作的机制,继中日韩之后成为第四个与东盟单独举行峰会的国家,并正式成立了第四个“10+1”合作机制。
2003年10月印度外长加斯特旺·辛哈 (Yashwant Sinha)在巴厘峰会上正式宣布“东向政策”进入第二阶段。他指出:“(东向政策)的第一阶段集中在建立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上。而第二阶段的特征则是把东方的定义扩展到澳洲、中国和东亚,这些国家与东盟一道都是该政策关注的核心。第二阶段也标志着从专注于经济问题转向经济与安全问题并重,其中包括维护海上交通路线的联合行动、合作反恐等。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与相关国家建立自贸区,以及制度性的经济关系。”[4]从这段讲话可以看出,印度“东向政策”第二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两个方面。首先,双方合作的程度更高,领域更广。在2003年10月于巴厘岛举行的第二届印度—东盟峰会上,印度与东盟签署了《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宣言》,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文件的签署表明印度与东盟的合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双方在政治、安全乃至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将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其次,双方合作所囊括的范围更广。印度“东向政策”不仅包括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国家,还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向政策”成为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尽管印度在后来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东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但东南亚一直以来都是该政策的核心部分。印度现阶段的“东向政策”更加务实,它推动印度与东盟组织及东盟国家分别建立了各领域、机制化的联系,印度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亚太地区战略结构中的存在。
在印度的战略视野中,印尼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因此印尼理所当然成为印度东向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
第一,印尼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作用。首先,印尼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正处于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国际航线的关键位置,掌控着这一重要航线上的三个关键要道——龙母海峡、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其次,印度与印尼隔洋相望,安达曼与尼古巴群岛是印度的中央直辖区 (Union Territory),它与印尼亚齐省的最近距离不超过150公里。印度建立了总部位于布莱尔港口 (Blair Port)的安达曼与尼古巴联合司令部 (Andaman and Nicobar Joint Command),该司令部的主要职能就是维护马六甲航行安全,以及印度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由于与中国在那图纳群岛 (Natuna Islands)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纷争,印尼对中国在该问题上的态度也保持警惕。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印度与印尼在排除中国对印度洋及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平衡中国影响力方面,都具有一致的利益。此外,恐怖主义威胁还为双方联合维护马六甲海峡航运安全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印尼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印度接触东南亚的政策中具有重要的优先性。
第二,印尼在地区及全球的积极角色使其对印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从地区层面来看,东盟所采取的大国平衡战略对于亚太地区关系的稳定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东盟的一体化及东盟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对地区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国家,它的持续而健康的发展对于东盟的成长意义重大。尽管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很不明朗,但印尼经济从2009年以来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2011年印尼实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长,达到了6.5%,世界银行预测印尼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将是6.2%[5]。随着经济的增长,印尼外交信心也不断增强。在地区层面,印尼利用2011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的机会,在泰柬边境、南海问题上扮演了地区冲突的协调者角色,并积极推进联合国与东盟之间在食品和能源安全、维和、气候变迁、灾害防治及人权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在双边层面,苏西诺第二任期提出“千万朋友、零个敌人”(thousands friends,zero enemy)的外交口号,积极推进与各国的关系;在全球层面,印尼在中东问题、G20会议、全球气候变迁等问题上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印尼战略重要性的不断增强导致了外部大国对其争夺的加剧,面对这样的形势,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 (IDSA)研究员认为,印度“应该加强对印尼的影响力”[6]。
第三,印尼的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对印度也非常重要。印尼在1998年之后进入民主转型时期,印尼民主化的顺利进行对印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尼建设多元社会与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不仅对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其在实现伊斯兰教与多元民主社会和谐共存方面的例子,也对拥有庞大穆斯林人口的印度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印度驻印尼大使毕冷·南达 (Biren Nanda)在帕纳曼迪纳大学举办的“一个印度”(a slice of India)展览活动的开幕致辞中指出,“印尼是多元而独特的,这个国家存在众多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这就是印尼成为治理多元化模范国家的原因。”[7]此外,印度与印尼在推进地区与全球的民主价值观方面也具有一致的利益。辛格总理与苏西诺总统在两国2011年缔结的《新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就指出,“作为本地区致力于多元文化主义、多元主义与多样性的发展中民主国家,印尼与印度是天然的伙伴。……他们必须为推进亚太地区及世界范围的民主、和平与稳定而扮演更积极的角色。”[8]
二 印度对印尼外交的软实力基础
早在印度立国之初,尼赫鲁总理就断言,“印度应该成为亚洲的核心”。直到现在,成为全球大国和亚洲核心一直是印度的梦想和前进动力,印度在不遗余力地增强着国家的综合实力。而自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的世界主题,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以经济、军事、科技为主的物质力量方面,历史文化、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影响力等非物质力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评判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印度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迅猛增长的基础上,日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构建。
“实力”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之一。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情报委员会主席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提出,国家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冷战结束以前,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主要依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科技、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等“硬实力”,但在冷战结束后,“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昔日极其突出的军事力量和政府”,“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9]。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就属于“软实力”,它是通过同化而非强制来让别人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硬实力与软实力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他们都通过影响别人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目的,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则在于行为的性质与权力资源的真实性的程度不同。支配性权力 (command power)是通过强制与诱导来改变别人的行为;同化权力 (cooptive power)是通过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或者使别人偏好发生变化的能力。”[10]软实力的内容通常包括:第一,文化吸引力;第二,意识形态感召力;第三,国际规则与机制的制定能力;第四,外交政策影响力;第五,良好的国际形象塑造;第六,国家与民族凝聚力。
印度具备对印尼开展软实力外交的基础。
首先,两印之间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2004年,奈在《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文中指出,当一国文化包括普世价值观,且对外政策是促进别国所共有的价值观和利益时,其获得理想结果的可能性增大[11]。印度是著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印度开展文化软实力外交具备了深厚的基础,而文化软实力正是一国软实力的基础。印度和周边国家联系的渊源当属宗教。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如今全世界有大约3亿的佛教徒,涵盖了东亚各国,佛教已经成为联系印度和东亚儒家文明圈的纽带和桥梁。2010年9月,印度国会正式批准了“复兴那烂陀计划”,通过该计划,印度、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16国合作,重新把那烂陀大学发展为学习及跨宗教对话的中心,将佛教和现代的大学结合,达到吸引外国留学生、宣传印度文化、扩大印度影响力的目的[12]。新德里如今竭力强调其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把佛教置于它在亚洲的软实力外交的中心位置[13]。
除了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也发源于印度,另外,印度国内还拥有众多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拜火教甚至犹太教信徒。其中伊斯兰教是印度的第二大宗教,在印度境内拥有大约1.62亿的信徒。可以说,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多宗教共存的大国,印度社会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精神,为其提供了和谐共存的环境。在周边关系构建中,宗教之间的联系为印度和邻国增加了亲近感,为消除怀疑和化解矛盾提供了基础。
在历史上,印度的宗教文化对印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印尼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就是印度教王朝,直到现在,印度教寺庙在印尼国内随处可见,其习俗和文化流传至今。另外,在印尼影响最大的宗教派别——伊斯兰教,也是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穆斯林传入的。印尼是著名的伊斯兰教国家,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Yudhoyono)经常谈到印尼是一个民主与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外交部长哈桑·维拉尤达 (HassanW irayuda)也常常提到民主与温和的穆斯林是印尼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法宝[14]。自1998年重返国家政治舞台以后,伊斯兰教对印尼对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9·11”事件以后,印尼将塑造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形象作为国际形象树立的目标,伊斯兰教成为沟通印尼和其它世界国家的重要桥梁。因此,印度丰富的宗教文化以及与印尼之间的宗教渊源为印度对印尼的软实力文化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两印之间具有相似的民族命运和政治价值观。约瑟夫·奈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一国的主导文化和全球的文化规范相近 (即强调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话,有助于软实力的建设[15]。印度和印尼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都进行过坚决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都在努力谋求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民主和自由,在外交政策上都主张不结盟和独立自主。另外,在政治观念上,两印都主张实行民主政治,认为只有民主才能保持国内稳定、在国际社会的亲和力以及对周边国家的号召力。印度在1947年取得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的议会制度,其实行的普选制使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精神得到发挥,其选举结果基本上反映了印度民众的民意。印度的民主和法制观念如今也已经深入人心,印度也因此被西方世界誉为“最大的民主国家”。而随着1998年新秩序政府的瓦解,印尼也进入了民主化的建设时期,如今凭借三权分立、议会民主选举以及各级地方首长和总统直选制等被国际社会评价为继美国、印度之后排名第三的民主国家。印尼政府和官员引以为豪的民主国家身份为其与其他民主制度国家开展合作与交往提供了更深的国家身份认同。现在,与美国、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和东盟、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地区伙伴的关系,是印尼对外政策的中心,印尼民主国家的身份在不断提升其与亚洲太平洋大国的关系方面功不可没。
再次,两印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需求与外交政策选择。“强大的经济是一国吸引力的重要来源”[16],“经济实力既可以转化为硬权力也可以转化为软实力,既可以用制裁来强制他国,也可以用财富来使他国软化”,“经济实力是粘性实力,它既可以起到吸引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强制作用”[17]。印度和印尼都属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落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任务。两国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有着很强的资源互补性。对于印度来说,发展资金虽然比较丰富,但能源和原材料的紧缺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而印尼虽然能源和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使之比较捉襟见肘。所以,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谋求深入的发展符合两印的共同愿望。
在外交政策上,两印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战略都很多相同之处。两印都以自己的民主国家身份为豪,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和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印度一直将建设一个强大的、受国际社会认同和尊重并发挥积极国际作用的世界大国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而印尼则明确声称,“将自身塑造成东南亚地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国际社会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民主与穆斯林之间的桥梁”,是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18]。印度和印尼的首要外交目标就是要确立和维护自身在所在地区的领导角色,同时积极扩大外交范围,努力发展与美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大国的关系,走全方位外交之路。印度的对印尼外交正是在其东向战略的大方向之内,而印尼对印度的外交是走出东盟范围的大外交战略的结果。可以说,两印之间相同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趋向为其双边的软实力外交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这些基础又为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注入了极大的动力。
三 在伙伴关系下印度对印尼的软实力攻势
2004年苏西诺就任总统以后,印度与印尼的关系定位实现了新的突破。2005年11月,苏加诺总统对印度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与印度领导人签署了两国新战略关系宣言,表明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战略伙伴关系阶段。2011年1月,苏西诺总统对印度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并作为印度共和国60周年庆典的主嘉宾出席了庆典,这标志着两印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目前为止,两印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有七个年头,国防部长对话、高层战略对话等双边协商已经陆续建立起来,在经贸、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已经向纵深发展,战略伙伴的实质性内容正在逐步构建。深入分析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和构筑过程就会发现,印度软实力外交的开展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软实力的运用: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通常是以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为目的,是国际关系领域中超越传统外交范围的一个层面,包括: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内培植舆论、一国利益集团和他国利益集团在政府体制外相互影响、媒体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络等,通过这一系列过程达到影响其他国家政策制定和外交事务处理的目的[19]。印度一直有运用公共外交或其他软实力外交手段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的的历史[20]。自实施“东向政策”以后,印度一方面延续着“传统性”的公共外交手段和路径,一方面非常注重根据时代变换和周边环境进行“创新”,使公共外交的“时代性”更加凸显。
在传统方式上,文化交流、学术联系、媒体对外播报是印度充分运用“软实力”的三大手段[21]。印度专门设立了致力于文化交流的公共外交机构——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 (ICCR),试图借助自己的文化、科技、教育的先进性和现代化,联络海外印度人,与海外商业利益集团建立联系,实施对外援助和发展项目,同时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机会展示印度的“国家标签”,运用新社会媒体影响年轻人等“新手段”来扩大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和实现印度的战略目标[22]。
在对印尼关系中,印度充分利用与印尼在文化上的悠久渊源,利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印尼盛行及与印度的历史联系,发挥本身的科技优势和现代化思维,对印尼社会阶层大力发挥文化外交。这种软外交方式,影响印尼社会内部对印度的认同与现代认知,从而建立起两印深层次交往的社会民间基础,有助于全方位国家合作的开展。最鲜明的例子就是2009年10月到2010年7月,印度在印尼举办了两次“印度文化节”,并把2011年列为两印“友好年”,以此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印度对自身文化大国的巧妙塑造对于其增强对印尼的影响力并强化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基础性的重大意义。
(二)硬实力的软运用:经济、政治和安全互动与合作
印度在构建对印尼的外交关系中,除了结合自身历史基础和现实优势来“巧妙”运用软实力之外,还将其硬实力进行“软包装”,加强与印尼的经济、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印度与印尼在1986年就签署了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双边协定;1999年G15峰会期间两国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该协议于2004年1月生效。2005年印尼总统访问印度期间,两国还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成立研究双边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 (CECA)可行性的联合研究小组。该小组2009年提交的最终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印度对印尼的出口最高可达到780亿美元,而印尼对印度的出口最高可达970亿美元,双边综合经济协议实现后对印度与印尼GDP的贡献分别为1%和1.4%[23]。
印度的进口商品主要是棕榈油、煤、石油及纸制品,而印尼主要进口香料、纺织纱线、化工产品、电力机械及零件、精炼石油产品、钢铁和钢铁制品、小麦、大米和糖。印度是最大的棕榈原油进口国,印尼已成为印度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新加坡。此外,印度正计划通过从亚齐到尼科巴群岛的海底管道向印尼购买天然气。印尼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印度与印尼的双边贸易额在2010年达到了130.2亿美元,印度分别是印尼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十六大投资国[24],可以预见,印度未来有可能成为印尼最关键的贸易伙伴之一。
进入21世纪之后,两印的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层互访和会晤的频率显著增强 (见表1)。两国在2005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中强调,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观,都主张民主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多极化,推崇法律的至高无上。2007年1月,印尼副总统卡拉访问印度时,与印度签署了在反恐、能源、自然灾害应对、电力开发使用、矿产和交通等方面的合作与对话协议。2008年印度总统巴蒂尔与苏西诺在雅加达会晤时强调,两国要在教育、科技、农业和旅游及影视业方面提升合作层次。2011年1月,苏西诺第二次访问印度时,两国就政治、安全、文化与社会合作签署了11项谅解备忘录。
2001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访问雅加达期间签署了两印的防御合作条约,印度重点向印尼提供防卫科技和训练。另外,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印度积极摆出支持印尼反击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姿态[25]。2004年7月,两印签署了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谅解备忘录,并成立了联合反恐工作小组。针对马六甲海峡海盗比较猖獗的现象,两国在打击以海盗问题为代表的海上恐怖主义方面,合作深度不断加大,不仅“两国军舰实行互访,而且还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海军舰队为印尼船舰前往安达曼海巡航护航”[26]。2011年1月,两印再次共同表示将在“情报分享、反恐政策制定等方面展开合作”[27]。

表1 2000年以来两国首脑互访一览表
结语
印度尼西亚凭借其位于印度和太平洋“守门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导角色,在印度的外交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印度将改善和加强与印尼的关系视作在东南亚地区扩展影响力的关键之举。近些年,在新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印度对印尼开展了全方位的软实力外交,在重视包括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内容的软性权力拓展的同时,还巧妙地将硬权力“软”使用,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印尼的合作伙伴关系。
印度极力在印尼开展软实力外交,其目的除了实现自己的“东向”战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联合印尼共同牵制中国。在印度看来,同为亚太地区不断崛起的大国,中国通过软实力外交所塑造的“魅力中国”形象,足以对其扩展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形成威胁,对其参与亚太事务形成阻碍,因此,只有奋起直追,充分运用印度所拥有的软实力资本,发展软实力外交,才能有效地制衡中国的影响力,实现所规划的战略目标[28]。
从本质上说,“软实力”外交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外交方式,对于印度对印尼的软实力外交开展,中国一方面需要看到印度企图充分发挥软实力外交来“对抗”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和努力,另一方面应更多从印度对印尼外交中获得启示,即如何在周边关系构建中更加巧妙地运用软实力。作为亚太大国,中国除了突飞猛进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之外,还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赋予了中国丰富的软实力潜力,思考如何将其运用到外交关系构建和周边安全塑造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软实力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周边安全问题不断,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正经历着进入21世纪后的新一轮挑战[29]。因此,在这种大背景和迫切现实面前,如何运用软实力外交来一定程度上化解中国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化解潜在的安全危机,塑造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更是现在的中国需要审慎思考的议题。
【注 释】
[1]印尼苏加诺政府采取了激进的左倾外交路线,提出“打倒印度,帝国主义的走狗”、“粉碎印度,我们的敌人”等口号,由此对两国外交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者拉塔尔·辛格 (L.P.Singh)将印—印两国建国之初的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1947—1958年友好和谐阶段、1959—1961年分歧阶段、1962—1966年紧张对抗阶段、1967年后恢复友好关系。参见L.P.Singh,“Dynamics of Indian-Indonesian Relations”,Asian Survey,Vol.7,No.9,1967,p.655.
[2]Faizal Yahya,“India and Southeast Asia:Revisited”,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5,No.1,2003,p.81.
[3]Thongkholal Haokip,“India's Look East Policy”,Third Concep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deas,Vol.25,No.291,2011,http://www.freewebs.com/indiaslookeastpolicy/what_is_LEP.htm
[4]Tan Tai Yang and See Chak Mun,“The Evolution of India-ASEAN Relations”,India Review,Vol.8,No.1,2009,p.31.
[5]Thee Kian Wie,“The Indonesian economy in 2011:a precarious balance”,East Asia Forum,January 4,2012.
[6]Pankaj K.Jha,“India-Indonesia:Emerging Strategic Conflu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Strategic Analysis,Vol.32,No.3,May 2008,p.455.
[7]“India sees Indonesia as a unique democracy role model”,ANTARA News,January 31,2012.
[8]“Joint Statement:Vision for the India-Indonesia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over the coming decade”,January 25,2011.
[9]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10]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p.5 -8.
[11]杨文静:《重塑信息时代美国的软权力—— 〈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介评》, 《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8期。
[12]《〈人民日报〉环球走笔:重建那烂陀的雄心》:http://www.dzwww. com/rollnews/news/201009/t20100929_6711684.htm,2010年9月29日。
[13]石俊杰: 《浅论印度的软实力》, 《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4期。
[14]里扎尔·苏克玛著,邹宁军译《印尼的伊斯兰教、民主与对外政策》,《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
[15]Joseph S.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4.
[16]Jos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7.
[17]约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8]闫坤: 《新时期印度尼西亚全方位外交战略解析》,《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1期。
[19]“What is Public Policy”,www.publishdilomacy.org/1.htm.
[20]Jacques E.C.Hymans,“India's Soft Power and Vulnerability”,India Review,8:3(2009),pp.234-265.
[21]Ian Hall,“India's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Action”,Asian Survey,42:6,2012,p.15.
[22]Ibid.,pp.19-26.
[23]Report of the Joint Study Group on the Feasibility of Indian-Indonesi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2009,p.90.
[24]Linda Yulisman,“India,RI expect trade to reach US$25b by 2015”,The Jakarta Post,06-10-2011.
[25]David Brewest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Indonesia:An Evolving Security Partnership”,Asian Survey,Vol.51,November 2,p.233.
[26]Akhyari,“India And Indonesia?An Analysis of Our Foreign Policy”,MeriNews,Feb.22,2010,http://goodnewsfromindonesia.org/2010/02/22/india-and-indonesiaan-analysis-of-our-foreign-policy/3
[27]Rajeev Sharma,“India,Indonesia Get Closer”,Eurasia Review,Jan.30,2010,http://www.eurasiareview.com/analysis/india-indonesia-get-closer-31012011/
[28]Philip Seib,“India is Looking Anew at its Public Diplomacy”, 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newswire/cpdblog_detail/india_is_looking_anew_at_its_public_diplomacy/>,20 May 2011.
[29]观点引自时殷弘教授在2012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大国的亚太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