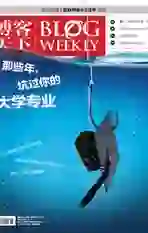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12-08-30

我的高考志愿并不是自己选的。
2006年,我报考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管理学专业。当时觉得,要想以后有所发展,就要选一个与人打交道的学科,不能选与器材、机械打交道的。但因为分数不够,我被调剂到新闻学专业。
那年9月,我带着铺盖,卷着对新闻学的未知,踏上从山东滕州到北京的列车。4年下来,我没有过于激烈地抗拒过这个专业,但也没有对这个专业所设的课程留下深刻印象。我最讨厌新闻史这门课,因为我始终不理解研究邹韬奋的新闻思想对现在做新闻有什么意义,那时候我想“不知道毛泽东办过什么刊物也无损我写出好新闻来”。
我和大部分学新闻的同学一样,上学的时候对“新闻理想”这4个字嗤之以鼻。因为要实现普利策口中的新闻理想,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下似乎不太可能;而课本中宣扬的那种,吸引力又非常有限。
但奇怪的是,在我一些同学的眼里,我还算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毕业时,有个同学喝得醉醺醺地跟我的老师说:“其实张宁(化名)有点新闻理想,但他不愿意承认。”我想之所以我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或许是因为我曾用心地做过一些专业功课。
与理论学科相比,新闻学里一些实践课程更能引起我的兴趣。2008年初夏,为了交一份纪录片的作业,我跑到了唐家岭—一个北京“蚁族”的聚集地。我的一名高中同学在这里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租了一间房,作为北漂生活的落脚地。他们住的地方不如农民工,吃顿饺子算是奢侈,嘴里却也谈论着中关村、Gucci。我拍了一部纪录片,想让人们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当时,“蚁族”这个词还没有流行起来。
跟新闻这门学科打交道的时间久了,我发现这个行业门槛其实很低。但如果想做一个足够好的记者,就得精通一些领域,比如财经、体育。我不由得对这个专业产生怀疑:新闻学教会了我什么呢?新闻敏感度?我想只有精通某一行业后,才能说对这个领域有新闻敏感度。在大街上找社会新闻的记者的出路在哪里?或许是在居委会大妈的眼界里。
到了毕业的分岔口,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我确实曾想过做一名记者,毕竟作为一种糊口的手段未尝不可。但我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这个圈子里,我报考了本校的研究生,同时报考了北京和天津的公务员。其实我并不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
庆幸的是,我考上了研究生,也得到了北京和天津的公务员的录取通知,以及北京一家晚报的offer。最后,我选择成为一名公务员,在天津的一个地税局里上班。
现在,我循规蹈矩地过着公务员的生活。我的上司是一位喜欢散步的科长,早上7点40分到办公室,在食堂里吃过早餐后,我和同事们会陪着科长在外面散散步。8点30分准时上班,下午4点半就下班了。下班时间大部分用于应酬,我的体重从毕业时的140斤涨到了160斤。
我偶尔会觉得这样的生活过于散漫,对未来有些忧虑。于是我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的考试,无事的时候,我会步行几百米,到附近的图书馆里复习。回想起来,新闻学这个专业虽不如想象中美好,但也没有多差,毕竟人们总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学新闻的人文笔都不错”,这也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帮了大忙。(本刊记者 高诗朦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