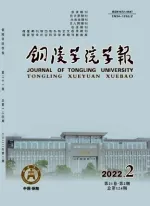城市化语境与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
2012-08-15瞿华兵
瞿华兵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城市化语境与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
瞿华兵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城市化语境下乡村题材小说形成一系列的文体特征。同时,城市化语境下乡村题材小说形成的文体特征又存在诸多问题。乡村题材小说作家要有超越所处时代的胆识和勇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修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乡村题材小说。
城市化语境;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特征;问题与可能
所谓“城市化”通常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现代产业向城市聚集,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物质文明和文化不断扩散并侵蚀传统文明,走向现代城市文明的社会历史过程。因此,城市化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影响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虽然从建国初就开始城市化的进程,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原因,城市化水平并没有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城市化水平获得质的飞跃,中国由此开始真正步入城市化时代。城市化语境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乡村题材小说上就是不仅导致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形成独特的审美取向、题材范围,而且还形成独特的文体特征。
一、乡村题材小说的文体特征
特殊的时代风尚形成独特的小说文体,城市化语境导致乡村题材小说形成独特的文体特征。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文体的狂欢化。狂欢化是城市化语境赋予乡村题材小说一个重要的文体特征,形成了乡村题材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狂欢化的故事。小说《受活》(阎连科)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讲述雄心勃勃的县长柳鹰雀异想天开,想用重金从俄罗斯购买列宁的遗体,建一个公园吸引游人,发展旅游业的故事。整个故事具有明显的荒诞意味,被称作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兄弟》(余华)通过讲述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从“文革”至今的跌宕人生,为读者展示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小说极具狂欢色彩,因此被冠之以“怪诞现实主义”。①同样故事具有狂欢化特点的还有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二)狂欢化的人物。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狂欢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众多狂欢化的人物。狂欢化人物的精神具有佯狂的特质,他们是以一种佯狂的姿态对历史和存在保持深刻的洞察。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他们不与世界上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他们看出了每一种处境的反面和虚伪”。[1]因此,“狂”是他们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的表征。像《秦腔》(贾平凹)中的引生和白雪,《生死疲劳》(莫言)中蓝解放就是世人眼中的“傻子”和“狂人”,他们都以一种有悖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另一方面,狂欢化的人物还具有“复调性”的精神气质。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各种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思想、情感、观念杂糅在一起,互相撕扯、纠缠,人物的性格呈现出分裂性、狂欢化的特点。《兄弟》中的李光头和《第九个寡妇》(严歌苓)中的王葡萄就是复调性型人物的典型代表。(三)狂欢化的语言。狂欢化的语言表现为不同的语言风格、语言种类相互混杂、交织在同一文本内部,呈现出既对立又和谐的话语形态。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常常是将中国当代的官方话语、民间俗语、河南方言、脏话,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严肃的和戏谑的等几种不同文化含义的语言形式结合在一起,充满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味道。《花腔》(李洱)里的语言油腔滑调,毫无正经。戏拟词汇、反讽词语、时髦词汇、黑话、粗话、俏皮话、插科打诨汇聚一堂,各种话语在这里对话、交流,使得本来逻辑严密、严丝合缝的历史显得飘忽不定、支离破碎,有力地解构了历史的真实。
其次,文体的故事化。文体的故事化是城市化语境下乡村题材小说形成的又一文体特征。所谓故事体通常指的是作家运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叙述一个或几个故事,小说的故事性极强,整个文本呈现出故事化的形态。故事化文体主要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故事的好看性。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特别重视故事的讲述,作家往往把讲述好看性故事作为文学创作最高的艺术追求,这其中尤以“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和以进城打工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底层文学”最具代表性。像《大厂》(谈歌)、《分享艰难》(刘醒龙)、《年前年后》(何申)、《马嘶岭血案》(陈应松)、《花落水流红》(王祥夫)等作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底层文学”因为对故事性的过分追求,还遭到批评家普遍的诟病。②除上述作品外,《日光流年》(阎连科)、《狼图腾》(姜戎)、《藏獒》(杨志军)、《公羊串门》(杨争光)、《淋湿的翅膀》(胡学文)等许多作品也存在这种现象,小说完全由故事构成,好看性成为作品的第一要义。其二是叙述体的形成。与故事体相对应的是叙述体的形成。传统的乡村题材小说都把描写作为最重要的艺术表达形式,但由于一味追求好看的故事,描写这一方法现已被作家们普遍抛弃,叙述代替了描写。“乡土作家笔下展现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乡村故事,是对叙述技巧的变换,却很少有精细生动的描写,很难看到切实生动的乡村生活画面和细致优美的乡村风景”。[2]许多作家的作品,全篇都由叙述构成,没有一句人物的直接对话,像你说、我说加双引号这种传统的对话方式基本从小说中消失,即使有对话,也只是采用在“说”后面加逗号这种更加快捷的叙述方式,也没有任何客观景物和人物肖像的描写。譬如毕飞宇的《平原》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通篇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物对话。
第三,文体的抒情化是城市化语境下乡村题材小说形成的第三个文体特征。文体的抒情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废名、沈从文、萧红、艾芜、芦焚等都是公认的抒情体小说作家,他们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典范意义的抒情体小说。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抒情传统被中断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种传统才得以赓续,重新出现了一批抒情化的小说。对景物和心理的大量描写无疑是带来乡村题材小说文体抒情化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迟子建对大兴安岭山林地带自然景物和风光的描写,使作品具有诗的旋律和恬淡悠远的意境;张炜纵情抒写胶东半岛上的野地和葡萄园,增添了作品的诗意氛围,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雪漠的“大漠”系列对一望无际茫茫戈壁的书写,造就了小说雄浑磅礴的气势。刘庆邦的《梅妞放羊》、《鞋》等小说中对青春期少女心理的细腻刻画,使小说充满了浪漫和温情;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大年》和迟子建的“北极村”系列完全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全篇,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作品好似一首首抒情诗。苏童说:“迟子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而来”。[3]以上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对景物和心理的大量书写带来抒情意味的,还有一些作品则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来增强自身的抒情性。小说中人物内心情感的大段独白,也增添了小说的抒情意味。张炜的《九月寓言》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小说中如果缺少人物内心情感的大段独白,表达对充满生机原野的无限向往和代表“清洁精神”教义的执着追寻,小说的抒情意味也会大大削弱;谈歌的《天下荒年》和李佩甫的《黑蜻蜓》中如果缺少作者的直接抒情,作品所要表达的对传统美德的歌颂、对物欲横流当下社会现实的否定就不会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当然,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诸如采用诗化的语言、诗化的节奏、塑造诗化的人物形象等等方式来构成小说的诗意抒情。总之,抒情化是90年代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文体现象。
二、城市化语境与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特征的关联
文学的文体属于艺术范畴内的问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文学的文体特征哪些得以张扬,哪些受到抑制,哪些得以发展,哪些会被忽略,却往往受制于整体文学风尚以及这种风尚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1990年代以来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充分说明了城市化语境和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特征之间的密切关联。
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的,是对城市化语境现实的真实反映。正如格非所认为的:“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形式,通常是作家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4]1990年代以来,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裂变导致社会思维异常活跃,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景观。市场经济带来了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盛行,网络传媒的迅速普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营造出无中心、平面化、游戏化、狂欢化的社会景象。历史完全丧失了它的完整性,甚至诗性,呈现出非延续性、断裂性和支离破碎的面貌。传统现实主义的美学概念,例如真实性、典型性等核心命题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层、贫富分化等问题的存在,成为当下小说中多种“声音”激烈交锋、对话的叙事背景。例如《花腔》设置多重叙事视角,不同叙述人说话的语境、风格、语调、对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它们之间既互相指涉又互相拆解,历史因游戏性和荒诞性的叙事操作而趋于文本化,历史的真实性和庄重性遭到彻底的解构。在林白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中,原本封闭、宁静的乡村生活因为城市生活元素的介入而变得五光十色,既有自然状态的蓬勃生机,又有城市生活的欲望翻滚,中国当下乡村生活的面貌真实地呈现出来。《受活》和《兄弟》中光怪陆离的画面可以说正是欲望翻滚、道德沦丧、贫富分化、金钱至上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余华在谈到《兄弟》的创作时说:“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这么丰富了。80年代我要采用一种‘虚伪的形式’去表达,但今天的很多现实生活按照常理都是不真实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不真实之中”。[5]小说的狂欢化正是作者对这个尖锐的、对立的、非理性的、充满荒诞感世界的感受和体验。
在现如今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学成为商品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已很难找到不为市场而写作的作家,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市场法则的影响。对故事性的追求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乡村题材小说当然也不例外。作家为了更多地占有读者和市场,大多追求小说情节的曲折生动,讲究故事的精彩好看。关仁山说:“不管哪样小说,小说还是要好看。……小说本质是什么?就是好看!小说好看的基本要素就是讲个好故事。不管新故事,还是旧时代的故事,只要有新意、真实、生动,合乎逻辑、跌宕起伏,才能引人入胜。”[6]乡村题材小说写得是越来越好看,故事情节是越来越复杂多变,叙述代替了细致的描写。小说对故事的寻求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7]故事可以说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也是小说的灵魂。尤其是在高速的生活条件下,或许已经不允许出现以往那种对乡土风貌的浓彩重抹的慢节奏描摹,而是需要快节奏好看的故事。许多作家都把讲述精彩的故事作为文学创作最高的艺术法则,甚至先锋小说作家也不能例外,开始大面积地“后撤”。先锋派小说的代表性人物苏童说:“我认同这么一个观点:人们记住一个小说,记住的通常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甚至是小说的某一个场景,很少有人去牢记小说的语言本身”,[8]这对一直视形式技巧(包括语言)为文学最高艺术追求的先锋作家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转折。无独有偶,其他先锋小说作家如马原、余华、格非等人,都重新审视故事的价值,召回过去被消解和淡化的“故事”,努力使作品“通俗化”,向大众靠近,在小说创作中又回归故事。余华在面对指责时辩解说:“我觉得现在的许多年轻的作家不明白一个道理,你写的作品在你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人接受你,以后永远也没有人接受。”[9]余华的辩解看似合理,但恰恰暴露出先锋小说作家对市场的迎合和妥协。
抒情化的文体在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中得以发展,自然和现实生活也是紧密联系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土开始沦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道德的严重滑坡,许多传统美德和传统价值遭到抛弃和颠覆。面对这种“文化失范”的状态,乡村题材小说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即拒斥城市文化,展示人文精神的失落、揭示商业文化弊端、固守传统文化。例如张炜热切地呼唤野地精神,严厉地谴责工业文明的粗暴无情:“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将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10]这些,正是作家面对现实生活真实强烈的情感反应。还有一批作家以一种远离现实的姿态对乡村进行刻意书写。他们有意撇开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而用浪漫温情的笔调去展示封闭、自足、诗意的乡村生活,表现出对现代化的否定和排斥。因此,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抒情,1990年代小说的抒情化则比较多地向现实方面转化,和现实紧密相联。无论是贾平凹的《高老庄》、《秦腔》、张炜的《柏慧》、《外省书》对现实的直接批判,还是刘庆邦、石舒清、郭文斌对乡村田园美和道德美的讴歌,作家们都不再像废名、沈从文一样去探求乡村文化的哲理和文化生命力,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乡村文化的现实命运,对正在消逝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充满追怀和惋惜。
三、问题与可能
应该说,乡村题材小说的这些文体特征都有着积极的文学史意义,体现出作家在特定的年代独特的艺术追求,非常值得尊重和肯定,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说,乡村题材小说的这些文体特征又存在诸多问题。正因为如此,文体特征的不足限制了乡村题材小说所能取得的艺术成就。
首先,我们来看看狂欢化的文体。小说的狂欢化高度契合转型期的中国现实,作家们普遍想通过狂欢化叙事反映出当下中国狂欢化的现实,由此批判狂欢化时代人性的异化和堕落。但狂欢化叙述却未达到预期的美学效果,根本原因是这些写作已经偏离了“狂欢美学”的精神本质,沦落为纯粹的形式游戏。作家们对狂欢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外部层面,而没有抓住其精神本质。尽管“狂欢”具有“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化、无我性、反讽、种类混杂”等特征,但它的核心要义是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对蕴藏于民间的“边缘状态中生命意识”挖掘和肯定,以及由此形成对权威、专制话语的解构和批判。从外在看,作家们几乎熟练借用了狂欢所有的元素:从体裁上对怪诞民间故事的戏仿,到表现手段上对诙谐、对话、杂语和傻子视角的借用;从环境描写上对富有象征意味广场的建构,到人物刻画上对傻子、白痴的描摹。但由于缺乏狂欢精神的支撑,他们的写作不自觉滑向一场无主题、无主体、喧闹狂欢而又六神无主的游戏实践。有的小说在琐碎的叙事中大肆狂欢,缺乏必要的节制和凝练,思想深度明显不足(如《生死疲劳》、《万物花开》等)。有的小说放纵于欲望景象的展览,大量堆砌离奇的情欲故事,整个写作与大众文学并无二致(如《兄弟》等)。有的小说在插科打诨、无所顾忌的调侃和反讽中拼贴历史,缺少对历史起码的尊重和敬畏,在过于冗长的多元叙述中,历史的真相已变得模糊和暧昧(如《花腔》等)。有的小说缺少明确的价值立场,对一些违背人伦和常情的罪恶行为缺乏必要的批判,作品不能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如东西的《后悔录》等》。对此,有批评者指出:“在具体的实践中,尤要警惕写作狂欢变为抽象情感和思想的纯形式狂欢,或是放弃写作难度满足于低级故事的大量结撰。”[11]只有深刻领悟狂欢的本质,才能写出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狂欢品质的作品。
其次,我们来看看故事化文体。读者对文学消费的核心是追求好看的故事,乡村题材小说文体的故事化是市场经济社会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故事之外,文学还应有其他的追求。对故事的单纯追求,给乡村题材小说小说创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人物形象的模糊。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虽然为我们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始终是模糊不清的,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映象,读者再也看不到像阿Q、孔乙己、翠翠、陈奂生、高加林这些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深刻映象的鲜活人物。小说中人物的消失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我想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作家一味追求故事所致,而把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在了次要位置。小说中的人物如同舞台上的道具,往往被故事情节裹挟着前进,故事常常淹没了人物。其次,小说意蕴薄弱。意蕴是深潜于文体和形象之中又漫溢于其外的韵调、情感、思想和精神。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艺术作品“要显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蕴。”[12]作品的故事化,客观上决定了作者在创作时,往往只能将丰富的生活窄化进故事之中,一切都是按照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来演进,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很难寄托深厚的文化内涵。比较现代文学时期鲁迅、沈从文和萧红在他们作品中寄寓的深层文化精神,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往往局限于就事写事,没有深入和超越于生活的深远人文内涵和文化进行思考,一大批小说都有着充当时代传声筒的倾向。虽然小说写得很精彩好看,但作品的意蕴却显得比较直白和浅陋,有着“问题小说”的嫌疑,结果导致了小说审美性的严重缺失。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抒情化文体。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是与人的情感分不开的,审美在希腊文中原本就是相对于理性的感性的意思,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理性的根本特点就是情感的渗透和介入,对于真情实感的发现一如科学规律的发现一样难得。乡村题材小说的抒情化应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是作家对当下物化现实的否定和反抗,试图为现代人营造出心灵的栖息地。但问题是许多小说是为了抒情而抒情,缺乏深层思想的介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文而造情”,甚至发展成为滥情和矫情。除了少数作品(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有深刻的思想统领外,我们很难找到像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在《故乡》结尾处将心灵世界和思想世界融为一体含蓄深沉式的抒情,也难以找到像沈从文在《边城》中表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相处冲淡平和式的抒情。一部分小说的抒情因缺少哲理内涵而显得肤浅轻浮,还有一部分小说的抒情因缺少冷静的沉思而显得浮躁凌厉。像《亲亲土豆》(迟子建)、《梅妞放羊》、《吉祥如意》、《柏慧》、《外省书》 等一批作品都存在这种倾向。其实,抒情与矫情和滥情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深层思想的有无,矫情和滥情往往是在感觉表层滑行,而杰出的抒情则表现出深刻的人格和哲理底蕴。这里要特别提到张炜。张炜是1990年代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抒情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一直以一个“大地”和“田园”的守护者而自居。然而遗憾的是,在张炜的作品中,绝望咒诅式的抒情掩盖了对大地爱的澄静的表达,呈现出狂躁、激动,缺乏应有的冷静和深沉。究其原因,是张炜对现代化的一味拒绝和排斥,从而抒情中缺乏深切的哲理和冷静的表达。
乡村题材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文体特征既是其自身艺术发展的规律,更是时代语境对其渗透的结果。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文体之所以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我想根本原因是作家只关注文体的外部形式,而缺乏对内涵的建设(如批判精神、价值立场、意蕴、深层思想、理性精神等)。因此,作家要有超越所处时代的胆识和勇气,不断加强自己的理论和文化修养,不但要善于继承,还要勇于开拓,不但要为市场和当下写作,更要为心灵和艺术献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有意味文体”的目标,乡村题材小说才能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注:
①具体可参见陈思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②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洪治纲的《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周保欣的《底层写作:左翼美学的诗学正义与困境》,《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史竟男的《“底层文学”:乡土叙事新景观》,《人民日报》2009年9月1日。
[1]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A].巴赫金文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5.
[2]贺仲明.论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6).
[3]苏童.关于迟子建[J].当代作家评论,2005,(10).
[4]格非.文体与意识形态[J].当代作家评论,2001,(5).
[5]张清华.混乱与我们时代的美学──余华访谈录[J].上海文学,2007,(3).
[6]关仁山.小说要好看[J].章回小说,2001,(3).
[7]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2.
[8]苏童.关于创作,或无关创作[J].扬子江评论,2009,(3).
[9]余华,张英.文学不衰的秘密[J].大家,2000,(2).
[10]张炜.融入野地 《九月寓言》代后记[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340.
[11]谢刚.狂欢式写作──新世纪长篇写作现象之一瞥[J].长城,2009,(3).
[12]黑格尔.美学(第 l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novels stylistic features of formation
Qu Hua-bing
(Tongling University,Tongling Anhui 244000,China)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the rural novels of the formation of a series of stylistic features.At the same time,the rural novels of the stylistic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there are many problems.Rural novels of writers have to go beyond the times of boldness and courage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ir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enrichment,in order to create good village novels.
urban context;rural novels;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problems and possible
I207.42
A
1672-0547(2012)01-0084-04
2011-10-12
瞿华兵(1978-),男,安徽枞阳人,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系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意象的研究》(编号:2008sk27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