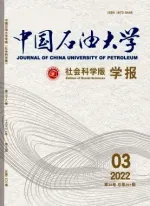朱子“格物”理论中“知”的特点
2012-08-15冯晨
冯 晨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山东济南250103)
朱熹对《大学》中“格物”、“致知”思想的解读已被众多学者所研究。本文欲从朱子格物思想本身的特点入手分析朱子“知”的特点,以期得出朱子心之理和物之理的关系。朱子“知”的特殊性隐含在他的理论模式中,要理解朱子“知”的特点,就必须先对朱子的“格物”说加以分析。
一、朱子“格物”的特殊涵义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子训“格”为“至”:“格,至也。”[1]4又说,“格,犹至也。”[2]283不论是“尽也”还是“至也”,都是“追穷”的意思。既然是追穷,就是要探究某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朱子说:“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2]283因此,朱子所谓格物,不是追穷物本身,而是要探求物中之理。因此,按照朱子“格物”之说,我们发现两层意思:一是物莫不有理;二是物中之理不是自现的,需要我们通过功夫去求索。
为了更好地说明格物之意,需要首先分析什么是物。朱子认物为事,“物,犹事也”[1]4,这和郑玄对物的解释是相同的,郑玄对格物作注曰:“物,犹事也。”[3]事必须和人有关系方为事。因此,以“事”来解“物”,不论此物是实体还是仅仅作为人际之间无实体的意义规定,此“物”一定带有人所赋予的意义,否则此物就难以成为“物”了。正如《中庸》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与“物”的关系,最终是人于物的关系,无诚,即物的意义就不存在。
格物,是穷究物中之理。物与人有关,那物中之理也与人必然有关。那么,朱子之格物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首先,物中有理,对理的认识能力为心所有。这是逻辑之必然。如果物中之理自在,那么,物与人的相关就是外在的。这种外在的相关性,是无法说明物的“事”的意义的。只有心有认识物之理的能力,才会理解物的理。如果物不与人相关,此物中的理如何探求呢?同时,心对物的认识能力是心的特点造成的,“盖人心至灵,有什么事不知,有什么事不晓,有什么道理不具在这里。”[2]264通过这句话,我们就会发现朱子之心的认识能力的特点了。“人心至灵”,说明心有知与晓的能力,这是通常意义的认知能力,但是,后一句“有什么道理不具在这里”是关键的。这说明,心之所以有知的能力,在于心中已有理具于心。此理也作为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朱子也表达过此种意思:“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乎至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7“因己之理而益穷之”就是说以我心中之理作为发现事物之理的基础。同时,当事物之理被我心穷尽的时候,我心之理也更加明晰,其对事物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也进一步提高,以至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其次,物中之理与心中之理必须是一理。虽然从朱子“理一分殊”的宇宙观中也能直接得出物之理和心中之理为一理的说明,但是,这种说明对分析格物的特点没有意义。因此,我们从实践中心和物的内在关系来说明物之理和心之理为一理的原因。
朱子曾经说过格物的目的在于穷尽事物之理。为什么要穷尽事物之理?朱子的学问的重点显然不在于对事物本身之探索,而在于明心见性,以见天理,从而存天理、灭私欲。因此,事事物物中的理与我心中的理应该是一致的,否则,格物对致知无益,对我心之“明明德”也没有作用。朱子对此有过较为明晰的说明:“致知、格物,大学中所说,不过‘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古人小学时都曾理会来。不成小学全不曾知得。然而虽是‘止于仁,止于敬’,其间却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为仁者,敬必有所以为敬者,故又来大学致知、格物上穷究教尽。如入书院,只到书院门里,亦是到来,亦唤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书院筑底处,终不是物格、知至。”[2]252)心中之理虽然已具,但是,落于气质,并非尽显,需要进一步求得其“所以然”,即“仁必有所以为仁者,敬必有所以为敬者”。因此,格物之功,在于明究我心之理之所以然。然而,理之所以然如果一味内求,就会流于玄虚,有禅学之嫌疑,这是朱子所大加批判的。因此,求理之所以然的功夫当须落实,即从格物开始。
心中之理如果不应用于事物,则心之理仅仅是一种潜能,其所以然也未知,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对人伦日用的不断应对才能发现此理之所以为理的根据。如孝之理,须在生活中以尽孝之具体的事中探寻孝之理的所以然,孝在当下生活中体现了爱亲敬长之意,此义即可以作为心中之理成立的理由。也就是说,心中之理需要通过道德实践以发现其有效性和合法性,从而为其理寻找到意义所在。因此,朱子心中之理虽然和物之理在性质上相同,但是其存在的形式不同。一个是作为与物不杂的理,一个是作为物中之理,两者因为物的特殊意义而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
基于以上分析,再看朱子格物之“格”字就会发现,格,是心之理与物之理的“交汇”,是心中之理和物之当然之间相互印证的过程。
二、朱子“知”的特点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的关注点就会很自然地落于一个问题上:既然格物是要探寻我心之理的所以然,那么心中之理是不是没有得天地之正而要通过格物之功去完善?显然不是。心中之理虽然具在,但是,天理落于人心,受到气质之影响,天理无法尽显,这就需要通过格物的功夫以去人欲之私而使天理彰显。
格物之功要具体落实首先是从作为主体的我开始的。朱子说:“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2]284因此,格物应该先从自身“理会”。只有自己有所理会了才能再去格身外之物,否则,没有一个明白的认知主体,如何去理会物之理,因此,朱子说:“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后渐渐推去,这便是能格物。”[2]284格物,应该是由己到物,一步步格去。关键是自家心内需要有对天理基本的感悟。朱子所言的“自家”是心。
心在朱子那里虽然是形而下者,但是,是气之灵者。因此,心具“知”的能力。“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1]7心知的能力表现在对物之理的探究上,理有未穷之时,说明心的能力也有未发挥全尽的地方。这说明两点:一是事事物物都有其所以然,待我心去发现;二是我心所具之理对我心来说有未明处,需要发明。既然事事物物都有其所以然,所以然之理与我心之理又是一理,因此,通过格事物之理就可以明我心之理。
但是,要去发现事物之理,如果没有一个开始的标准,事物之理如何被确定是物之所以然?因此,我心就不是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去发现事物之理。如果以我心所知之理验证事物之理,就能以事物之理察识我心之理。如此往复,最终会使得“我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因此,“气之灵者”之心所能“知”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有自己的判断依据。
同时,由以上之分析得出,心对物的判断的性质非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的标准来源于事物自身,是从事物自身中归纳出一种普遍的标准作为衡量个体事物的尺度。但是,价值判断所依据标准的来源往往是一个形式上的主体,否则,对善与恶的来源的拷问就会把其来源无形中纳入因果链条,导致无穷倒溯。因此,关于道德判断的来源的寻求要么终止于先天,要么终止于一个无上的权威。在我们的传统中,道德的来源往往是天,这一点,从朱子对《大学》中“明明德”一语的解释中就看得分明。他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居众理而应万事也。”[1]3“明德者”,是指我心,是用来应对万事万物的,而“明德”是一种先天的能力,其应对事物的能力是根源于心中之天理。因此,“格物致知”之“知”是对事物的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虽然,由于朱子对心有不同的界定,导致我们对心的功能的理解上有困难,但是,心之知不是单纯的认知这一点是确定的。因为,认知是关于事物真与假的事实判断,无关事物的价值。我们已经发现,朱子要求心能“明明德”,并且说“凡自家身心上,皆需体验得一个是非”[1]3。这样的心也就不是单纯的认知之心,知也就不全是认知意义上的“知”了。
既然格物含有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紧密相关,那么,心如何能知物之是非?
朱子认为,仁义礼智之理自在内心,“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目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求寻,仁义礼智是也。”[2]285因为心具众理,是与非就是心运用理则对事物作出的判断。但是,自身所具有的众理,我们如何而知?显然,朱子对仁义礼智存于心是肯定的,这种肯定的信心何来?孟子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朱子显然是继承了儒家这种道德体悟方式。在此,我们不得不给朱子这种意义上的“知”一个说法,叫做“体知”。
所谓“体知”,完全是心的自我感悟,无需借助于外在的事物而有的“知”。否则,怎么会在早晨睁开眼,仁义礼智就摆在那里呢?因此,这种知具有认识的基础意义,如果没有“体知”,就没有作为格物的基本标准,那么,又如何判断事物的是是非非呢?又如何在事物的是是非非中求得我已知之理的所以然呢?自我感悟出的理则,是自身作为格物的标准,不须外求。有了仁义礼智之理的基础,格物之格才有定向,否则,事物于当前,我如何知它的是非善恶,其理又如何被格得?于是,朱子说:“格物,先从身上格去。如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须从身上体察,常常守得在这里,始得。”[2]285朱子所谓的“体察”,如果作为知一种形式的话,就是我们所言的“体知”。
有了因体知得到的格物之最基本的标准,就可以“渐渐推去”,去格事事物物之理。这也就是朱子所申明的“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道理。此“已知之理”,作为源头之知,其来源非“体知”之说不足以说明之。
因此,朱子之格物,不是去看事物的黑白、大小,不是去求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在事物背后寻找一个应该如此的根本理由,也即事物之理。物之理与我心所具之理同,因此,可以因物之理去体会我心所居之天理。如牟宗三所说的,“朱子说格物之主要目的是在就存在之然以推证其超越的所以然”[4]386。这个“超越的所以然”既是物之所以然也是我心所感之理的所以然。我心之理和万物之理因此而具有了同一性。朱子说:“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至于敬。又更上一著,便是穷究的为人君,如何要止于仁;为人臣,如何要止于敬,乃是。”[2]284朱子的格物过程中,认为事物“当如此”、“当如彼”的态度,就已经为事物赋予了意义,这种意义,貌似事物之本有之义,也是事物的本具之理,但这理和心居之理的要求是一致的,如,“事事物物上各有个是,有个非,是底自家心里定道是,非底自家心里定道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是是,非底定是非。”[2]285当然,心的这种力量,来源于心中存有的仁义礼智,这是心能格物的条件和基础。
因此,格事事物物之理的过程,其实是“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心之灵所体知的是非标准去求索事事物物之理。这时,物被心评判,物因自己的特性表现为自身的美丑、好坏、善恶。事实上,其善恶美丑是因为我心本具之理对之作用的结果。朱子说:“圣人之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2]287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事物之若静若动所表现的天理人欲是人因心的评判而来,因此说,事物的价值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我心的标准落实于事物和被事物检验的过程,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知的过程。如果给这个过程界定一下,根据其特点,可以称其为“推知”。
体知,是就自我之心来说的,是心的自我体察之知,此不假外求。推知,是就心之外的事事物物来说的,是在事事物物上去寻找个所以然之理,是心带着是非的标准去求的。
三、心被作物格的可行性
朱子之格物是要显现心中之天理,因此,朱子的知,是在事事物物上求得一个个所应有的理,如散兵攻城,到一定功夫,心豁然开朗,天理尽显。如果使这气质之性中的天理尽显,就需要以事物作试金石。在格物中,也就是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天理和人欲在事事物物中显现出来,天理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人欲之私意形成对决,从而使天理昭彰。这个过程,不仅为心中之理找到一个显现的机会,也为其找到了意义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心之所感之理和其所居之理就不能完全为一。
朱子以把对心中所居之理的体察作为其格物的开始,一旦开始,朱子就走得较远,即把心本身也作为了推知的对象。他说:“格物者,如言性,则当推其如何谓之性;如言心,则当推其如何谓之心。”[2]284但是,这样做从逻辑上说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因为心对其中所居之天理难以完全发明出来,要以心对此所居天理的体知去推知心之所以然之理,心之所以然之理是心的明明德之所以然,这就需要为心的存在提供说明。那么,心的所有的表现,包括其对自己的推知之能力也要有一个所以然的理的说明。这样就造成一种无谓的倒溯。如果我心对其中所居之理已经体知得明白透彻,那么,推知就变成我心之知推知我心之理,这是无意义的。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在‘推究如何是心’处,无论推究其超越的所以然,或是推究其为存在之然自身之曲折而说出一个定义,要皆有格物之实义,……它(性)本身即是超越的所以然,故再不能复推证一‘所以然’以然之。”[4]386
如果把心作为反观而产生的物,那将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因为,反观的能力来自于作为认识主体的心,此心之灵反观自身所“发现”的心已经不是本然意义上我们体知而得的心。反观后所产生的心是根据我心之表现而建构的一个心,这个心与体知而得的心性质完全不同。体知而得的心是心本身所显现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说,体知即是心中之理在表现本身。因此,如果把体知而得的理作为天理,推知的对象为建构的心,然后在这个建构的心上去寻求所以然,就会避免逻辑上的无穷倒溯。
那么,朱子所言的被作为物来格的心是否是建构意义上的心呢?为了说明这一点,可分析朱子心的特点。朱子言心,是指“心统性情”之心,性和情为心所统摄。心为气,天理之在人心是居于人心,而不是与心为一。基于这个特点,朱子的心之灵的功能更多的是对心之理发动后的效果的体会,而不是在理起动处体察。如《朱子语类》记曰:“傅问:‘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发见理会得否?’曰:‘公依然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且如见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便是发了,更如何理会。若须待它自然发了,方理会它。’”[2]286待心发了之后再去理会,显然是落后了一步。以此,我们体知到的天理,非心之所居之天理本身。
虽然心所体知的对象是我心居之理,但是,是在我心居之理自然发动了之后我才能体知于它。因此,朱子心的内容是在性之已发处理会到的理。此仅仅是理的内容,已经没有道德的生发性。同时,我心也成为了理的内容的场所。这样的心,因为不是道德的生发源,也就是说不是德性的最后根据,因此可以作认知之心去被静态地反观。由此反观而形成一个被构建的心,并以此为物,以求其所以然,当无不可。
尽管朱子把心作为物格没有问题,但是,这样所得的心之所以然是心之已发之后的表现——体知之理,而体知之理的所以然为心中之天理。因此,在朱子的理论中,如果仅仅通过格我之心的方式达到我心中之天理尽显的目的,还是存在困难的。
[1]朱子.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子.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郑玄.礼记正义[M].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95.
[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3卷[M].台北:正中书局,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