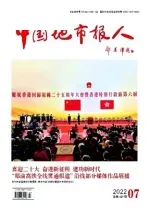小议舆论监督的发展趋势
2012-08-15冀亚凤
□冀亚凤
(漯河日报社,河南 漯河 462000)
说起“新闻”,容易引起我们联想的有两个词:一个是“监督”,一个是“宣传”。新闻监督、新闻宣传这两项工作是我们媒体人同时肩负的两大使命,缺一不可。
当下的社会,监督有着四大监督体系。这就是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的群众监督和新闻的舆论监督。这四大监督体系各有所长,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公器,具有特殊的作用。
进入网络时代,随着网民的全民化,人人都可以在网络这一新兴平台上发表个人的见解,每位网民都成为一位独立的发言人。作为自然人,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欲望因为网络这一表达平台的设立成为可能。媒体监督的功能也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泛社会化。周久耕、躲猫猫、赵作海、孙志刚等人物和事件成为这一新兴监督形式的代表。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新时期新闻事业大变革的三十年。首先是与伤痕文学同步的反思类新闻,对历史进行客观冷静的检讨和反思。这时候的典型文体是全方位展示某一社会现象的通讯类的大视角,如《唐山大地震》、《西北大移民》等;其后是直面社会阴暗面、自揭伤疤类的大曝光文章成为媒体主打,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中的文章,《大河报》上关于张金柱的报道等;之后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转型的报道,人们心无旁骛,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创造社会财富上。如关于马云盈利模式的报道、史玉柱东山再起的分析等。
最近几年,随着国际国内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我们的媒体人面临适应新社会,思维观念重构、报道方式创新的挑战。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各种敏感问题也随之出现。
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媒体人必须摒弃原来纯粹的监督者、正义者化身的角色,不能再一味地对社会品头论足、指指点点,而要成为社会进步大船上的 望者和预警员。
2009年11月底,成都市民、企业家唐福珍自焚维权案发生,如果放在10年前,可能整个媒体就是一道腔:声讨暴力拆迁者,同情以死抗争的唐女士。毕竟,面对强大的拆迁一方,唐福珍属于弱者。但事实情况是:媒体不仅对唐福珍表现出了足够的同情,对拆迁方给予无情的谴责。同时,人们更多地把眼光盯住了有违宪嫌疑的《城市拆迁条例》。造成一件件以命相争的恶性案件、群体性事件的“靠山”或者“元凶”不是别人,正是这部条例。一个“拆迁”,将双方争论的焦点由寸土寸金的城市土地变为按照建筑物面积去赔偿的物什。难以统计,一部条例制造了社会上多少的不和谐音符!同时,也正是这种反思的舆论,推进了《条例》的修订,使“城市拆迁”向“搬迁”迈进。
我们不会忘记,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本是我国的一个省级建制的行政单位内部发生的一起有预谋的事件,结果受到各种国外媒体、团体的别有用心的关注。多亏了国家及时实施互联网管制、欢迎境外媒体实地采访等措施,截断了谣言传播渠道,使得事件及时得到平息,国际舆论也最终成为可资利用的力量。
政府越来越开明,问题越来越多;时代越来越敏感,处理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人人都是媒体人,但每个人的发言都不权威。这就是我们媒体人所要面对的现实。
这样的媒体生存环境让我们想起了一则故事。
古代一位高明的民间医生和一位御医相遇。民医问御医:我们都是救死扶伤,我是民医而你是御医,你说民医和御医有什么不同?御医回答:你在给人治病时只求治好病,别的什么都不考虑;我在给皇上治病时不但要考虑治好病,还不能让皇上有痛苦。这就是咱们的不同。
一语中的!尽管我们常说苦口良药利于病,但如果药太苦,病人仍然不愿意吃,甚至因此把病情给耽误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最为妥当的办法就是给药裹上糖衣,让病人无痛苦地服下。
御医有着让普通民间医生艳羡的地位,但也担当着难以预料的风险:一旦在治病的过程中让龙体有了痛苦感,可能就有性命之虞。因此,御医在治病过程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理可以感同身受。
作为新时期的新闻从业人员同样需要御医这种心态。不是为某个人,是为了适应整个社会对新闻工作的需求。
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风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风险。我们已经走过了“上级让说什么,媒体人说什么;媒体说什么,社会听什么”的时代,更多的时候是大家都在说,分不清谁是职业媒体人、谁是业余的,分不清谁的权威独家、谁的是流言蜚语道听途说。这对我们媒体人的政治素养和敏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和鉴别力,就有可能被人利用,被所谓的民意所裹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权威风险。我们已经知道,网络时代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说,作为职业媒体人要说到点子上,说得让大家口服心服,就要有足够的权威的对新闻事实的掌握,有严谨的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分析,有科学的对事件性质的评判。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过硬的新闻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正如大家同时身陷险境,你要让大家都听你的,相信你能带领大家走出险境,就要有足够的智慧和人格魅力。
权力风险。我们已经习惯了面对负面新闻,地方媒体和外地媒体截然不同的两个态度:地方媒体集体噤声、外地媒体不依不饶。集体噤声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认为负面新闻都是家丑,家丑不能外扬;外地媒体不依不饶是因为他们觉得要报道事实真相,地方官员的意志无法强加于他们。即便如此,本地与外地本身就是逻辑学上的一组模糊概念,把握不好,仍然有轻者受批评、受处分,重者调离工作岗位的风险。准确拿捏负面新闻的曝光度,并非易事。
跟风风险。网络时代的新闻与传统媒体的新闻时代的显著区别就是新闻传播的瞬间效应。无论是非曲直,只要是网友感兴趣的,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新闻,都会被热情的网友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开来,很少有纠错的时机。这对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新闻事实,来不得半点的“可能、也许、似乎、大概”。一旦出现闪失,造成的负面影响绝非个人努力能够挽回。
相对于互联网理论上没有数量上限的网友,和他们的热情、敏锐、冲动、跟风以及几乎无所不能的“人肉”手段,作为传统媒体人,所谓的新闻舆论的工作内涵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大众传播方式,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将以往惯常使用的监督社会下发为引导舆论,成为舆论羊群中的领头羊,解放大军中的先导部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的舆论环境,才不至于被网络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