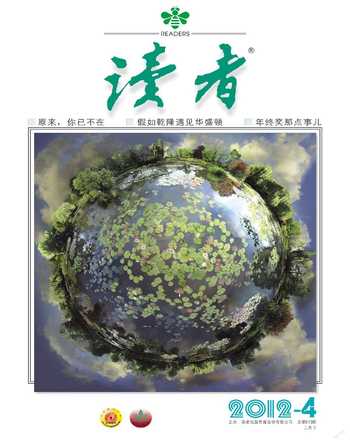老驼的喘息
2012-07-04梁晓声

“文革”中我从大字报汇编中得知,有人通过画骆驼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丑化”,偌大的画曾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画上的三头骆驼看上去有些瘦,也有些疲惫。我觉得恰恰是那样,画出了骆驼的坚忍性格。但批判者们似乎偏爱肥壮且毛色光鲜的那一类骆驼。他们莫须有地指出,将骆驼画得那般瘦、那般疲惫,还要命名为“任重道远”,不是居心“丑化”党和社会主义才怪了呢!
故在当年,我一看到“骆驼”二字或联想到它,心底便生出几分不祥之感来。
后来我下乡,上大学,加起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竟再没见到“骆驼”二字,也再没联想到它。
三头骆驼屹立在风中,也从十几米外望着我们。它们颈下的毛很长,如美髯,在风中飘扬;驼峰很挺,不像我在动物园里见到的那样,驼峰向一边软塌塌地歪着;都昂着头,姿态镇定,使我觉得眼神里有种高傲,是介于牛马和狮虎之间的一种眼神;但皆瘦。事实上人是很难从骆驼眼中捕捉到眼神的。我竟有那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大约是由于它们镇定自若的姿态给予我那么一种印象吧。
有人说,骆驼天生是苦命的,野骆驼比家骆驼的命还苦,被家养反倒是它们的福分,起码有吃有喝。
还有人说,这三头骆驼也未必就是名副其实的野骆驼,很可能曾是家骆驼。主人养它们,原本是靠它们驮运货物来谋生的。自从汽车运输普及后,骆驼的用途渐渐少了,主人继续养它们就会赔钱,得不偿失,反而成负担了。可又不忍干脆杀它们吃肉,于是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趁它们不注意,搭上汽车走掉,便将它们遗弃了,使它们由家骆驼变成了野骆驼。骆驼的记忆力是很强的,是完全可以回到主人家的,但骆驼又像人一样,是有自尊心的,它们能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宁肯渴死、饿死、冻死也不会重返主人的家园。但它们对人毕竟有了一种信任,即使成了野骆驼,见了人还是挺亲的……
果然,三头骆驼向吉普车走来。
最终有人说:“咱们车上没水没吃的,别让它们空欢喜一场!”我们的车便开走了。
那一次在野外近距离见到了骆驼以后,我才真的对它们心怀敬意了,主要因为它们的自尊心。动物有了自尊心,虽为动物,在人看来,便也担得起“高贵”二字了。
不久前,我在内蒙古的一处景点骑到了一头骆驼背上。那景点养有一百多头骆驼,专供游人骑着过把瘾。它们一头连一头,连成一长串,集体行动。我觉着有东西拱我的肩,勉强侧身一看,见是我后边的骆驼翻着肥唇,大张着嘴。它的牙比马的牙大多了。我怕它咬我,可又无奈,因为我骑的骆驼夹在前后两头骆驼之间,它们连在一起,我想躲也躲不开它。倘它一口咬住我的肩或后颈,那我可就惨啦。我只得尽量向前俯身,却无济于事。骆驼的脖子那么长,它的嘴仍能轻而易举地拱到我。有几次,我感觉到它柔软的唇贴在了我的脖颈上,甚至感觉到它那排坚硬的大牙也碰着我的脖颈了。倏忽间我于害怕中明白它是渴了,它要喝水。而我,一手扶鞍,另一只手举着一瓶还没拧开盖的饮料。我当然是乐意给它喝的,可驼队正在波浪般起伏的沙地间行进,我不敢放开扶鞍的手——如果掉下去,会被后边的骆驼踩到。就算我能拧开瓶盖,也还是没法将饮料倒进它嘴里——那需要有好骑手在马背上扭身的本领,我没那种本领。我也不敢将饮料瓶扔在沙地上由它自己叼起来——倘它连塑料瓶也嚼碎了咽下去,我怕锐利的塑料片会划伤它的胃肠。真是怕极了,也无奈到家了。
还好它不拱我了。我背后竟响起了喘息之声——那骆驼的喘息好似人的喘息,如同负重的老汉紧跟在我身后,又累又渴,希望我给“他”喝一口水。而我明明手里拿着一瓶水,却偏偏无法给“他”喝上一口。我做不到的呀!
我一向以为,牛、马、骡、驴,包括驼和象,它们不论干多么累的活都是不会喘息的,那一天、那一刻我才终于知道我以前是大错特错了。
既然骆驼累了是会喘息的,那么一切受我们人类役使的动物肯定都会的,只不过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罢了。举着一瓶饮料的我,心里又内疚又难受。
那骆驼不但喘息,而且还咳嗽了,如同人的咳嗽,又渴又累的老汉的咳嗽。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骆驼的咳嗽声……
一到终点,我双脚刚一着地,立刻拧开瓶盖要给那头骆驼喝饮料。偏巧这时管骆驼队的小伙子走来阻止了我,因为我手中拿的不是一瓶矿泉水,而是一瓶葡萄汁。
我急躁地问:“为什么非得是矿泉水?葡萄汁怎么了?怎么了!”
小伙子讷讷地说,他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总之饲养骆驼的人强调过不许给骆驼喝果汁型饮料。我问他这头骆驼为什么又喘又咳嗽的,他说它老了,说它是旅游点买一整群骆驼时白搭给的。我说既然它老了,那就让它养老吧,还非指望这么一头老骆驼每天挣一份钱啊?小伙子说,你不懂,骆驼是恋群的。如果驼群每天集体行动,单将它关在圈里,不让它跟随,它会自卑,会郁闷的。而一旦那样,它就容易病倒……
老驼尚未卧下,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瞪着双眼凝视我,说不清望的究竟是我,还是我手中的饮料。我经不住它那种望,转身便走。
我们几个人中,有著名编剧王兴东。我将自己听到那老驼喘息和咳嗽的感受,以及那小伙子的话讲给他听,他说他骑的骆驼就在那头老驼后边,他也听到了。不料他还说:“梁晓声,那会儿我恨死你了!”我惊诧。他谴责道:“不就一瓶饮料吗,你怎么就舍不得给它喝!”我便解释那是我当时根本做不到的,我有严重的颈椎病,扭身对我是件困难的事。他愣了愣,又自责道:“要是我骑在它身上就好了!你当时做不到的,我能做到,我骑过多次马……”我顿时觉得他可爱起来。
几个月过去了,我耳畔仍常常听到那头老驼的喘息和咳嗽声,眼前也总是浮现它凝视我的样子。
由那老驼,我竟还联想到中国许许多多被“啃老”的老父亲老母亲们。他们之所以被“啃老”,通常也是因为儿女们的无奈。但,儿女们是否也想到他们手中那瓶“亲情饮料”,正是老父老母们巴望饮上一口的呢?在日常生活中,那是比在驼背上扭身容易做到的啊!
中国许许多多的底层民众,他们渴望被关怀的诉求往往像一瓶“责任饮料”,握在各级官员手中,而官员们是否乐于为民众解渴呢?那往往比在驼背上扭身难不到哪儿去。即使难,做不到,他们会为此内心不好受吗?
天地间,倘没有其他的动物,自远古时代便唯有人类,我想,那么人类在情感和思维方面肯定还蒙昧着呢——万物皆可使人开悟啊!
(师蕊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