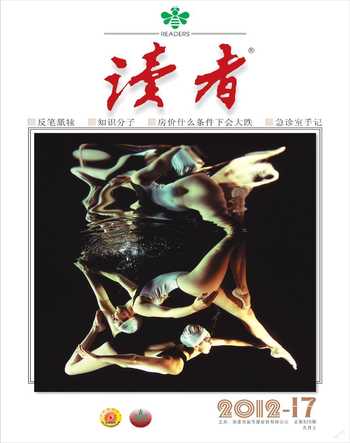我总是无法缓和自己的呼吸
2012-07-04尉克冰
尉克冰

1
二爷叫尉新泉,牺牲于1948年4月。那年,他17岁。
前段时间,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两本日记。一页又一页的纸,被时光打磨得斑斑驳驳,被岁月点染成了暗黄色。二爷就安睡在日记里,不曾离去。
真不敢相信,那些日记是二爷10岁时写的!单看那隽秀挺拔、飘逸灵动的毛笔小楷字体,就难以想象它们出自10岁少年之手。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着那一张张泛黄的宣纸。战乱是那个年代的音符,年幼的二爷,就是在硝烟滚滚和炮声隆隆中坚韧地求学。
二爷的日记,字字如泣如歌,落在我心头。
2
“现今,正在世界纷乱、国际惶荡的时候,物价腾贵,谋生艰难。我所在学校使用的笔墨纸砚,比别处价高。我手文钱缺乏,着实痛苦。为此,我少写些字。一天两张大楷,一张小楷。此外,一片纸也不能浪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战乱中的孩子早成熟。
“我们做事,要立志向,养成忍耐的性格。好逸恶劳绝不会有什么成就。汉朝匡衡,凿壁借光,多么坚韧耐苦。现在,我们坐着杌子,在教室里,如果不好好读书,对得起家长吗?”一篇短短的日记,折射出二爷发奋读书的决心。
二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业的落后,民生的凋敝,他尽收眼底。他写道:“其实,农村生活是一种最辛苦,也是一种最愉快的生活。我们假使将农村组织进行改良,那么,农民自然安居故乡了。”
一个人,在苦难的生活中,关注的不是自己,而是劳苦大众,这个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二爷正是这样。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我要劝大地主们,你们不耕自食,还不发些慈悲,减轻些田租?”
国有内忧,更有外患。外邦入侵,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二爷心事凝重。
“国为公共的,不可不保。虽云保国,而需忠勇,还要同心。如此,国家何不安哉?”“两鸡斗时,四目对射,至死不退,非常勇敢。国家的兵若能如此,我国何能亡?”二爷既习文,也习武。他要练就一副强壮的体魄,驱赶外敌,报效祖国。每天,天还未亮,他就起床练功了。耍刀,舞枪,挥拳,弄棒,抓举石锁,练习跳跃本领。一米多高的平台,他双腿齐跳,纵身而上;两米宽的壕沟,他腾空而起,一跃而过。他结实健壮的身体里,积蓄着无限的能量。
可惜,他只是个孩子。尽管一腔郁郁如裂帛,但他只能饱蘸着忧伤的泪水,把孤独和愤懑写进自己内心深处。
冷酷绝情的时代,将二爷读书报国的美好梦想,一点一点,撕成碎片。
“光阴似水,不知不觉,我已读书三年了。我心实愿升学,可惜,家庭狭小,经济困难,父母不叫。我无奈何。只得安慰自己做商,发展吾国之工商业。”
1941年冬季的一天,二爷上完了他的最后一堂课。那天晚上,二爷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3
1945年9月,家乡解放,日本侵略者被彻底赶走了,全中国都在庆祝抗战的胜利。二爷高兴地在街上狂跑着,跳跃着,放着鞭炮,唱着歌儿。
那年,二爷14岁,经人介绍去了一家中药铺做小伙计,负责抓药。他个子小,够不着上面的药抽屉,就站在凳子上。可他做起工来,毫不逊色于大人。郎中的字多数写得龙飞凤舞,他也能辨认清楚。待到不忙的时候,他还能帮老板打理账目,噼里啪啦,打得一手好算盘。老板好生喜欢!
二爷心里也在打着算盘。他白天做工,夜晚用功。他在钻研《本草纲目》,他要学中医,过几年自己经营一家药铺。有了经济基础,他再开一家纺织厂。他要踏踏实实,朝着自己“发展吾国之工商业”的目标迈进。
可是,灾难一重接一重。赶走了日本人,又来了内战。
1947年,解放军为攻取山西太原,进一步扩充兵员,从晋冀一带农村征兵。征兵名单里,有我爷爷,也就是二爷的大哥。
那一晚,二爷失眠了。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替哥从军!大哥憨厚、木讷,自己精干、强健,更适合当兵。从小就有雄心壮志的二爷觉得,这也是实现理想、报效祖国的好机会。
那年,二爷年仅16岁。告别新婚的妻子,他毅然奔赴前线,成为十三纵队三十八旅旅直工兵连的一名战士。
硝烟弥漫的战场,点燃了他少年时期的梦想。他终于可以在炮火的洗礼下,做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了。他头脑机灵、精通武术、体魄强健,深受连队领导的赏识,每次战斗,他都被派到最前沿、最危险的阵地。
1948年3月,部队从太原转战临汾。在这里,要打一场硬仗。他作为精兵,加入主攻行列。战士们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奋勇前进,一个个倒在血泊中。
战斗持续了20多天,临汾城还是攻不下,双方死伤异常惨重。
敌机在阵地上空疯狂地扫射、投弹。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血,汩汩地冒出来,顿时在他身体上盛开出一朵鲜红的花。可他依然用精神的伟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一次又一次站起来,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干,他轰然倒下!他还没有留下后代,战争的火焰就吞噬了他。
死亡,像一座黑暗的城堡,幽禁了一个又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生命。历经72天的苦战,临汾城终于被攻下了。解放军1.5万余名战士成了烈士,歼灭国军2.5万余人。
4万生命换取了临汾的解放。拼杀声、嘶喊声、轰炸声,交汇成一曲悲怆的挽歌,久久回荡在支离破碎的临汾城上空。
战士们的血氤氲成一道河流,将残阳和云朵染成殷红色,铺满西边的天空。突然,一阵狂风呼啸而来,漫卷着飞扬的尘沙,遮天蔽日。那声音,如怒吼,像呜咽,似悲吟,是在哀悼众多逝去的英魂吗?
一个人的苦难,或许容易改变,而一个时代的灾难,似乎注定了无法逃避,它需要无数生命为之殉葬。在战争面前,生命向来脆弱得如同蝼蚁,不堪一击。
就这样,年仅17岁的二爷,安静地睡去了,睡在数万战士中间。他的神情平静、安详。他知道,奔赴战场意味着什么。
4
二爷牺牲时年仅17岁。他的死和其他战友们的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奋力拼杀,倒地身亡,被临时埋葬在荒坡野岭。坟头上,一个小小木牌就是他的身份证。接到阵亡通知书,爷爷赶到临汾,在新坟林立的山岭间找了三天三夜。挖开那堆黄土,二爷依旧安然地睡着。可他的身体,早已是千疮百孔。黑紫色的血,凝固在他的军装上。爷爷抚摸着弟弟冰冷的身体,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痛哭不止。爷爷知道,是弟弟用他的死换取了自己的生!
爷爷赶着牛车,将二爷从山西接回了河北老家。沿途村庄的乡亲们得知车上躺着的是烈士,便自发为爷爷提供食宿,一程送到下一程,一村送到下一村,把二爷护送回乡。曾祖父和曾祖母在村口迎着儿子。盼星星,盼月亮,盼回的却是儿子冰冷的尸首。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他们唯一的亲生骨肉(爷爷是养子)!
一个鲜活生命的凋零,换回一张薄薄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
烈字第0018486号
尉新泉同志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在十三纵队卅八旅任战士。不幸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在临汾战役中光荣牺牲。除由我军奠祭英灵外,特怀哀悼之情报贵家属,并望引荣节哀,持此证明书向河北内丘县人民政府领取抚恤金及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其家属得享受烈属优待为荷。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贺龙
政治委员邓小平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证明的背面,是表格,登记着二爷的基本情况。几十年过去了,这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下发的牺牲证明书,已经被岁月侵蚀得破旧斑驳,静静地躺在老家的一方旧匣子里。
从1951年开始,曾祖父每月从政府领取6元钱的抚恤金,直到1984年曾祖父去世。
和以往牺牲在千百场战斗中的众多战士一样,二爷死得那样平凡普通,做了一颗通往新中国大道上的铺路石。
如今,二爷的身躯已化成一行细小的文字,躺在《内丘县志》烈士英名录中,默默无闻。他太年轻了,参军还不到半年,没有成为众人皆知的英雄。甚至,就连他的相貌我都不清楚。只听长辈们描述过他的样子,浓眉毛,大眼睛,白皮肤,高个子,敦实,英俊。时隔60余载,了解二爷的人大多已过世,二爷所留下的生活印迹都模糊成了断裂的只言片语!如今,二爷的遗物,就只有这张牺牲证明和两本日记了。
与那段苍老的岁月牵手,与那两本泛黄的日记牵手,我能感受到二爷剧烈跳动的心脏和奔流的血液,我能读懂他那颗愤懑而忧伤的心。在他面前,我永远都要仰望和跪拜。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名誉和尊严。此刻,我又想起二爷的一篇日记《说名誉》:
“常说,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人有好名誉,比当富翁还好。财帛集在手中,死去一文不见,何如名誉好,名誉留在人间,就可以百年不朽。后世人传说起来,此人有益,真可做万世的模范呀。”
5
人,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生命的尽头。有的人死去了,就意味着永世的寂灭。有的人死去了,却意味着一种永恒和超越。
瞬间与永恒没什么截然的界限。有的瞬间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有的永恒凝结在一个短暂的瞬间。
面对这样一位先人,我总是无法缓和自己的呼吸,无法释放自己的惆怅和叹惋。
我相信,二爷的逝去便是一种超越。一种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