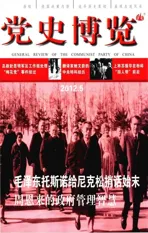李德三问
2012-06-25曹春荣
曹春荣
在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第一位也是唯一曾与红军一起作战的外国军事顾问就是李德。也正是他的错误指挥,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直到今天,关于他是怎样来到中国、来到苏区,又是怎样成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统帅部的 “太上皇”,一直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如今,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解密、公布,研究禁区和思想迷信的逐渐破除,上述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李德是怎样来到中国的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早年曾参加德国工人起义,19岁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多次被捕入狱,又多次成功越狱,后被送往苏联。到莫斯科后,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参加了苏联红军,曾任红军某骑兵师参谋长,并被选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他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以优秀学员资格被分配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李德到苏联后能平步青云,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背景,而是靠自己作战勇敢。他既富有实战经验,又具备很高的军事理论素养。所谓李德不懂军事指挥,只会照搬军事操典的说法,其实不足信。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李德究竟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真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吗?
李德自己还真是这么说的:“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但一些人不认同李德的说法。有的说,李德只是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特工,其理由不外乎他原本就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伍修权回忆说,王稼祥讲过,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在共产国际的王明派遣,来掌握中共军权的。至于王明为何会通过共产国际要来李德,则因为他迷信苏联城市暴动的革命模式,觉得中共恰恰缺少城市街垒战专家,不利于城市暴动成功,所以要求共产国际派这方面的人才去帮助中国革命,而李德便成了首选。
上述几种说法虽有种种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李德来华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受某一组织安排的。事实的确如此。但是,究竟是什么组织在什么背景下,安排李德来华执行什么任务的呢?
众所周知,中共成立的第二年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后者的一个支部。为方便就近对中共进行领导、指导和监督,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派驻有各种代表和军事顾问组。共产国际中国联络站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也一度驻在上海。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审讯之后,警方发现转递给马来西亚共产党人的经费来自上海,还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警方将此线索转告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后者很快查实与此有牵连的两处可疑地点,进而于6月15日以“特务嫌疑”罪名逮捕了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叫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十月革命时,他以“芬兰团”政委身份率队攻打冬宫。后在苏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和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隶属苏联军方情报系统。1927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其时,他有多个公开身份: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书记、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以及“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的老板。其妻汪得利昂,人称牛兰夫人,真实姓名叫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930年初携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中国联络站负责共产国际跟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之间的信息、人员和资金流转,任务重大而艰巨。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切断了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和资金流转通道,局面已是十分严峻。然而祸不单行,被国民党当局捕获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指认了牛兰夫妇。1931年8月14日,牛兰夫妇被以“国际间谍”罪名,秘密“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从上海解转南京。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打算以此为突破口,一举切断中共的国际联络渠道,摧毁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还传言要判他们死刑。
这样,营救牛兰夫妇就成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燃眉之急。这项任务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名叫理查德·佐尔格,其时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撰稿人,真实身份则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特工。他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名义,主持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组(上海工作站)工作,与中共中央和其他相关部门都建立了固定的工作关系与横向联系。1932年初,佐尔格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他在调动社会舆论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的同时,派人侦知了牛兰夫妇在南京的下落。佐尔格没有满足尚无真凭实据的信息,认为最好有个文字依据予以确认。为此,他通过自己情报网里的中国组同志,秘密接触到主管牛兰夫妇案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谈妥以3万(一说两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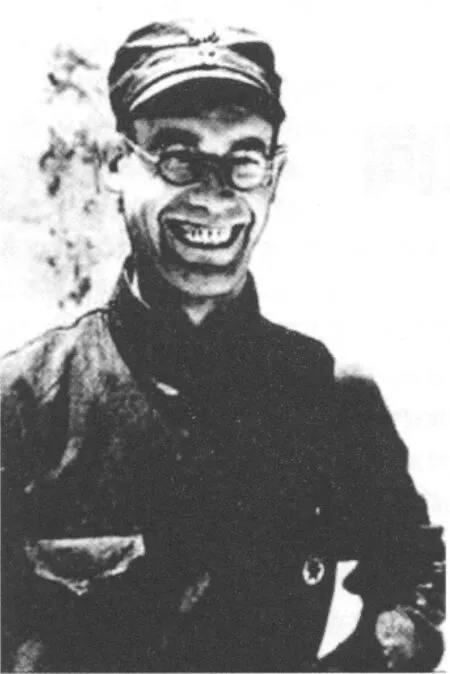
李德
佐尔格经过一番权衡,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做,但要求对方先交货。得到对方肯定答复后,他当即电告莫斯科方面,莫斯科方面迅即同意他的建议,并告知送款人已经上路。选派送款人的机关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虑及送款路线须穿过被日军控制的东北等地,而德国与日本为结盟国,因此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一名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任务。为保险起见,选派两人,每人各携带3万美元,分别取不同路线去中国。两名送款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个就是奥托·布劳恩。所幸两人都顺利完成了这项特殊使命。只是前者交付款项给佐尔格后便回去了,而后者却留在了上海。在佐尔格的精心策划下,牛兰夫妇逃过了死刑,并最终逃出了国民党的监狱,回到了苏联。
奥托·布劳恩是因为奉命给佐尔格送一笔特殊款项,来到中国的。因此前文所述他来中国是受苏军总参谋部派遣也罢,受共产国际派遣也罢,就都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奥托·布劳恩又是怎样留在了上海、留在了中国呢?照他本人的说法,当然是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不过这个说法已被史实否认。另一种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李德在上海遇见了老熟人阿瑟·尤尔特和博古(但博古否认了此事)。尤尔特其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远东局下设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组。尤尔特也是一名老资格的德共党员,且曾与李德在德国共过事。如今军事顾问组正是用人之际,尤尔特通过组织程序将李德留下,是有可能且办得到的。
李德是怎样来到苏区的
1933年9月底,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身份,从上海起程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其时,瑞金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国工农红军统帅部及中共临时中央驻地。据说布劳恩一到瑞金,就由博古“钦赐”中文名字——李德,说是姓李的德国人。这种传言不可信。可以相信的倒是“谐音说”,那便是布劳恩在莫斯科时有个俄文名字,叫做利特罗夫,“李德”就是这个名字的前两个字的谐音。这样的取名法在当年颇为流行,就像“博古”是“波古良也夫”前两字的谐音,“洛甫”是“依思美洛夫”后两字的谐音一样。李德在瑞金还取了个笔名叫华夫,用在报刊发表文章署名。
关于李德为什么会到苏区来,也有种种说法。曾在瑞金为李德做过翻译的王智涛说:“李德原来不是共产国际正式的军事顾问,他只是被那位正式顾问派来打前站的,为其进苏区探路作准备。但是李德到达后那位正式顾问却因故不能来了,这才由李德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在一定时间内仍得按上海的那位军事顾问的指示办事。”照王智涛的说法,李德“捡”了个顾问头衔。李德自己则是这样说的:“博古和洛甫动身(去中央苏区)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正准备迁至苏区,总军事顾问又指日可待,可以预料,我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一定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李德“同意”的前提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以确认他到苏区的身份和权力。为此,尤尔特和博古向莫斯科发了几封请示电报。1933年春,他们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肯定的答复: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人根据李德的自白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复电判定,李德进入苏区不关共产国际的事,是中共中央(其实就是博古)要他去的。
事实如何呢?且看当事人之一的博古是怎样说的。博古在延安时期(1943年)的笔记手稿上写道:“(我)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冬)远东局负责者爱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这几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博古与李德相识于1932年秋冬之际,且经过远东局负责人介绍。这就否定了“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了一年”的说法,也否定了李德留在上海与博古有关。其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经远东局电告中共方面,派来当军事顾问的。这表明李德去中央苏区不是他和博古的私下勾结,而是经过组织安排的。
如果说博古的自述尚不足为凭,那么看看近些年披露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就会进一步明白事情的真相。
1932年12月初,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二号报告中,关于总的工作计划部分的第十点写道:“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目在加工材料。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他那个局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下,财务方面也由我们管。”这里的“邻居”,指的就是奥托·布劳恩,“他那个局”则是指布劳恩所在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情报局)。这则电文把李德去苏区前的隶属关系、工作情况,说得既简洁又明白;也表明了派他去苏区是远东局计划中的事。
12月31日,皮亚特尼茨基给远东局格伯特的电报指示:“瓦格纳应去苏区。行前发给他每月200元的薪金和去苏区的旅费。在那儿他应从当地朋友们那里领取薪金。”这里的“瓦格纳”就是指奥托·布劳恩,而皮亚特尼茨基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当地朋友们”,显然是指中央苏区的中共同志。这则电文无可争辩地表明,李德去苏区,是奉了共产国际之命的。这也表明,假如李德把他被派往中国,是指去苏区而不是去上海,是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的,那绝对是真的。
1933年2月7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三号报告中,关于苏区的工作部分写道:“不言而喻,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当然,当他本人在那里时,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得好得多(此事正在安排中)。”这里的“瓦格纳”,依然是指奥托·布劳恩。这则电文不仅再次告诉我们,派李德去中央苏区当军事顾问是共产国际的慎重决定,而且肯定了李德的军事才干,并寄希望于李德到中央苏区后的作为。
同年3月5日,李德在上海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皮亚特尼茨基等负责同志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中,透露了他最近要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行踪。更重要的是,他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和判断,指出了中共方面对苏区及红军面临的局面、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过分夸大的估量和宣传,而这势必“造成对真实情况的错误概念”,进而提出了他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包含了他的看法与建议)。李德的这份书面报告,无形中是对上述埃韦特的第三号报告的呼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埃韦特的话。
从上述所引的几份历史文献中,我们完全可以确认:李德去中央苏区,的确是共产国际所作的刻意安排,而不是博古的个人行为。即便博古和洛甫对远东局提出了派李德到中央苏区去的请求,也不能认为这是他们之间的勾结。至于说李德“捡”了个正式的军事顾问头衔,则偏离事实甚远。
李德是怎样成为红都“太上皇”的
李德到瑞金后,很快就从一个无指示权、听命于中共中央的顾问,变成了具有决策指挥权、让中共中央俯首听命的“太上皇”。这话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当年的许多红军将帅及中下级指挥员都这么说,就不能不叫人相信了。客观地说,李德那一套脱离中国国情、红军实际的作战指挥理论,给红军反“围剿”及战略突围带来了重大损失,他难辞其咎。尤其是他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更加令人愤怒。因而人们讥讽、抨击他为红都“太上皇”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则,李德究竟是怎样成为红都“太上皇”的呢?当年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说白了,是博古的推崇纵容,使得李德掌控了红军的进退存亡。对此,博古本人也是认账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检讨过:“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应受党的处分。”在这一点上,博古也有其苦衷,那就是自己不懂军事。李德对于博古的放纵自然心领神会,而且认为博古这样做是“有意识的”,因而越起权来便不免心安理得。
既然旁观者和当事人都这么说,那李德成为红都“太上皇”的原因似乎就太简单了。不过,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委员们也该挨板子了。当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会议,并不是“一言堂”;中央和军委的工作程序,也不是博古或李德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的。这样看来,就可以推断出李德成为红都“太上皇”的原因,其实并不那么简单。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当然是主要原因)外,至少还有这么一些因素。
其一,博古、李德身后都有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不仅管着他们,也管着整个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七大以前的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他们及整个中共都必须遵从和执行。套用“文革”时期的一句流行语,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在这一点上,博古和李德都是教条主义者(李还是经验主义者,迷信自己的作战经验),盲目服从和推行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策略)”,致使对红军军事战略战术作出错误的决策指挥。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绝对权威,在造成李德话语强势地位的同时,也使李德承担了本不是由他作出并负责的某些错误决策的责任,如针对十九路军的军事行动等。
其二,当时军事工作的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先送李德住处,查明电报上的地点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制成简图交李德批阅。李德提出处理意见后,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根据来电内容,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由此可见,其时决定重大军事问题,须经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讨论,而不是由李德一人拍板。如此程序原本无可厚非,因为李德是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问题是,既定程序容易养成习惯、形成思维定势,正如李德所说的:“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久而久之,便在红都上下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李德“具有极大全权”。且不论李德所言有否夸大,博古、周恩来会前与李德交流对某些军事问题的看法,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在中共中央分别主管政治、军事,都是中央四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另两人为朱德、项英)。
其三,李德自命不凡,瞧不起“土包子”,听不进不同意见;作风粗暴,动辄训人;生活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这些不良的个人因素,也对他被戴上红都“太上皇”“桂冠”,起了作用。
共产国际的背景,军事顾问的头衔,街垒战专家的声望,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才生的牌子,以及成长经历、实战经验、军事理论修养,甚至种族、肤色,一起极其充分地造就了李德的优越感和骄傲的资本。他瞧不起非科班出身或虽科班出身却一度混迹于草莽、旧军队的中国红军将领。他曾不顾军情,随意责令罗荣桓带兵埋地雷、复又起地雷;也曾呵斥刘伯承不如一个称职的参谋人员。遇到战事不利,就拿别人问罪,要撤这个的职,关那个的禁闭,也不细察因由。弄得一般的人忍气吞声,刚烈的人奋起抗争,彭德怀和他大吵后甚至准备坐牢、被杀头。
李德在瑞金住的是专门为他修建的独立房子,吃的是鸡鸭鱼肉、面条面饼,喝的是奶粉、炼乳,抽的是听装卷烟。当时,这些生活物资当地大都没有,主要靠前线缴获、白区购入,再就是特意生产,如专为他养鸭群。这种优待之举,即使出自李德个人愿望,原本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其生活习惯应尽可能予以照顾。问题在于当时红军和苏区老表的物质生活太贫乏了,吃不饱饭是常事。两相对比,不啻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假如李德吃了用了这些稀罕东西,能为中国革命多做些好事,多善待别人,倒也罢了。偏偏他的所言所行走到另一头去了,那就怨不得人家怪他、骂他。
总而言之,李德成了红都“太上皇”,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与共产国际派他来的初衷大相径庭,既是中国革命的不幸,也是李德本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