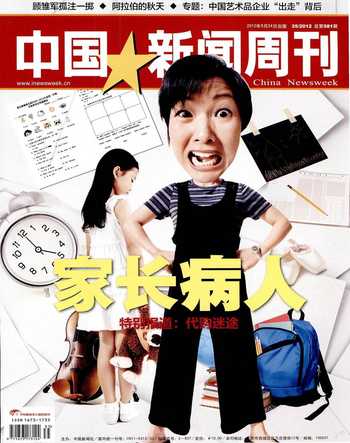美国不曾真正了解的世界
2012-06-12徐方清
徐方清
“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去整整11年了,但美国人的心灵创伤并未愈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的遇袭身亡,是往伤口上新洒的一把盐。
袭击就发生在“9·11”11周年的纪念日。这是自1979年美国驻阿富汗特使阿道夫-杜布斯在遭绑架后不幸身亡以来,美国驻外大使首次死于暴力袭击。
就在两个月前,刚担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不久的史蒂文斯向他的亲朋好友们发了一封邮件,称“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对我们笑脸相迎,他们对外国人越来越开放,尤其是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受到了非比寻常的招待”。
仅仅两个月后,乐观的史蒂文斯最终等来的,却是呼啸而来的炮弹。和他一起在炮火中倒下的,还有他的3名美国下属。
悲剧发生次日,奥巴马誓言将与利比亚政府一起追查凶手。但让他感到不解的是:“史蒂文斯死在了班加西,这是一个他曾帮助拯救的城市。”
伸向在战争中亦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交官的恐怖黑手必须斩断,这一点于法于理都毋庸置疑。但要释开心中的难解之惑,奥巴马和希拉里还得正视如今正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浪潮的现实并反省自身,而不只是急于撇清美国与引发反美示威的影片的关系。
利比亚和埃及完全不同
从朋友那儿听说了关于电影《穆斯林的无知》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消息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埃及24岁小伙穆小龙去网上看了电影预告片。
“太让人生气了!片中的全部内容我都无法接受,整个是对穆罕穆德的亵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小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因为属龙,所以来到中国后,他自己就取了个中文名叫“小龙”。而姓“穆”,正是因为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译成中文是“穆罕穆德”。
即便此时身在埃及,穆小龙也说自己不会参加反美游行,虽然他参加过抗议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游行。穆小龙相信,如美国政府所说,这部电影跟美国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多年来一直相互讨厌。在美国的媒体上,似乎每个穆斯林教徒都是恐怖分子,在阿拉伯媒体上,美国则一直都被称作是‘最大的侵略者。而电影的始作俑者正是利用了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彼此讨厌的情绪。”穆小龙说。
自11日开始至今,示威活动逐渐蔓延至全球20多个国家,包括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国。
经历过“阿拉伯之春”洗礼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新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民众有权要求,民意要得到尊重。
对于因为这部电影而走上街头进行反美示威的人们,穆小龙并不反对,“不能指望普通民众都能像政治家一样想。”
“但我反对暴力,因为它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穆小龙又说。
在穆小龙看来,在这场民意的洪流里,利比亚和埃及属于完全不同的例子。
曾在多个美国驻中东国家使馆工作的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米歇尔·邓恩9月15日参加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一档新闻评论节目时说:“利比亚的安全形势一塌糊涂。在有安全保障的国家,不大可能会发生美国大使遇袭身亡的悲剧。”
曾经担任中国驻叙利亚、也门大使的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副会长时延春在多个场合和利比亚新政府的官员进行过接触,他对于利比亚的现状感到担忧。时延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利比亚新政府缺乏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力,民众对新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
跳出剧本的剧情
美国曾为“阿拉伯之春”设定了前景,“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但多次上演的“我们上街,别人上台”的剧情超出了原先的剧本。
卡扎菲、穆巴拉克等政治强人被推下历史舞台后,长期被威权世俗政府作为打压对象的政治伊斯兰思潮和力量,在突然到来的乱局中纷纷登场。
在突尼斯,成立不过半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首次制宪议会自由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在更受西方关注的中东强国埃及,存在近一个世纪的激进宗教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期曾长时间作为“非法势力”存在,智慧地顺势而为,在最后时刻成为埃及革命摘桃子的人。约旦的穆兄会也在国内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发揮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这些伊斯兰教党派的登台上位或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方搅动的“阿拉伯之舂”,但他们并不完全买西方的账,而是各有自己的主张。
在上海一家国际学校担任老师的美国人马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政府应该多花些精力在自己的经济上,而不要在中东投入太多。下一个政府是谁,对美国友好还是不友好,都有太多的变数,并不由着美国来。”
过去4年来,埃及每年从美国获得16亿美元的援助。从2011年推翻卡扎菲的运动刚刚开始到目前利比亚新政府建立,美国拿出了2亿美元。也门在2011年获得了美国1.34亿美元的援助,今年获得的援助金额也已达到6400万美元。
就连靠着西方的武力攻势才将卡扎菲逼向绝路的利比亚新政权也出现了一些西方不愿听到的杂音,称作为伊斯兰国家,利比亚将伊斯兰教法作为主要法源,任何违背伊斯兰教的法律都将无效,并拒绝向海牙国际法庭引渡赛义夫等。
对于这些出乎西方意料的变局,时延舂却并不觉得意外。“伊斯兰教派一直在阿拉伯世界占主导地位。虽然它们在强人政治时期受到约束和压制,但一直秉持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倡社会公平正义,反对腐败,颇得人心。”时延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强人政治不再,伊斯兰教党派掌权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9月14日,埃及总统穆尔西谴责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的美国影片,是伊斯兰世界首个表示谴责的领导人,但他同时呼吁民众保持克制、不要冲击外国使领馆。
时延春和中东的宗教领袖有过很多接触。在交谈中,很多宗教领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非常感兴趣。这些宗教领袖一方面宗教色彩很浓厚,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形势很了解,视野也比较开放。
“这些伊斯兰教政权不大可能走原教旨主义的道路,会保持世俗化的执政路线。他们都明白作为宗教领袖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区别。”时延春说。
两个标准的世界
2009年6月,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奥巴马在访问埃及时发表演讲称,美国与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有一个“新开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并不排斥,不需要相互竞争。
英国牛津大学当代伊斯蘭研究中心的塔瑞克·拉马丹教授和米歇尔·邓恩一同参加了半岛电视台的评论,他表示,在奥巴马时代,美国的无人轰炸机较之前总统小布什时更多地出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造成的平民伤亡并不比小布什时候少,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
时延春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策略并未得到改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未见进展,“在奥巴马时期,巴以矛盾反倒是加剧了”,这是阿拉伯民众的心头之痛。
对于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政策,塔瑞克·拉马丹教授认为,美国推行民主不应盯着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而应更多地解决阿拉伯人民面临的问题。
“在谴责反美示威中的暴力行径的同时,美国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批判性思考:你在中东推广的民主是否考虑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是否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塔瑞克·拉马丹说。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埃及人不喜欢美国,只有19%的人对美国还有好感。美国在中东地区几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率都比2008年更低。
参加过抗议穆巴拉克游行的穆小龙代表着一部分中东地区年轻人的看法:“我愿意参加抗议穆巴拉克的游行,因为我内心想看到埃及发生改变。但埃及的内部事务不需要外国人来参与。”
“美国政府要是只管自己的事情,这个世界马上和平了。”穆小龙说。不会去参加街头反美抗议的穆小龙,却无法阻止内心对美国的排斥和抗拒。
即便能撇开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因素,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明间也存在不能轻易逾越的巨大鸿沟。
“未来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中最有力量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堪称上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观点。
他还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无可避免地也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世界:人们用一种标准对待他们的同类国家,用另一种标准对待别国。”
出钱又出力的美国,却让中东民众的心中积郁了一触即燃的怒火,“祸根”正是因为美国的双重标准。因为文明的相近,美国不可能改变其偏袒中东盟友以色列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伊斯兰文明的偏见和蔑视已渗进了一些美国人的骨子里。这样的情绪一旦姿态傲慢并且毫无遮掩地表露在宗教情感强烈的阿拉伯民众面前,冲突乃至暴力往往不可避免。
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强烈的文明冲突背后,是伊斯兰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的矛盾。2006年2月,因为丹麦一家报纸刊发了嘲讽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也曾爆发了一次全球范围的穆斯林国家的“反欧风潮”,丹麦、挪威驻叙利亚大使馆遭到焚毁。这次因电影而起的反美运动中,欧洲国家也未能幸免,英国、丹麦等西方国家的驻外使馆也受牵连,遭到示威者围攻。
因为坚持言论自由,美欧各国对电影和报纸的内容传播无可奈何。但在曾于德国担任伊玛目(阿拉伯语中的“领袖”)的宗教学者伊斯梅尔·穆罕默德看来,对宗教先知的描述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它侵犯了教民的权利,西方必须了解伊斯兰世界民众的意识形态。
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侮辱宗教是犯罪行为。
一些美国媒体更快地适应了从“阿拉伯之春”向“阿拉伯之秋”的过渡。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做了一档关于中东世界反美浪潮的专题节目。该节目的评论员说:“这种局面是早就注定的,因为对那里的人们,我们从来就不曾真正了解过。”
(实习生李熠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