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印象
2012-05-30叶开
叶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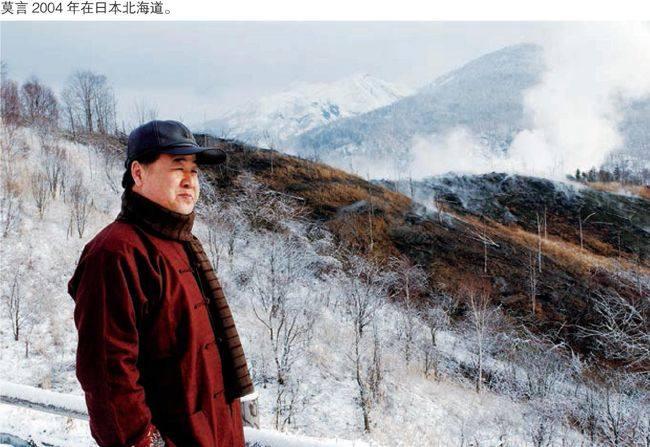

2012年10月11日晚上7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把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并未有效地终结争论,却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式诺贝尔奖焦虑症。
莫言的创作,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他以自己丰富的作品、杰出的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坦然领受诺贝尔文学奖。
我和莫言结识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酒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出版后遭到了中国大陆批评界的冷遇,后来格非从北京带回一本赠书,在上海,我们一起聊天时热烈地讨论这部小说。特别喜欢《酒国》的还有曹元勇,我和曹元勇当时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我硕士,他博士,可能是志趣相投,我们都认为这是一部杰作。1996年春天,我们去上师大,和张闳一起正儿八经做了个《酒国》三人谈,发给了莫言。那时张闳先认识莫言,后来曹元勇去北京时拜访了莫言,我最后认识莫言。但因为共同语言比较多,我们认识之后,交往就频繁起来了。
莫言来上海,一般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或发条短消息。有空我们就一起聚会聊天,没空只是说一声来上海了。那时候的聊天也只是家常,或者相互推荐一些好作品。
2007年8月的某个傍晚,我和曹元勇兄陪莫言在上海瑞金宾馆前的草坪上聊天。我记得,那天,日光已经散尽,四周繁茂梧桐枝叶丁当作响,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那时候我花了近一年半刚完成《莫言评传》初稿,正打算征询莫言的意见。
2006年谢有顺兄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邀我撰写《莫言评传》。为打动我这颗不坚硬的心,他还以稻草成金的娓娓动听话语说:“莫言将来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就成了首席研究专家,谁也绕不开你了。”
我还在犹豫,有顺兄继续吹风:“你博士论文也是写莫言的,顺便写评传,不是轻车熟路嘛。”
我就这样被说动了。
那天傍晚在草坪上,似乎有凉风从脚底升起。他们一人喝茶另一人咖啡,我赶时髦喝依云矿泉水。谈到我写的评传,莫言似乎略有些紧张。我记得我当时还开玩笑吓唬他说:“莫言老师,您看我掌握了您的生杀予夺大权,您得对我友好点。”
莫言说:“你一定是写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家伙。”
我说:“确实,我虚构了一个莫言……”
莫言如释重负。我也如释重负。
莫言说:“这句话就放在扉页里吧。”
遗憾的是,这句话后来没有放在扉页上。这本书的责编杨莉前天跟我解释说,因为是评传作品,她担心扉页上写这句话,可能会让读者产生误解。我和莫言本来就是带着戏谑、开玩笑心态,如果登了这样一句话,那多有意思啊。而且这也是对那种“全知全能”写作的一种批评。我对那种貌似权威的“客观化”叙事一直很警惕,写作体现的是作家本人的独特角度,但在“客观化”叙事中,人们总是伪装成全知全能,而企图灌输读者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我的理解则很个人化,在评传里,作家不过是一个描述对象。我看到的莫言,跟其他人看到的莫言,不会是完全同一个“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莫言形象。“虚构莫言”的意思即如此。我理解杨莉的担心。我们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紧张,想象力和幽默缺乏足够空间,开玩笑是要谨慎的。一个简单玩笑可能会让人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米兰·昆德拉对此深有体会,他写过一部精彩长篇《玩笑》,还在随笔里专门谈到幽默。他引用的那句话,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自以为思想深邃,超越别人而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都应该再读一读这句话。
但是人开玩笑呢?幽默呢?上帝会不会发笑?
莫言是个很警惕的人,他也善于自嘲。一个自嘲的人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莫言对自己的作品很有自信,提起来却总很谦虚。他写完长篇小说《蛙》后发来给我,以续和《收获》的前缘。在他的一再请求下,我提了十一条个人阅读感受,供莫言参考。收到信后,莫言觉得有道理的地方,都逐一作出修改。他改完稿子后发给我,发信时间竟然是凌晨五点半。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在创作上追求完美的精神,并且写作上很有激情。一般作家说“多提宝贵意见”都是假客套,不能当真的,当真你就落入陷阱了。但莫言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话可以当真。在很多文章里,莫言都提到编辑朋友的意见。在“收获精品系列丛书”《司令的女人》自序里,莫言就写道:“1986年冬天,我写完《红蝗》,再次寄给《收获》。李小林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她抄了一段话给我,大意是说,一个人只有在冷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莫言对写作有很高的自我要求,每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结构都绝不重复,都有新发现。在中国作家中,近三十年来莫言是最具有文体意识、对小说结构最有追求的作家,不是之一。
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故事背景,是山东苍山县农民因干部工作不力而导致丰收的蒜薹大量腐烂在地里而引发抗议和暴乱。这部小说在莫言的创作系列中属于“残酷现实”部分,直面了当时的具体现实,用直接、锋利的语言直接切入土地的心脏,而因为这种切入实在太沉重、太暴力,莫言又通过一个卖唱的瞎子张扣在每一章的开头的唱词,来减缓这种语言的暴力。接着莫言创作了那部极其怪异的长篇小说《十三步》。莫言自己在回顾时说:“直到现在《十三步》也是我的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别的作家写得比《十三步》更复杂,我把汉语里面能够使用的人称或者视角都试验了一遍。”
但在当时,这两部长篇因其复杂性、探索性和超前性,出版后没有什么反响,反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莫言作品的英语翻译者葛浩文教授一眼就看中了《天堂蒜薹之歌》,与《红高粱》一起,在1988年就翻译介绍到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世界。
在我看来,莫言的小说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阶段是1986年开始发表的《红高粱》系列,以此为核心,他写了《食草家族》等一大批小说,创造了一个慷慨激昂、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高密东北乡文学共和国。1995年出版的《丰乳肥臀》是莫言的第二个高峰,他自己认为是他所有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他全部作品的基石。此前于1992年出版的《酒国》是一部令人难忘的、技艺高超的杰作,但长期遭到忽略。第三个高峰是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此前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都令人印象深刻,但《生死疲劳》是真正的杰作。这部小说通过一个自由自在的“轮回”结构和狂放中收发自如的语言,描写了土改、“文革”及其之后的一个令人眩晕的恶意乡土,并在小说的推进中,以中国小说中缺乏的、也是最难得的“宽容”精神加以和解,从而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情怀。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对过分惨烈的残酷叙事作品《檀香刑》作的修正。200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蛙》,则延续了《生死疲劳》的思考,通过“姑姑”这个现实中有原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相关政策在乡村中造成的各种惨烈危害,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控诉:“姑姑”退休后,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忏悔。她与做泥人的丈夫一起为自己亲手“杀死”的2800个孩子做了塑像,供奉在三面墙的壁龛上,每天燃香诵经,为自己赎罪。这种“赎罪”行为,是莫言自我救赎的心迹体现,莫言自己在年轻时期,就曾因为计划生育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忍痛带着怀孕的妻子去做人流,这件事情,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让他一直深深自责。他在长期内心焦虑中,通过创作进行自我救赎。
《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创作业绩,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作者系《收获》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莫言评传》作者、莫言多部重要作品首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