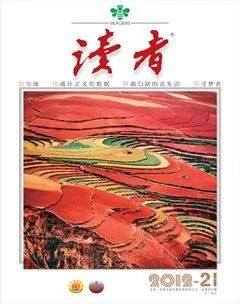寻梦者
2012-05-30郑玲
郑玲
回忆总是具有谜一般的荒凉魅力,既美丽又令人生畏,我多半只是站在回忆的门口徘徊一下,不敢真正走进去。但是,几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不过,早以为与他幽明永隔了,而他,突然来了,像陷落的庞贝古城的一尊雕塑复活了。
不知他怎样终于找到我的工作地点,反正他们通知我,有个风尘仆仆的四川老乡要我接电话。一听到他自报姓名,我手里的话筒差点儿落在地上,我急忙一边叫人去接他,一边旋风般的走向梳妆台。想起当年他那雪莱般的容颜和风采,我怎能黯淡无光地迎接重逢?
我穿戴好了,照了几回镜子,努力镇定自己。
奇妙的少年时代有过许多悲欢,多是一阵轻风、一首短歌,说忘就忘。但有一种悲欢却是一片新绿的幼林,它会在你的记忆中长大、茂盛、横逸斜出,与你的一生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
他不是我的同学,那时,我们是男女分校的,但我与诗的因缘际会却是从他开始。到过抗战大后方的同时代人也许知道,长江上游的一个绿色小城里,一群诗的圣徒集结在抗日风云之下,他们之间无论相识与否,都相互交换诗人们的诗集或自己的习作,我这个从来没有写过诗的中学生,也连续收到《黎明的林子》。给我寄这本刊物的,是一个陌生的名叫史之曦的男生。他在信中说知道我体育不及格,作文却很有诗意。起先,我不敢回他的信,只把那诗刊藏在课桌里读,放在枕头边读。但有一天,我感到有一种东西在心里萌动,便鬼使神差地写起诗来。这是我和诗神最初的邂逅,悄悄地渴望有人分享我的甜蜜,便把那些习作寄给史之曦。从此,我们的友谊在《黎明的林子》里无声无息地开花,终于从书信往来中跳出了一个约会。
那是在秋天,明沙净水,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站在一块伸出水面的岩石上。我一看,就知道是他,因为那异常优美的风姿,正是我从他的诗里感觉到的。但我不敢先打招呼,带着稚气的羞涩躲在岩石后面。不知怎么他也感觉到了我,惊喜地唤着我的名字,从岩石的另一面向我跑来。他那双湖水般的眼睛有些含愁,仿佛注视过摇篮里的我,亲切极了,一下子就赢得了我的信赖。而他故做成人的严肃,问我的理想和对社会的认识,我不好意思背出作文上的句子,红着脸,只回答“是”或“不”。不知是恼怒还是失望,他顺手捡起一块薄薄的鹅卵石往江面一丢,一圈圈涟漪连环似的出现在水面,很长很长,好看极了,我不禁欢快地惊呼起来。他连忙拾一块塞在我手里,教我扔了几十次。最初相约的黄昏,便在“打水漂”中度过了。
那时,来四川的流亡学生很多,他们比较开放,但本地人最怕子女自由恋爱,管得很严。但之曦也是本地人,他那洒脱而高贵的风度又招我家人的喜欢,都觉得他的心灵如明净的溪流,是有岸的,很安全,便让我跟着他去参加学生们的各种集会。对我最有影响的是“诗的会”,参加者都是些追求自由民主的、怀着山河之痛的青年。我那时当然不能完全理解其进步意义,只是因为父亲的一处产业被强权霸占以致家道衰落,朦胧地感到一种痛苦。但我不懂得之曦为什么不满当时的现状,他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子,集千般恩宠于一身。有一次,我想问他,有个女同学暗中扯了一下我的衣角,我便噤了声。后来才知道,之曦是姨太太的儿子,刚发出第一声啼哭便被大娘夺去,伪称是自己所生。他的亲娘则被远逐,在备受虐待中死去。他在大娘的监护下宁静地长大,谁知宁静也有缝隙,秘密终于泄露出来,他不敢诘问,一种咬啮神经的怅惘就这样永远地在他眼波中荡漾了。
之曦的外表优雅而文弱,相处久了,就会知道他有一种禀性上的狂热,常在校刊上发表一些热血文字。他之所以幸免于被开除,除了校长畏惧他家庭的势力,还有赖于进步老师的庇护,说“他的才华比门第更高贵,有成大器以光耀母校的趋势”。那时,他算得上是小城里少年们心中的英雄,许多女生都希望得到他的青睐。他对我的专注很快就传开了,有调侃的,有攻击的,尤其可怕的是他的表妹,她与我同班,总是黑影似的盯着我,她那小女巫般的眼神和气息令我坐立不安。
当时,我还是个短发覆额的小女孩,爱情尚未在我身体内觉醒,根本不懂得它的神圣伟大可以直面刀山火海,只感到受了诬蔑,觉得非常羞耻,白天罪人般地走进学校,夜里在噩梦中惊叫,最后大病一场,耽误了功课。我不愿留级,就跳级考到远离小城的另一所高中。
离开小城的前两天,我写信约他到公园里告别,因为我们曾在凉亭里共读过诗章。那天一到凉亭,我便看见一位华贵的夫人正在凭栏打量我,瓷一样的目光,很冷。她慢悠悠地自言自语:“史之曦明天订婚,今天同他的未婚妻选戒指去了,不会来了!”
一见她身后那个女巫般的女孩,我立刻明白这夫人是谁了。像一头幼鹿逃避眈眈的虎视,我掉头便跑。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之曦。高中毕业后,我离家出走,参加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我全力奔赴新生活,日夜处于鏖战般的兴奋状态,顾不上和人通信,再说之曦属于应该被打倒的阶级,也不便通信。总之,往事在我心中沉寂了,犹如前生的经历,朦胧而遥远。
然而,他却来了,在我一心要“忘却”的时候,他却千里迢迢地来了。
他来做什么?是为大半生的思念寻找归宿吗?但少年时代的情谊如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光芒,若真若幻,怎值得思念大半生!他来做什么?是以诗会友吗?似乎不像,如果为了诗,他早该写信来了。他来做什么?是不是路过此地遭遇不测,偶然知道我的地址而来寻求帮助呢?但是,我等待着,以少年时代的全部激情等待着,回忆如丽日中天,脑海里尽是他当年的形象,英华独秀,玉树临风,天生的优雅中有一种我害怕触动的纤弱。
终于,他出现了!
他是谁?她是谁?我们各自心惊,都不敢相认。沉默!沉默如雷!
他就那样拘谨地站在门边,一动也不动,一套簇新的、款式很旧的中山装,一双完全不相配的镶花破皮鞋,满脸沧桑,原来那湖水似的含愁的眼睛,露出一脉干涸的凄凉。我第一次感到时光是一个残酷的行刑者,竟可以把人天生的优美剥蚀得荡然无存。而他,也在惊诧地打量着我和我家的摆设,那种不相信的表情有如走错了门。久久,我才叫了他的名字,他才说:“我以为你已经是明日黄花,竟没有想到你如暮云春树!”
啊,这正是之曦的语言,我欢乐地伸出手去,不管他的变化多么出人意料,重逢的喜悦依然压倒一切。他尴尬极了,近乎自语地说,传错了,传错了,完全不是那样的。我问传错了什么?他一副失落的样子,茫然不答,只说他如何在火车上睡觉时被一个年轻人偷换了黑色的新皮鞋。
晚餐时,丈夫回来了,他是个极喜欢朋友的人,他向之曦敬酒,找他说话。但丈夫也和我一样有些纳闷,之曦为什么远道来访友,却极少言语,心事重重的。他嘱我明天陪之曦到公园里走走,问问他需要什么帮助。
我和之曦在公园信步,走到一座凉亭,垂柳如烟,湖水荡漾着迷濛的奇丽,清风唤醒了种种异香又加以散播,恍若几十年前的情景。我说:“还记得吗?这里多像我们曾经读诗的地方。”“正因为记得,我才来弥补!”
淡淡一语,波澜不惊,却使我震动了!
啊,原来是为“弥补”而来,可“弥补”是什么意思呢?他并没有对我做错什么。我们又沉默了,像国画上的留白,看起来像空,实际充满了期待,我期待他说出缘由,他期待自己有勇气说出。霍然,他黯淡的目光一闪,眼睛中有冰与火在跳动,再明白不过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寻梦来了,当然不是来寻那个声如流泉的如诗如梦的少女,而是来寻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太婆。当年,因为我的罪过,你从我面前消失了,我的三魂七魄分开去找你,天上人间都没有你的消息。过去,死在我心里了。
今年春节,我进城去买教科书,偶然碰到陈碧佳,她说杨凤从外地返乡过年,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说你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文革”中又被流放边陲,回城后做临时工,四处漂泊,“改正”后虽然被安排在文联工作,但是举目无亲,愁病相煎,憔悴得像枝枯竹。她说你什么都不愿提及,只顾打听我的消息,还说你想回乡安度晚年,只是已经没有亲人和房子了。这些话有如你的呼唤,回忆像远方山谷里的钟声,从青春岁月里向我传来。我立刻要了你的地址,和老伴商量了半夜,特地来接你回乡!你看,回程票都买好了。
我既感动又惊骇,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火车票,我对杨凤的恶作剧简直气极了,是想助谈兴而编造传奇,还是一种天真而愚蠢的同情?在学校时,她是篮球队的中锋,我自幼柔弱,她以保护者自居,我们便成了最亲密的朋友。重逢后我自然会对她讲述自己过去的苦难,但她也目睹了我如今的生活,非常羡慕我的家庭,怎么会把我描绘得像长满野草的禅房、玫瑰已谢的旧客厅、一幅孤星血泪图?而之曦,居然把这些不合逻辑的谎言信以为真,简直像个世外之人。我不禁问道:“这些年你都在哪里?”
“可以说是在世界边缘。你离家出走后,我上了大学,参加了‘迎解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的一个文化部门工作,那时的前途可谓红日高照。后来,因为出身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到林区监督劳动,‘改正后再也不想出山了,就留在林区的子弟学校教书。入山既久,便成了山囚,然而这种囚徒有一种城市里得不到的自由和岑寂,正好安放我的灵魂。当年所向往的英雄的叱咤、成功的殊荣,早已摇落在子夜的西风中了。我终于明白,权力是可耻而危机四伏的,财富是沉重而愚昧的,荣誉更只是一种偏见。我已经学会知足,不愁最低的物质生活就行了。我和老伴虽是听严母之命而结合的,倒也相处得融洽,她始终和我共度忧患。她自然知道我们小时候的情谊,完全同意接你去住。我就这样寻梦来了。早晓得你的处境如此之好,原是不该来的。我为什么不先写封信了解一下,只凭感情的驱使呢?唉,感情有理智根本不能了解的理由!”
静静地听完这一席话,我的心在胸中融化了,急切地要从眼眶里涌出来,我怎能将他高贵的同情视为梦游者的呓语?能拥有如此念旧的朋友,真是人生大幸。但是,我怎么酬答他呢?他的梦幻一开始就具有悲剧的冲突,他从遥远的彼岸走近我,却永远抵达不了我的此岸。
我不忍对他说:我早已向少年时代告别,女人无故乡,哪里有我的事业和朋友、有我的诗巢和爱巢,哪里便是我的故乡!
我不忍对他说:我跟时代一起痛苦过,却也在跟时代一起进步,我曾被狂风恶浪冲到边缘,现在正奋力回到激流的中心。
我更不忍对他说:你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英雄业绩,但你是个因心灵而伟大的英雄。如果我以这句话去感谢他拯救性的真诚和慷慨,他定会以为是一种讽刺。
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是对梦的追逐将他从巴山夜雨中带到了洞庭之滨,他的梦却如落叶,一片接一片地脱离了梦之树。我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的无能为力,只好陪着他绕着湖慢慢地走。但是,总得回答啊。于是,我说话了:“我怎么可能对杨凤说要回故乡度晚年?我尚未产生‘夕阳情绪,觉得一切犹未为晚。而且我早有个家,即使在流放时期,我也不是孤苦伶仃的。我和丈夫结识于穷途末路,我们的结合是命运之结所系。我们穷愁而不潦倒,虽然在肉体上受尽种种折磨,精神的圣殿却从未坍塌。他是个以奋斗自娱的人,可以在荆棘丛中打滚,在苦难中奇异地充满生气。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才熬过了那些难熬的岁月。”之曦微微颔首说:“昨天,我一见到他,就明白你是幸福的,就感到我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第二天黄昏,他即起程,任我如何挽留,也执意要走。我请求他留下通信处,他没有,只说,把人团结在一起的是精神而不是文字。
站在月台上,我无限困惑,本来应该去紧握此生再难相见的故人的手,却只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
月余后,杨凤来看我,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备。她喊道:“我恶作剧什么呀?只不过是打抱不平,想刺激一下他的良心罢了。当年,你不是为他受够了气吗?他害了你,自己倒好,十六岁就和人家结婚了。再说,我也想不到如今还有这样认真的人,认真早已被大家看成致命伤了,谁知他会傻里傻气地跑几千里来寻梦……”
我只好央求她再管一次闲事,去打听之曦的通信处。
我给之曦写了好几封信,希望他记起自己笔挟风雷的时代,不要辜负上天赋予的才华,改变他目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并请他出山当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可每封信都在长风中杳失了,几年没有回音。我也沉默了,我想他已经是一个孤僻得或者超脱得极其彻底的人,为什么要改变他?据说孤独是禅的最高境界,我记起《世说新语》里的那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