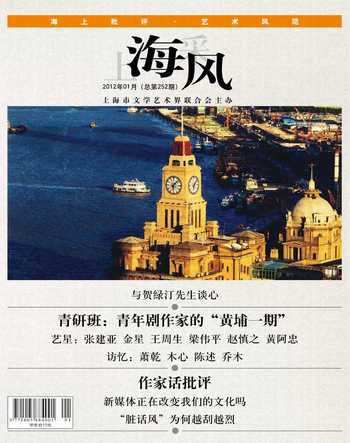黄贻钧:打造乐坛奇迹的“神手”
2012-04-29董存明
董存明



不凡之人有一种无形的感召力,并不依附于权势名位,纯粹凭其超常术业之功和人格魅力,赢得人们心口信服。德艺双馨的黄贻钧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用平实无华笔触工工整整大写的人。
黄老的音乐人生与中国交响乐事业自肇始之初的发展史迹相交集。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但一手引领中国资历最为悠长的上海交响乐团以全华人阵容声名远播,还一手培育了从零点起步的中国最为年青的管弦乐队,创造了乐坛奇迹。一老一新,母子双塔,耸立于一代宗师黄公丰碑前,令后辈音乐人高山仰止。
总理动议 应运而生
那是半个世纪之前火热又奇异的特殊年代。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在沪观看民族舞剧《小刀会》后,欣然提出动议:“上海也应有芭蕾舞,可以开办舞蹈学校,如果需要老师,我可以帮你们从北京请。”时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市文化局领导徐平羽和钟望阳(后调任上音党委书记),迅即落实总理指示,为了日后组建上海芭蕾舞团,决定同步培养音乐与舞蹈人才,筹建舞校的同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管弦班。其时,正值“三年大饥荒”,六亿人民食不果腹的当口,已在谋划明天的精神食粮,并从捉襟见肘的国库里拨款在上音新建一幢教学楼(北大楼),更何况决策引进的是舶来品芭蕾艺术,不由为总理的远见卓识和过人胆魄所折服。
1960年秋,上音管弦班开学。舒群同志受命担任管弦班负责人。她早年就参加革命,公心为上富有责任感,并于1945年进入上海音专,曾在中央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学馆工作。懂行的她深感这副担子之重。按通常的音乐院校阶梯式培养模式,怎么也得十来年,而现在仅限于三分之一的时间,要“一整锅”地从无到有端出个大乐队来谈何容易?其难度系数之大,更在于从普通中学招收进来的学生只懂简谱,专业基础绝大部分可称之为“白丁”。当时社会上会玩弄稀罕洋乐器的人凤毛麟角,远没有当下年年有数万名学童参加各类乐器考级这么普及。虽则在招生重重考核中有不少人显露出了良好的音乐潜质,属于可造之材,但能否如愿变数很大,这是无可改变的严峻现状。其时的社会背景正盛行“大跃进”思维,大干快上“放卫星”、创奇迹,可终究不能违反艺术教育客观规律。只能充分利用上海作为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发祥地的丰富音乐资源,去强化艺术教育,才有完成艰巨使命的希望。
令旗挥舞 频伸援手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师资如沃土。上音院部党政领导贺绿汀、钟望阳十分关注呵护新开辟的“实验田”,倾力扶持。谭抒真副院长和管弦系系主任陈友新及窦立勋、赵志华、朱起东、韩铣光等诸位教授都亲自出马,常态化地给予指导、点评、会诊、考核。木管声部和竖琴均由系里一批中坚骨干教师包揽主科教学。其他各系也都指派了谭冰若、程卓如(上音附中校长)、连波等专家,担当起《西洋音乐史》《基本乐理》《戏曲与民歌》等十余门共同课讲授之职。在众多声名赫赫的名师哺育下,全面摄入艺术文化素养的养料,幼苗窜枝拔节茁壮成长。
黄贻钧先生自从获悉上海将诞生一支全新乐队的讯息后,屡屡给舒群提供专家建议大力辅佐。他明确主张管弦班应设在音乐院,统一住校的方式能增加练琴时间又便于严格管理,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专心致志于学习。而时行的兴办学馆方式,相对条件没这等全面,他尤为担心年轻人免疫力差,会沾染上某些旧社会遗留下的不良习气。后来,他主动把学馆里几名学员都并入了管弦班。此举正说明他并不把学馆视作乐团私产,全然是为学员成长环境前程着想,也是用行动来支持这一新生事物。
起初招收的学生有120余人之多,因为另外还要承担为上海各乐团补充新人,一对一的主科教学使师资匮乏成为燃眉之急。他身为乐团团长,不仅没有借口“不属于本职范围”推诿了事,在开班之前就慷慨无私地输送了司徒海城、王文山等元老精英和十余位资深演奏家组成了老师班底,挑起大梁。相继又调来“老法师”郑金銮(小提琴名家郑石生之叔)、王人艺(聂耳的老师)再予充实。为确保团里演出质量不致下滑,他在人力资源上合理调度,让好多声部首席和艺术骨干担任主科兼职,达到两全其美。又特意把团内著名学者杨民望先生(丰子恺女婿)调往主讲《音乐鉴赏》课,使学生从理性视角阐释音乐内涵,大大提升了艺术品位。
我们曾见过社会上某些地盘上的一方诸侯,紧紧看护自家领地,唯小团体利益至上。这正反衬出黄老站在国家音乐事业发展的制高点上以大局为重,体现出无私无欲,无欲则刚的博大胸襟。他从不口吐莲花把漂亮大话挂在嘴边,但从其一系列行为中能触摸到一颗滚烫的心和水晶般的品格。
名帅亲征 两大创举
黄老是中国交响乐指挥界之翘楚,孚享盛名。难以让人置信的是,他竟不顾身价毅然去调教一批娃娃兵,这无异于国学大师去教童蒙“三字经”。
短短两年主科学习中,一面孜孜于教一面孜孜于学,“勤为径”已蔚然成风,“偷”电灯泡、抢琴房,天天从清早练到熄灯铃响,连寒暑假也主动留在学校苦练。好些天赋禀异的冒尖学生进步神速,考核时管弦系教授们顿觉眼前一亮,惊喜不已。同时,因艺术教育高淘汰率的筛选和国家财政拮据诸因素,已送走约三分之二的学生,余下正可以组成一支乐队。客观地说,那时无论专业技巧掌握程度和控制能力都尚显稚嫩,整体水准还欠火候,黄老自当十分清楚。然而,他与舒群合议后,决定立马推出新增加一门“乐队课”。一来管弦班培养目标不是独奏家,而是称职合格的乐队演奏员人才;二来也许与黄贻钧的自身经历有关,对“实践出真知”深信不疑,提前训练乐队合作技能有益无害。开设“乐队课”无疑是一个大胆之举、创新之举、在全国音乐院校中首开先河之举,今日回过头来看也是明智之举。
“乐队课”首排曲目是德国作曲家韦柏的绝作《奥伯龙序曲》。第一次合排好不兴奋,可是其中小提琴有一长段Allegro连续十六分音符快板,说实在话能独自顺顺当当拉下来已属不易,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难免顾此失彼。但车到山前必有路,黄老不是等闲之辈,为此他采用了“母鸡带小鸡”的对策妙招——由“老司徒”等五位原乐团弦乐老师分别担任声部首席,再安排他们负责指导分部练习,传授长年积累的乐队实践经验,正发挥了班上师资的优长。这一招用了一年后,他又让学生顶上首席位置,但分部排练仍由老师指导,“扶上马,送一程”。
开设“乐队课”和“母鸡带小鸡”,黄老都是顺势而为,取得了明显实效。两大创意,“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关键性难题。
妙招迭出 点石成金
虽然黄老已谢世多年,但他排练中的场景会时常在我脑海中“回放”。
气场驾驭一切——正当盛年的黄贻钧常穿一身卡其布中山装很为朴素,但眉宇间神采飞扬,谈吐温和举止沉稳是位谦谦君子。那一口带有苏州吴侬软语口音的普通话,很有亲和力。时而在眼镜架上方瞟你一眼,暗示你即将进入,或则微微点头以示赞许,环顾的眼神不容任何角落有丝毫懈怠,他的“气场”驾驭一切。黄贻钧的指挥手势会说姿态优雅的“哑语”,柔臂在空中舞划即兴挥洒“音画”。
在排贺渌汀《晚会》时,曾出现过有趣一幕。乐曲中小反复变换大反复,反来复去,稍一不留神就“炮声”连连。因为后半拍起音的旋律,一旦忘了反复,正拍休止处突然冒出一个音来“放炮”,十分明显,又好气又好笑。而此时黄老不愠不怒,从来没见他大声呵斥过,仅是含笑看你一眼,这一眼就尽在不言中了。一则是他富有涵养的个性使然,二则“放炮”不是技术性原因,倘一指责就会愈加紧张,更易出错。他要让入门不久的学生,在松弛又神情集中、适度紧张的演奏状态中释放潜能。看来能读懂演奏员心态的指挥方能称得上好指挥。
讲解音乐内涵——初次进入音乐殿堂,对于音乐的理解力有限。黄贻钧有时会显得不满地说:“你们拉的是音符,不是音乐!”那时的确难以区分这两者到底有多大区别。音乐与诗歌、散文一样,都讲究“贵在意境”、“形散而神不散”和真情实感的融入,没有此“乐之魂”,就如同行尸走肉了。难怪他要说“你首先得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听众”。
在排练蒙族风味的《森吉德玛》时,让你想象一马平川的草原旷野之美景;演奏《瑶族舞曲》时,我们则都成了盛情主人的宾客,在民俗节日中欢快地共唱同舞;在排练贝多芬《爱格蒙特序曲》的尾段时,他又根据剧情形象地指出弦乐这句最后两个音必须放开来拉,那是英雄被砍下了头颅,弓子要干脆利落,收音要干净……当然,无标题音乐无法一一明说,也更难于理解和演绎。此后在排《贝五》时就领教了,幸好有前面这些铺垫,使理解能力渐入佳境。
精言回味无穷——大文豪鲁迅曾在“语言有三美”论述中,把“意美以感心”放在第一。黄贻钧有好多精言耐人咀嚼再三,得益匪浅。
“要分清谁是老大、老二、老三”。必须通晓乐理分清主次,地位不得僭越也不必谦让。
又强调“要忠于谱子”,即包括音符和所有音乐术语标示符号,尊重作曲家的创作原意。
他对音质音色要求很高:“响而不炸,轻而不浮”。
“你们得首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听众”。强调审美过程是由演绎者与受众共同完成的。
经常借用古语“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勉励发挥主观能动性,踢开绊脚石。
他尤为强调演奏时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心无旁骛,全身心浸润于乐曲意境情绪中去。
他再三告诫学生“要学做一个聪明人,善于举一反三”。得益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平衡艺术是乐队合作技能的核心,这与《易经》中的阴阳八卦中和之理相通,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揭示表演艺术真谛的话语至今还言犹在耳,使学生如醍醐灌顶,终生受用。
细节决定质量——重视细节,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莫不如此。
黄贻钧在排《贝五》首段时,对节奏扣得很细。起初,后半拍起音的主导动机往往会休止符稍长而后面三个音挤得过紧,他说有些世界名团也会节奏精准度不够,建议用“填充法”——即内心在休止符里补唱一个同音来弥补,立竿见影。
对每一个音他都要求交代清楚,比如弱起节奏起音的旋律,容易含混不清一带而过,应该有意识稍加强调一下拉宽些,使旋律保持完整。
艺术需要适度夸张,对于这个“度”的准确把握并非易事。黄贻钧曾说过 “水平差的乐队响到一个f 、最多ff,轻则又轻不下去,根本听不到fff、ppp。音量幅度一定要对比明显,否则观众感受不到”。对于定音鼓发声比较迟缓的乐器,他又要求敲击动作要稍稍赶前些,因为声音传送到观众席存在时间差,大场子更加明显。这正说明他对这个“度”的理解不止于主观上认定,一切应以审美对象客观感受的音响效果为准绳。立足点上的差异,显见他对“度”的理解层次更高。
黄老在宏观把握好乐曲整体布局外,细节之处也大做文章,体现出了他严谨的艺术态度和一丝不苟的艺术精神。
过河指点门道——一般而言,指挥提出艺术处理要求之后,你能做到就好,一旦总是做不好,就会束手无策。但黄贻钧另有一绝,他会具体指导你采用什么技术途径去达到目的。
比如当他提出在乐句语气上的要求之后,发觉原谱上弓法、指法不尽合理,就会很在行地提出建议怎么去改动,也会很尊重坐在首席位置上的老师一起商讨去体现到位。当弦乐总是该轻轻不下来,他会提醒运弓侧着弓毛,上移靠近指板,说得那么在行在理。遇到管乐吹奏中“音头”太重太硬了些,他也会提醒你该用舌头什么部位,与气息如何配合,简直有点像上主科那样。假如管乐的和声起点参差不齐,他会用反弹拍点预留一个“气口”,使吸气准备即已统一,从指挥手法上解决问题。
正是因为黄贻钧自己会拉提琴,吹奏过圆号、小号,早年在洋人为班底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里工作过,他熟谙乐器性能和演奏技法之故,因而能点中“穴道”。甚至,他还曾让几个吹圆号的学生到乐团来亲自辅导。具有如此能耐的指挥,可谓另有一功。
突破门户之见——“同行相忌”是文艺界的通病,门户之见甚深者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而肚量很大的黄贻钧,为了让学生增长见识接触不同指挥风格,请来了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
杨教授在排练时机智风趣的语言常会博人一粲,上课气氛轻松愉悦。当他指挥老柴的《花之圆舞曲》时,用地道的南京口音说“要像雪花打在玻璃窗上”,顿然引来一阵哄笑,他那句形象化的比喻立即让学生心领神会。没想到这桥段成为乐队“活宝”津津乐道的保留节目,活脱活现“拷贝”了几十年。
我们亦然心知肚明,比喻是为启迪学生,但抽象的音乐语言不可能用具象的文字语言来表达,而要靠“悟性”去体认音乐气质。
走出课堂实习——音乐是时间艺术。正式场合“一次性”演奏演唱,好与坏全是它了。上课排练则不然,重点段落常需要反复精排。舞台演出经验不可能在课堂上获取,有个长期积累过程。
黄贻钧正是考虑到这一层,寻觅合适的机会让学生到蓝天中放飞。于是,他作为一团之长,安排了在“大世界”拼台演出,以老带新。初次上台,直接与听众互动,演奏心理和演奏状态都会发生微妙变化。有的会“人来疯”超常发挥;有的会“上场慌”大为失常。好在“大世界”连续一阶段每天会演上一两场,天天有所进步。
在“大世界”演出都由樊承武老师执棒,节目有歌剧《卡门》序曲和几首气氛炽热的中国乐曲。平时他一直作为黄老的副手参与培训乐队,负责为铜木管、打击乐排大分部。后来到金山县干巷公社下乡劳动锻炼期间,也为农民兄弟演出了好几场。的确,樊老师也为乐队成长奉献了一己之力。
自编排练教材——平地而起的乐队课无先例可循,如何由浅入深有针对性地精选曲目作为教材也是一门学问。我们无从得知黄老殚精竭虑备课过程,考量的出发点和依据是什么,但卓有成效的训练成果已经足证一切。
“乐队课”上了两年半,共排了莫扎特第三十一交响曲、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格鲁克芭蕾组曲和《洪湖赤卫队随想曲》等四十余部中外经典音乐作品,涉及不同曲体曲式、不同流派风格、不同作曲大家、不同合作难度,广长了见识。记得他曾经说及“曲如其人”,要区分作曲家个性各异的性格特质,谱子上同样一个力度记号f,贝多芬的作品要气势豪放些,音头清晰有一种刚性;相对而言莫扎特的典雅曲风,在音量上对比出来即可,不要“凶巴巴”。这让我们联想到原来系统学习《西洋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史》都那么重要。
有几位自己很“要”的同学,每次排练后都认真记录了笔记,倘若整理一下,或许亦可拾遗补阙留下一份音乐史料了。
上述八个侧面,恰如一个八度音阶,谱写了黄老《育苗奏鸣曲》中的一个乐章。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且借用魔术师刘谦正式表演前常说的一句话:“大家注意,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莺声初啼 乘云直上
但凡圈内人都知道,崇尚个性张扬的独奏家未必能组成一流乐团。乐队需要“忘我”精神的“自我”价值体现。多声部的交响谐调,来自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又心灵感应般默契的彼此照应,以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
经过黄贻钧大师悉心调教,点石成金。一堆散沙,砌筑成一座座缪斯艺术女神沙雕。转眼到了1964年冬,“上音”大礼堂内毕业汇报音乐会隆重举行。这是乐队首次集体亮相,全面检阅教学成果。贵宾席上端坐着院内外专家领导,全场挤得满满当当的,连走廊也站满了人。
开场是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留学前苏联时所作的《节日序曲》。号角齐鸣,礼花四溅,这气势恢宏的节庆场面正贴切此时此刻人们的心境。又奏响了《开河序曲》这首原创作品,这是下乡劳动时由于群昌同学根据浦东说书音调改写的主题旋律,经由朱践耳先生加工扩展、编曲配器的自产作品。音调里透出上海郊区田歌劳动号子的泥土味,备受好评。可惜,总谱已不知去向,不曾想首演即成绝响,遗憾之至。
压台重头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内行人尽知这部经典巨作是块试金石,乐曲富含深奥哲理,跌宕起伏幅度大,同时每个声部都有乐段展现功力究竟如何,合作难度也颇大。当黄贻钧凝神将指挥棒一砸下,砰然响起了千钧之力的命运敲门声的主题。骚动的心惊惶悸怖,浸淫脆弱的心灵。随之,呈示部、发展部、再现部逐一层次递进。大师的指挥棒出神入化,剔除了年青乐队的青涩,俨然是支训练有素的乐队。听众沉浸于乐思演化推进,品咂着。末尾,当调性转换,扼住命运喉咙的凯歌声响起,同时宣告一个崭新的、全国最年青的乐队呱呱坠地了,声音洪亮且清脆!
冬日里的黄贻钧一再谢幕后走下台来时满脸汗涔涔,他坦言自己也挺紧张,想来是怕新兵第一次见大场面会失控吧。一画上圆满的句号,这位“教父”对众弟子台上争气的表现深感慰籍,苦心换来了甜心。
1965年初,当我们从音乐院大门走出,按惯例要下乡劳动锻炼半年,谁知才过了约一个月,因要赶排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而急召回上海舞校。三个月后《白》剧在《上海之春》上公演,一切正如当初开班所期许的那样,一支全新的双管编制乐队首次亮相于公众面前,充满了青春活力。
乐池里,谱架灯漏出吝啬的光,如有灵性的指尖叩醒了五线谱上一个个小精灵,千回百转的音浪,荡漾心旌摇曳的律动,裹挟起足尖飞舞……
自此,随同舞剧《白毛女》在“文革”中成为革命样板戏,乘云直上,享誉全国。乐队在补充进首席王希立和十余位新成员后,进一步增强了实力。《白毛女》剧组频频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十大元帅和亚非拉国宾政要招待演出,公演了1600余场次,拍摄了彩色电影在全国放映。相继出访朝鲜、日本、法国、加拿大诸国,特别是1972年,周总理策动“芭蕾外交”打开了中日建交的大门,他对出访成果异常兴奋满意,专电告知上海组织三千人欢迎队伍到虹桥机场接机,这等高规格礼仪迎接国内文艺团体出访归国,从无先例。
1979年上海芭蕾舞团成立后,管弦乐队除了为舞剧《天鹅湖》《葛蓓莉娅》和团里原创新作《雷雨》《苗岭风雷》《阿Q》《魂》《阿里巴巴》伴奏之外,还由指挥家陈燮阳执棒举办了上百场各类音乐会,并曾与法国当红指挥家皮里松合作演出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等等。
罗列这些硕果,无非想表达片片绿叶对根的眷恋。引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论文选》中一句话来说:“一切光辉灿烂的东西总令人想起太阳,而且沾得太阳一部分的美。”我们都沾得了黄贻钧大师的艺术之光和美。
师恩如山 林木护绿
悠悠五十年,棵棵小树苗已长成一片粗壮林木,枝叶翠绿,装点高山。
以管弦班学生为基本阵容的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日臻成熟,在上坡路上不断前行。未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音乐团体进行重组,指挥陈燮阳和首席王希立等十四位成员调至上海交响乐团,在“出国潮”中又有十余名成员分赴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和加拿大、中国香港、美国等一些交响乐团工作,其他成员则调往歌剧院、爱乐、轻音乐团或留在芭蕾舞团、歌舞团,一个好端端的乐队就此解体。这对于管弦班情结很深的师生们来说,不免备感失落和无奈。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音乐人仍然在为音乐文化事业奉献自己的艺术才华,黄老的一番心血并没有白费,因为人才属于国家,音乐没有国界。
2010年深秋时节,原上音管弦班八十余位师生回到母校,为五十周年举行庆生派对。所有健在并在沪的教师都列为嘉宾应邀出席,十余位“海外”学友也专程返沪,济济一堂,热闹非凡。聚会上,召集人缪陆明同学在“祝词”中缅怀先师,提到一长串光辉的名字,立下了头功的黄贻钧先生理当排在首位。喜看今日为数众多者被评为国家一级、二级高级职称,有多人出任声部首席、副首席,成为上海五大乐团骨干力量;也有同学从事社会文化事业,就任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上海音乐厅经理、上海市歌星俱乐部总经理等职务;或在美国成为世界顶级长笛品牌总厂技术总监;下一代中的佼佼者摘得了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成年组金奖,以及在德国、加拿大交响乐团中担任声部首席。大家都把这些业绩视作管弦班的骄傲。满头银发的舒群老师深有感触地给予精辟总结:“反思管弦班之成果,包含了两个基因,是乐团‘实践派与上音‘学院派优化组合、良性互补的结晶。”可谓一语中的。
可敬可亲的黄老与学生不但结下了师生情,还有一份流淌着艺术血脉的亲情。他的精神今日仍在感召我们做好艺术传承,致力于培育新一代音乐人。我们毕业后,他还吭哧吭哧地骑着自行车来到偏僻的西郊,在舞校大院芳草地上与我们共沐春光,一同亲密无间地笑谈。听到了吗?还是那一口苏州口音的普通话,糯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