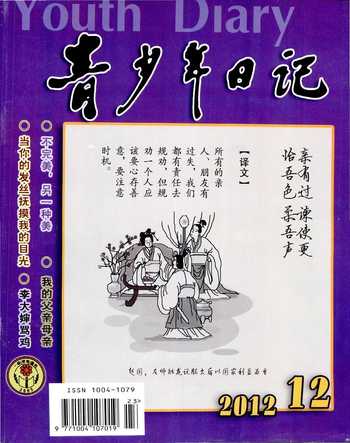从前的夏天
2012-04-29杨蓉
杨蓉
人的童年的种子,会在多年后的桌一天浸润着寂寞的雨水发芽。
想起小时候,一个个稚拙的画面,背后藏着无知无畏的惊险。当时生涩,在回顾时得以融汇贯通。童年清澈的时光之水倒流而来,洗涤着行年的沧桑和疲惫。
——题记
(一)
一道高高的坝埂下,依偎着大大小小的村庄。村落外,田畈迤逦而开。夏日午后,村子里是一片寂静,只有蝉的嘶鸣。我踏过遍地的桑阴,顺着一条小河往前走,日光下的水面泛着亮锃锃的光。再穿过一条条弯曲的田埂,我朝着不远处另一个叫“叶个坝”的村子走去。那住在村头第一家的就是我大姥(父亲的大姐)家。我小时候,在宋村和一班小喽啰玩得没了新意之后,就是喜欢去大姥家玩。
大姥家和我家一样,有姐弟三个。一个表姐和两个表哥、表姐不太带我玩,她离我比较远,像挂在墙上年画里的人。在大人眼中,她是漂亮能干的。我常听到大人们说,青梅真会做事啊,又会烧饭又会洗衣服。她的脸白而嫩,两只眼睛水汪汪的,我望过去,像两只沾着露水的黑葡萄,连她的名字叫起来都那么动听。我常常看到她在房里,对着一面小圆镜子,梳她那又黑又长的头发,有时候还给自己的脖子缠上花花绿绿的围巾。有一次,不知道围巾是怎么绕到脖子上的,越解越乱,她的脸涨的通红还没解开,我担心那围巾会把她的细脖子缠断。后来还是大表哥帮她从后面解开的。
大表哥长的很英俊威武。他不爱读书,经常挨我爸爸的板子。但是我和小表哥都很崇拜他。他喜欢表演节目给我们看。他躺在床上,两只手伸向空中,似乎扯着了一根绳子,一拉一拽,身子竟然就一下一下直起来了。我也模仿他这样扯绳子,身体还没直到一半就摔了下采。小表哥比我大三岁,他也学着样子扯,身体倒是直起来了,却没有大表哥扯的那么有节奏,像机器人一样。我曾经疑心大表哥面前是真的挂着一条绳子,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玩过扯绳子,我们就玩捉迷藏或者打仗。
玩提迷藏我最拿手,当然,他们不知道我从指缝里偷看。床底下,门后面,灶壁间,屋后的稻草堆,一株大栀子花上,是他们经常藏身的地方。只一次,大表哥爬到树上,任我“翻江倒海”,屋里屋外转了好久都没找到,他眼睁睁地看着我转圈圈,最后自己笑得从树上跌下来。
打仗他们会使用自制的武器。他们把破败的伞撕去伞面,只留下伞的骨架,拆开来,用锤子砸扁,一根根放在石头上磨,再剪下一截牙膏头,安装上去。就成了锋利的宝剑。虽然小巧了些,但和电视上的宝剑真是太相似了,且一样具备杀伤力。这件武器要花费不少时间来精心制作,所以最宝贵了。我看了眼馋,但他们一般情况下却不给我玩,说眼睛被剑刺到了会瞎的。
有个午后,不知道是大表姐责骂我们扰了她午睡,还是我们在家玩腻了,我们就一起来到坝埂上。坝埂下一个水电站,有两层小楼房,旁边还有一个水闸。那时候村子里都是草屋或者瓦房,这楼房看上去很气派。我们坐在水闸不远处,看着滔滔的水流进闸口,打几个漩涡就吸进去了,后面的水流又翻滚着灌过来,声音很响亮。大表哥指着那两层楼房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就要住这样的房子。我们都觉得“结婚”是很遥远的事,但对他的话又深信不疑。我让小表哥把宝剑给我玩,他不给。我就动手抢起来,拉扯中他用手推了我一下,我“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一直滚到水闸口,头重重地撞击在水泥面上,一翻身,就会掉下去。他们两个大呼小叫着跑过来,一把按住了我,把我拖回到坝埂上。我好半天才坐起来,懵懂懂地看着他们。小表哥的脸吓得灰扑扑的,大表哥摸了摸我的头,说不知道头会不会撞扁了,我这才哇的大哭起来。在静寂的午后,我的嚎啕真是·凉天动地。小表哥伏在我面前,一遍遍地恳求着,让我别哭。我越发哭得凶,他把宝剑塞到我手里,我才慢慢地平息了哭声。他们带我来到厨房,大表哥从鸡窝里掏出三个鸡蛋,打了一碗糖打蛋。我一边吸着气一边吃。他们叮嘱我别告诉我爸妈。我拿了宝剑喜孜孜地回家,一声都没吭。
大表姐要结婚了,让我送亲。我牵着大表姐的手绕着坝埂和村子走了一圈,到了大表姐的夫家。其实他们两家“门当户对”,就住在对面。不过几十步之遥。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绕那么远的路,也许结婚就是这样麻烦的事。我牵着大表姐的手,她的粉嫩的脸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一直都是绷得紧肾的,两只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里闪烁着严肃的光,自有一番新娘子的庄严。关了新房,门外鞭炮齐鸣。坐在床上的大表姐,她的脸色像身后的被面那样鲜艳。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是喜悦还是忧伤,却无处安放。只默默地站在一边。我想,等过一会儿就溜出去找大表哥,告诉他结婚真没意思,让他以后别结了。
可是我去读师范的时候他就结婚了。小表哥结婚比我还晚,我妈妈做的媒。对象就是我外婆家门口的,和我同龄,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我们一起下河洗过澡,也上树偷摘过别人家的梨子,还因为分赃不均曾大打出手,只是他们两个人过日子常常吵闹,我妈妈提到他们总会叹气。过年的时候见到他们,小表哥已做了爸爸。
(二)
从大姥家出来,一条河沿岸都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蒲草。走着走着,有时会突然窜出来一些大鸟,如果大弟在这里,他肯定会摸下河钻进草丛里捉到鸟的。我也下过河,和他们一起找鸟蛋,但更多的是折“水蜡烛”
大弟捉鸟雀的本事都是和阿会学的。阿会比我大一岁,他家和我家隔了几户。他有一个妹姝叫阿群,是我的喽,之一。阿会不爱读书,考试总是不及格。可他在村里人的眼中却是个天才。用我爸爸的话说,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怕阿会,阿会是它们的克星。他天生异禀,无师自通,既是捉鱼高手,又是神枪手。只要他扛着枪在村子外转一圈,一会儿手里就提了一串鸟儿回来,村子里养鱼的包塘户像防贼一样,阿会都能从他们眼皮底下,又到大鱼带回家。他还能钓到几斤重的鳖,他的那杆鸟枪就是他卖鳖的钱买来的。以前他用弹弓打乌,也是百发百中。何况现在鸟枪换弹弓,每次都是战果累累。我的大弟是他忠实的追随者,在他身边充当学徒的角色,拎鱼提鸟。烈日炎炎,大弟跟着他“南征北战”,一个暑假下来,晒得漆黑。可的确学到了不少诀窍。一段时间过后,阿会也时常放手让大弟实践。
我有时候会跟着他们叉鱼。一般在午后三点左右,阿会说这时候看塘的人困乏,警惕性差,容易浑水叉鱼。选定一处,他让我们带着鱼叉躲在树丛里,他蹑手蹑脚地,出去侦查环境,一会儿朝我们招手,大弟拿着鱼叉快步跑过去,我也跟过去。水里一条大鱼静静地发呆,阿会说,这条鱼在打籽。他举起叉,瞄了瞄,又向鱼底下偏了约莫寸把长,我说歪了。他不作声,屏气凝神,“刷”的一下,一道银光从我眼前划去,我再定睛细看,那鱼已经在他手里了。他端详了片刻,说够大了,我们就打道回府。在路上,阿会对我解释说水里的鱼,我们看到的只是影子,真正的鱼身在影子下面。后来我学到初中物理中的光的折射,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阿会,他的确很聪明。他叉鱼不贪心,说又多了鱼会变得越来越精,以后就很难叉得到。但他每次出去都不会空手而归。
有时候动静太大,惊动了看塘人,他会迅疾地蹿到芦苇丛或者蒲草丛里躲起来,像一只野兔。有时候实在跑不掉,看塘人堵住他的路,他会狡辩,说你哪只眼看到我是从你家塘里叉的鱼。有的看塘人警告后就放了他,而有的却不依不饶,夺过他的叉,揪着他的耳朵,领到他家里去责问他的父母,说阿会把他们鱼塘的鱼叉完了。阿会的爸爸脾气很暴躁,会追着阿会打。阿会边跑边还嘴,说你吃了我叉的鱼还打我啊。他的爸爸听了,拿起鱼叉就朝他掷去。阿会一溜烟地跑远。
到阿会家投诉打鸟的人也不少。因为他的枪声经常会让人从睡梦中惊醒,且大人也害怕他的枪走火,会伤到人。他的爸爸没收了他的工具。我们就会去芦苇丛里找鸟蛋,或者挖洞掏螃蟹和海虾。阿会能从洞的形状判断出洞中之物,八九不离十。但他有次说洞里是一条黄鳝,结果拖出来的却是一条蛇,吓得我魂飞魄散。我就不敢再和他们去挖洞了。就去折“水蜡烛”。
褐红色的拇指粗的“水蜡烛”,一根根很显眼地立在枝头上,我踩着盘根错节的蒲草去折,折了一大捧带回家。水蜡烛能用作打仗的暗器,还能晒干后当蚊香用。这是听阿会说的。
我把水蜡烛摆放在敞阳处的石板上晒干,有一个黄昏,我突发奇想,点燃了几根水蜡烛,扔到床上,放下帐子。对着里面嗡嗡乱飞的蚊子自鸣得意,想象着它们马上就被熏死。一会儿爸爸回家。见房里烟霹弥漫,欲掀开帐子,我上前拦住,说我在熏蚊子呢。爸爸推开我,拉开帐门,卷起席子扔了出去,又转身抱起铺在床上的稻草。我看到那席子上烧了几个黑乎乎的大洞,不觉傻了眼。爸爸拣起还剩下半截的水蜡烛,哭笑不得地问我,你就是这样熏蚊子的呀。这个关于水蜡烛的故事被他们传诵了许多年。我至今记得。我们躺在阿会家的平顶上,露宿的那一个个夏夜。大人们摇着蒲葵扇,谈着天,我们躺在席子上,看星星。萤火虫飞来飞去,渐渐眼前模糊。不远处,点燃着一根根的“水蜡烛”。
(三)
乡村的夏夜到处生长着诗意。
蝉停止了嘶鸣,躲在高大的树木上准备做梦了,它们比我还累,一天叫到晚,还那么用力。河塘里的水,渐渐地浮起一层轻纱。偶尔有不安分的小鱼儿跳出水面,溅起清脆的水声。小孩子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拎着木桶从河塘里打水,洒在干燥的场地上。一瓢水洒在地上,“扑哧”一下就干了。地面吸饱了水,散发出凉气。大人们从田地里回到家,搬出凉床,摆开小桌子,乡里的人家,都这样露天吃着晚饭,自在惬意,也颇为热闹。一天的疲惫在闲言碎语中淡淡消散。
村子里有人家买了电视机,黑白的。21英寸。大人们吃完饭不再热衷于乘凉谈天,而是赶着去看电视,去晚了就抢不到好位置。人黑压压地挤在屋子里,一直连到屋外。院子里也站着人,只能看到屏幕上点点雪花里晃动着人影,但他们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哪怕是听到里面传出的厮杀声也是新奇和满足的。看电视也指导了我们玩打仗的技术,我们把电视上学到的招式,耍的虎虎生风,个个都像是流落民间的武林高手。玩累了,钻到大人的怀里,或者躺在大人腿上,一会儿就软绵绵地睡着了。我也常常这样迷迷糊糊的被妈妈背着,或者爸爸扛着,往家走,有时候在颠簸里睁开眼,星星那么亮地挂在头顶,也像刚睡醒的一样。
有一个夏夜,我和大弟捉萤火虫。我们很好奇这虫子为什么会发光,问爸爸,他站在人群里伸长着脖子看电视,妈妈也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对我们捉到的萤火虫发光的小屁股一点不感兴趣。我用手捏了捏,光捏灭了,肥又圆的小屁股也捏扁了,大弟愣愣地望着我,好半天才挤出来一句:“这只虫子是我捉到的,你赔我!”我没想到他刚刚还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现在说翻脸就翻脸,觉得大失颜面,就说,你等着,我马上就捉一只来赔你。掷地有声,转身离去。
星星在头顶一闪一闪的,我疑心那是萤火虫变的。见我真的下决心要捉他们,他们好像和我捉起迷藏来,远远地在天上向我眨着眼睛笑呢。转了好长时间,竟然捉不到一只,转身往回走了几步,想到夸下的海口,又不知从那儿升腾起的豪气。于是我向水边的树林走去,那里有几点光一闪一闪的。星光夹杂着水汽,我终于看到一只萤火虫就停在水面上浮起的枯草上,见我走进,又向低处飞去。我趴在地上,手像水面伸去。我至今记得,清凉的水气在夜气里漂浮着,我整个人也像是浮在里面。那萤火虫好似在逗引我,我手一探近,它就展翅飞走,可也不飞远,就轻轻落在我手下面,让我的身体一点点像水面倾伏去。
就在我将要抓住那只萤火虫的时候,电视结束了,院子里的电灯拉亮了。人群散了,妈妈在叫我的名字。发现我半个身子伏在水面,跑过来拉起我,问我一个人趴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要捉一只萤火虫赔给二子,好不容易要捉到了,却被你吓跑了。妈妈看着爸爸,两个人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一种紧张的欢喜,还有说不清的感激。大弟早已在爸爸怀里睡着了,妈妈一把搂住我,好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
我终于没有在那一夜实现自己对大弟的承诺,虽然他一觉醒来早已经忘记。但是事隔多年,我仍然记得,那只在水面上逗引我的萤火虫,那么有耐心地,和一个孩子天真地捉着迷藏,做着游戏。也许,那场游戏会让一个孩子,带着懵懂的勇敢,提前到达一个水晶世界。但是妈妈的呼唤总那样及时,那样有力。而我,无论过去多少岁月,还依然记得他们当时那相望的眼神,那里面充盈着的深深的欢喜和感激。让小小的我,一下子变得那么神圣。
(未完待续)
安徽省无为县第四中学